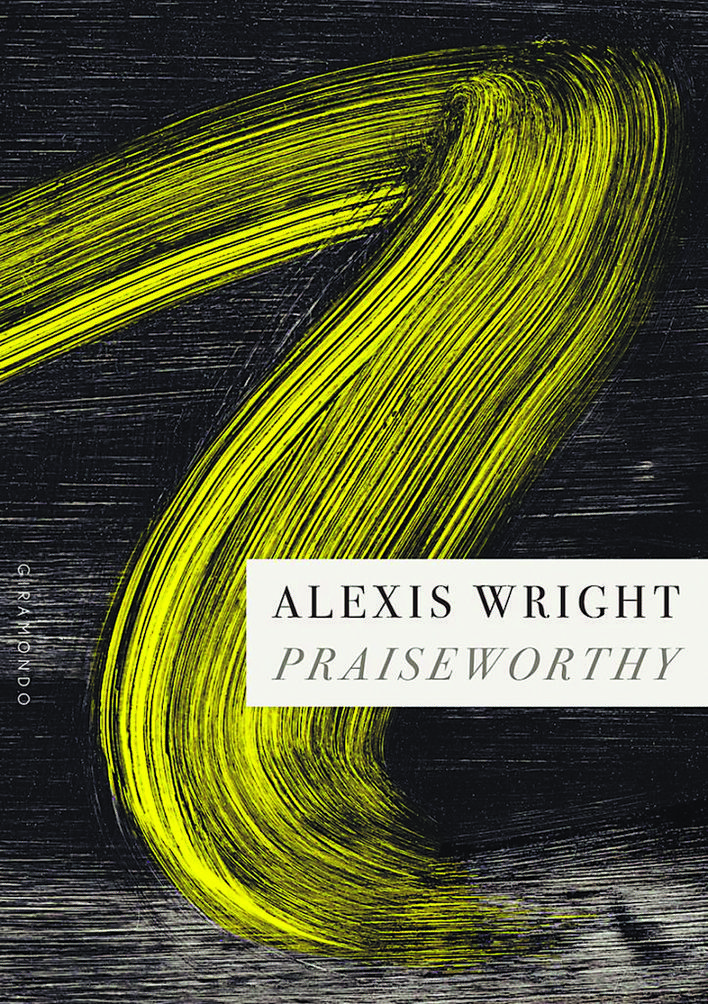“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挑战读者”
2023年4月,澳大利亚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在本世纪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可赞之处》(Praiseworthy)由吉拉蒙多(Giramondo)出版社出版。之前两部小说是《卡彭塔利亚湾》(Carpentaria,2006)和《天鹅书》(the Swan Book,2013)。其中前者曾获得2007年度澳大利亚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后者在2014年获澳大利亚文学协会金奖。
阅读这三部长篇作品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首先文本篇幅很长,每本都有三五百页,甚至还有厚达七百多页的。在网络时代,人们习惯于快速获取信息,而这类长篇小说往往需要持续的专注阅读,复杂的情节和多个角色的存在需要读者潜下心来,摆脱各种干扰,才可能进入更深层的阅读体验。
除了篇幅以外,该作家带给读者的另一个挑战是她的创作类型和内容。纵观其作品,她喜欢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超自然元素,如原住民的神秘传说、祖先的灵魂、魔法以及土地的魔力等,这些超自然元素与现实世界相交织,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感和奇幻性。小说的内容也比较沉重,不论是《卡彭塔利亚湾》里一个沿海小镇发生的原住民部落之间、原住民与白人之间、新一代与老一代的争端,还是《天鹅书》中一个年轻原住民女孩的命运转折,都呈现出一种暴力,既包括人对人的暴力,也包括人对土地的暴力。由于白人殖民者对土地的扩张和资源开采,环境被污染,生态系统被破坏,原住民社区和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小说中呈现诸多沉重的主题,如殖民主义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和文化认同等。这些都是没有答案的复杂主题,作者则通过一种非线性的叙事结构进行意识流式的思考,其中穿插着梦幻与回忆。这些梦幻和象征性的情节及人物,一方面带动故事情节发展,另一方面也表达着深刻的主题和意义,让故事的叙述更加有深度和层次感的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更大的阅读难度。
五年前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一场澳大利亚文学周活动中,笔者曾受邀与赖特讨论她的作品,并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关于基督教文明与原住民文明冲突的问题,还有她作品所要传递的信息等。当时,作为原住民作家,她回答说原住民与土地之间有一种精神联系和精神法则,她的族人心胸开阔,愿意去融合两种文明的力量。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原住民并没有权利决定基督徒能否在保留地建教堂。对于其作品,比如《卡彭塔利亚湾》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这个问题,她说自己的作品希望尽可能地忠实于她的国家与故乡。她力求塑造有强烈个性的人物:“我的族人是非常坚强的,所以我想让书中的人物显示出那种力量。其他人物也是坚强的化身,如诺姆·凡特姆、埃利亚斯·史密斯等。我们族人的力量来自过去,它将驶向未来。” 当时参加讨论的还有北京一些高校的学生,也有学生在引述了关于《卡彭塔利亚湾》的几则书评之后,询问赖特如何看待读者抱怨她的小说难读这一现象。对此赖特的回应是,她知道自己的小说难读,因为她所写的世界是很复杂的世界,难读是正常的;此外,她喜欢在写作中挑战自己,虽然也可以写通俗易懂的故事,但她作为原住民,民族传统就是这样教育她要迎接挑战,无论面对的任务多么艰巨。记得在当时,一同参加研讨的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幽默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强调“好的文学作品就应该挑战读者,否则,作家就是不合格的”。
确实如此,好的作品有常读常新的特点,在不同的时段和环境下,与处于不同状态的读者产生不同的共鸣。它们通常具有开放性,不会强加特定的解释和意义,而是给予读者一定的自由的时间与空间,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理解去解读。
“我连尘埃都不是”
《可赞之处》的扉页是对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一句诗歌的引用:“我连尘埃都不是,我只是一场梦。”看到此句,笔者想起赖特在2022年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中澳高级别人文对话上的发言,她在那场发言的开篇也提到了“尘埃”。当时她所讲的主题是思考如何应对世界的动荡变化。面临着生态系统和原住民生活方式的双重被破坏,作为原住民作家,她希望向内转向对原住民传统文化的溯源与思考,进而从中找到可以借鉴的延续人类生机的方法。她引用的是慧能法师的一段佛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她认为,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对大地的独特理解,所以在经历各种“大自然的尘埃风暴”——文化压迫、干旱和山火后,仍旧能够生存。
笔者理解赖特所一直强调的原住民与土地之间的精神联系。因为精神觉悟后,人就不容易被生命中的尘埃所腐蚀和影响。在原住民看来,土地是他们的主宰者。原住民与土地上其他生命体是一家人,都处于同样的从属地位,被土地所庇护。这种思维与欧洲移民开疆拓土的征服想法属于完全不同的境界。就像慧能用上文提到的偈语来回应他师兄神秀所说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轻拂拭,勿使惹尘埃”。赖特引用此典故意在说明真正的觉悟在于修心、而非修身或修身外之物,而一些原住民、特别是原住民的长老们已经达到类似的清净通透、不被俗世尘埃所扰动的状态。
看到赖特在小说扉页对博尔赫斯这个句子的引用,笔者也想起美国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地球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这句话来自他的《淡蓝色的点》一书,而那个淡蓝色的点指的是天文史上那张著名的关于地球的照片。1990年2月14日,情人节,“旅行者1号”探测器已经飞过冥王星轨道,正向太阳系边缘飞行,它调转相机,从60多亿公里之外为地球拍摄了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里,地球的大小甚至还不到半个像素,而这个不到半个像素的淡蓝色的点就是人类所生存的地球。萨根对这粒尘埃完整版的描述如下:“那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一切。你所爱的每一个人,你认识的每一个人,你听说过的每一个人,曾经有过的每一个人,都在它上面度过他们的一生。我们的欢乐与痛苦聚集在一起,数以千计的自以为是的宗教、意识形态和经济学说,所有的猎人与强盗、英雄与懦夫、文明的缔造者与毁灭者、国王与农夫、年轻的情侣、母亲与父亲、满怀希望的孩子、发明家和探险家、德高望重的教师、腐败的政客、超级明星、最高领袖、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圣人与罪犯,都曾住在这里——一粒悬浮在阳光中的微尘。”与广阔无垠的宇宙相比,地球就是一粒尘埃,显得微不足道。而在这个一粒尘埃般的地球上,人类则更加渺小,这种渺小不仅体现在空间上,也体现在时间上。赖特的小说做着一种超越时空的描述,其核心也是强调人作为肉身的存在、或者说物质世界的存在是不可能永恒的,对于澳大利亚原住民而言,真正的永恒性在于他们原住民精神的传承。
小说的“可赞之处”
在《可赞之处》一书中,赖特用了700多页讲述了地球之上发生过的众多故事中的一个。这个故事发生在澳大利亚北部一个叫“可赞之处”的小镇。因为地球变暖,小说的主人公——一个被用多种名称称呼的梦想家希望给他那些谦卑的族人一个礼物,就是原住民主权发声的永恒无限性。这个梦想家希望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他的族人穿越世纪,从过去的故事中寻找线索,而且他也深知自己的族人已经将历代所经历的故事植入了他们的民族魂魄之中。他认为所有的故事讲述的是不同时代幸存者的经历和感觉——“被改变、被进化、被不断地挑战,但最终总是生存下来的感觉”。对于如何解决全球气候危机和原住民经济困境,他幻想着用驴子来帮助解决问题。与之前的小说一样,该作品充满了魔幻色彩,以及隐喻与象征。
比如,先从地名说起,“可赞之处”(Praiseworthy)这个地名的含义,与《卡彭塔利亚湾》的故事发生地——德斯珀伦斯小镇(Desperance)相比较,要美好一些,因为Desperance有绝望的含义。尽管这是赖特想像的一个城镇的名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澳大利亚西澳区域确实有一个名称相近的城市——“Esperance”(希望),赖特用否定的前缀构词来表达了一种绝望,而且这种绝望感也弥漫在小说之中。比如小说《卡彭塔利亚湾》第二章在开首部分就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是否可以找到希望?然后小说给出的答案是他们不知道希望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幸运的是,长者记忆中的魂灵还在倾听,他们说,任何人都可以在大大小小的各种故事中找到希望”。从故事中寻找希望也是《可赞之处》这部小说的一个主题。
在这本最新的小说中,赖特用“可赞之处”来命名她所想象的原住民居住的海边小镇。但是,它是否值得称赞,这是一个问题。比如主人公和族人居住的地方真是一个可赞之地吗?尽管这座城镇获得过“干净整洁奖”,但它被雾霾笼罩着,城市管道系统破旧,饮用水被污染,电力有问题,贫苦的居民生活在拥挤的、被石棉污染的房屋里。因为过度的开发,这里原住民所生存的环境和地球上其他地方一样,也面临着自然环境的恶化,气候变暖等问题的困扰。从某个更广阔的角度说,本来地球是一个宜居的可赞之处,但是因为人的不可赞的行为而变得问题重重。与萨根、博尔赫斯一样,赖特一直在用她的小说质疑人类的自以为是,暗示人类可能没有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样特殊或重要。一方面她的作品提倡对人类自我认知和谦卑的反思,同时也提醒我们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生命和地球,倾听原住民的声音和可能的拯救地球的原始智慧,因为那也可能是可以称赞的。
在这部小说中,除了“可赞之处”有深刻的、开放性的寓意以外,读者也可以从斯蒂尔(Steel,英文词汇含义为“钢铁”)家族的四个人物的名字来领略作者赋予小说的深刻寓意。首先主人公——父亲这一角色,他的本名是考斯曼·斯蒂尔(Cause Man Steel)。其中“Cause”作为普通名词,在英文中可以表示因果中的“因”,也可以表示“事业”和“诉讼案”。除了这个本名以外,在小说中对他的称呼还有许多:比如“荒诞的末日预言家”,“怪咖”,“令人沮丧的黑鬼”,“见多识广者”,和“阿星”(因为他喜欢研究天上的星星)。这些不同称谓显示出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他一直相信用500万头澳大利亚野驴可以抗衡全球的气候危机和经济危机,因为这种碳中和的运输模式甚至比飞机还具有可持续性。这是他所坚持的一项事业,因此他的英文名字“cause”的另一含义“事业”的寓意也就呼之欲出。关于“诉讼案”的含义与法律有关,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大儿子与警察所打的交道的经历中有所展现。
他的大儿子名字叫“原住民主权(Aboriginal Sovereignty)”。这不是一个常见的原住民的名字,也不是欧洲白人常用的名字。当这个长子出生时,主人公的妻子本希望给孩子起名为“保罗”或者“波琳”这类澳大利亚人常用的名字,但是丈夫坚持给这个长子起名为“原住民主权”,因为这是他“唯一喜欢说的一个词”,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白人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与压迫。他想用这个特殊的名字时刻提醒他的孩子不要忘记自己原住民的身份与诉求。长大后,这个长子的表现也如其父亲所期望的,他是一个拳击手,同时也非常会跳舞,亦被其他族人所喜欢,因为他身体里附着着原住民祖先的灵魂。但是,当他的父亲以无穷尽的斗志去改善原住民在全球气候变暖大环境中日益恶化的处境时,他能感觉到自己与儿子“原住民主权”之间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在那个鸿沟上面根本没有任何的桥梁”。这个儿子的崩溃在于当他知道自己15岁的女友要被政府送到收养机构进行同化改造教育,而他以“恋童癖”的罪名被指控的时候。警察告诉他,“你再也见不到她了,别去惹麻烦。你已经造成了足够的耻辱,她不适合你。你将被送去监狱。这就是澳大利亚的法律,伙计。最后他选择消失在大海之中。
对于家庭成员的死亡,亲人应该是最痛苦的,但是“原住民主权”的弟弟汤米霍克却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出生于2000年的弟弟,不仅在名字上表现着与白人的趋同,他也用本身的行为证明他是被白人统治者成功同化了的类型,是个“被政府成功洗脑过的少年法西斯”。他已经不再认同自己的原住民身份,而是要融入“全球公民的大圈层”之中。他蔑视父母,渴望被“金发的白人上帝政府母亲”所领养。他也痛恨自己的哥哥,嫉妒他受到当地人的喜爱。他总是刺激哥哥,以折磨哥哥的内心为乐。比如,他知道哥哥不喜欢“白人警察“这个词,他仍旧会提。当哥哥愤怒地要打他时,他更加感知到哥哥的恐惧,他会变本加厉地重复该词。他甚至亲自给警察写信告密,把哥哥和女友的恋爱行为举报成他的哥哥是恋童癖、在强奸幼女。尽管逻辑链条有些不可理解,但是他盼望着这个哥哥自杀,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种解脱,可以离开可赞之地,过自己想过的白人的生活。他没有任何兄弟之情,只是偏执无理由地觉得自己和哥哥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仔细分析他定义的这种斗争的结局,其实这个挑事儿的弟弟又是失败者,因为即便哥哥消失了,他仍旧没能找到自身的安宁。
化蛹成蝶的母亲意象
小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主人公的妻子丹丝(Dance),这个名字英文词汇的含义是舞蹈。她追随着蝴蝶学习舞蹈,并在互联网上搜寻方法,希望溯源自己的原住民和华人的双重背景,渴望能到中国生活。作者用斯蒂尔家族的孩子并非纯粹的原住民血统来表达着她对强调“真正原住民”纯粹性的一种质疑。当然这也会让人想到在现实生活中赖特本人的血统溯源,她的曾祖父来自中国广东,她的身上也有一部分华人血统。
丹丝在小说中的另一个称呼是“moth-er”。赖特有意地将母亲mother这个词汇用破折号分拆开,这种方式给笔者带来了一种欣喜的顿悟与发现,因为moth(飞蛾)、butterfly(蝴蝶)和mother(母亲)这三个词汇可以在多个层面上产生联系和象征意义。首先从词义联系上看,蝴蝶原本就是一种“飞蛾”(moth),而这个英文词汇后面加一个“er”,就成了Mother——母亲的含义。母亲的伟大就在于从Moth(飞蛾)向Butterfly(蝴蝶)的转化和新生,因为从蛹到蝶的转变代表着生命的蜕变和成长。飞蛾带着渴望新生或者追求光明的愿望成为美丽的蝴蝶,这恰恰符合丹丝这个人物的心境和精神追求。进一步思考其寓意,赖特通过蝴蝶、以及对丹丝作为母亲这个身份的概念解构,赋予了这本书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因为这个化蛹成蝶的蜕变也应该是她对澳大利亚原住民未来的美好期望。
读完《可赞之地》这部小说,掩卷思考澳大利亚原住民生命历程的变迁、独特的情感表达,以及他们的家庭观与自然观,心中油然而生对他们坚韧精神的赞叹。“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这句话深刻地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化使得所谓的可赞之事或许在另一种时空中失去光辉。时间在变,环境在变,主体在变,赞扬的标准可能也在变。
比如这本书中“钢铁”先生提出的应对地球变暖的方法——不用飞机,而用驴来进行运输。虽然在现实中或许难以实行,但这种富有创意的思考却让我们反思当今工业化对环境的冲击,促使我们寻找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再比如澳大利亚的国庆日1月26日,也被澳大利亚原住民称为入侵日;这一天,英国人正式登陆澳大利亚,从此原住民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他们遭受各种不公与压迫。然而,赖特这位原住民作家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不断描述她和她的族人所经历的侮辱和磨难,却始终在故事中寻找着希望的种子。
在自然界开始反噬人类的时候,澳大利亚原住民对土地的敬畏传统为人类提供着某种启示。他们特有的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智慧或许能够帮助人类找到新的灵感,成为人类寻求拯救和希望的重要支持。
(作者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