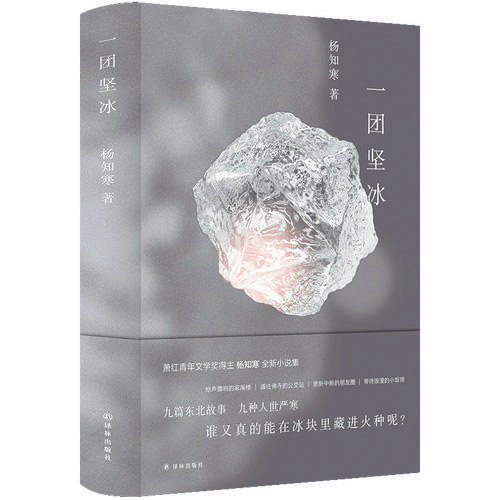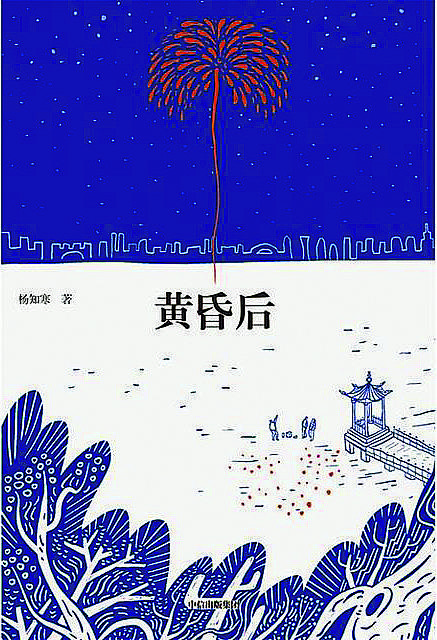2019年初冬在大连,辽宁师范大学与哈佛大学共同举办了一场“东北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王德威、王尧、张学昕、季进、宋伟杰、黄平、班宇等嘉宾与会。会议安排了四场讨论,华东师大的黄平在发言时,以“新东北作家群”来评述双雪涛、班宇、郑执等新锐作家的创作,与会学者积极评价这一新文学现象。记得我和张学昕主持最后一场讨论时,有位教授建议新东北作家群的青年作家,要多读经典作品,汲取创作营养,我半开玩笑地说,现在的年轻人可是喜欢“撕标签”的,班宇听后,一脸粲然。
其实这茬青年作家既有生活积淀,也不缺乏经典作品的照耀,其作品的光芒就是明证。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班宇的《冬泳》,是新东北文学代表性作品。他们在思想上不落窠臼,在艺术上天马行空,没有羁绊和束缚,一任才情挥洒,令人耳目一新。他们的文学无疑高起点,一出道就触摸到文学的命脉,找到小说之核以及与读者情感的共鸣点。
毫无疑问,被称为“铁西三剑客”的双雪涛、班宇和郑执,是文学的英俊少年。他们就像一场早来的春风,生气勃勃地融化坚冰,柔韧的文字还带有寒冰的气质,以超越他们年龄的稳健与犀利,开掘人性的深井,呈现了别样的北中国画卷。他们的小说也是近年影视改编的热点,无论是根据双雪涛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刺杀小说家》,还是由班宇担纲文学策划的《漫长的季节》,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聚焦现实,直面痛楚,不回避矛盾与纠葛,能够捕捉冷色调的魂,在审美上有独到追求,他们的创作令人耳目一新。
在新东北文学的方阵中,有一位独行的女侠,并不逊色于前述的几位,她就是近几年大放异彩的“90后”杨知寒。我七年前主评第五届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学奖,首次接触到她作品,是齐齐哈尔市作协推荐的《破茧》。读这本书时,我惊诧于一个20出头的女孩,能有如此成熟的语言,叙述老练,笔触收放自如,轻灵而不失深沉,有一颗沧桑心,仿佛活了几辈子。
自那以后,杨知寒和她的作品走进了我的阅读世界,只要逢着她的作品,总不会错过。她带给我的文学惊喜,使得我在作协常提起她来,感叹杨知寒是天才作家,我们要对好苗子做好服务工作。近年来她斩获了黑龙江两个重要文学奖项——首届萧红青年文学奖和首届黑龙江文艺大奖,她也是入主黑龙江文学馆展陈系列的最年轻的作家,作品入选黑龙江作协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打造的“野草莓”丛书,同时是新换届的黑龙江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她的作品均发表于文学名刊,近年的各类文学排行榜,总闪耀着她的名字,《水漫蓝桥》《虎坟》《美味佳药》《百花杀》等,收获了众多如我一样的读者。王德威教授和宋伟杰主编《东北文学读本》,我将《水漫蓝桥》在网上下载,转去推荐,他们读后对杨知寒的小说给予高度评价,她应该也是收录在这个读本里的最年轻的作家。何平教授尤其关注杨知寒的成长,特别寄来了译林出版社推出的《一团坚冰》。杨知寒以她的一支笔,英姿飒爽地走向文坛,成为黑龙江青年文学人才的领军人物。
前年作协召开全委会,我见到了杨知寒。她梳着齐肩短发,瘦瘦的,清秀安然地坐在一角,像个女学生。我过去与她打招呼,她只是点点头,绝无寒暄,看上去是个活在心灵世界的人。会议未结束,她为着赶赴一场重要的文学活动提前离会,所以也没机会和她聊聊天。今年黑龙江文学院举办青年作家培训班,我见前来授课的老师名单中有张学昕教授,于是建议把班宇和杨知寒请来,一起在文学馆举办一场新东北文学的对谈。
我再次见到了从杭州飞来的杨知寒。她依然一副女学生的模样,白T恤,休闲裤,参差的秀发像春天的柳枝,随意自然地飘散着。她看上去明媚了许多,目光里有柔和的光影。她告诉我结婚了,先生是大连人,我说怪不得跟上次见你不一样了呢。在人潮蜂拥的中央大街上,一行人于傍晚散步到松花江畔,我们边走边聊,但每说一句话,都得扯着嗓子喊,街市实在太喧闹了。
杨知寒有异族血统,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文化工作者,我说你天生就是好作家的料子。她成长于齐齐哈尔,虽然定居杭州,但笔下故事依然是她熟悉的北国风物,时常回到故乡。不久前收到她寄来的最新小说集,捧读时有些句子让人忍俊不禁,如《喜丧》中的“胖子讲话有点憨,许是被脸上肥肉给挤的,眼睛眯成一线”,《黄昏后》“三七分的头发一颤一颤,茂盛得没分寸”,但《描碑》中“我上手给他眼皮顺下来,心说,博,先到那头儿,先等吧”,描写死亡如此深沉内敛,又叫人心疼。年轻一代的女作家中,南方的孙频,北方的杨知寒,文学气质都与众不同,各自妖娆。
前不久我在黑龙江文学馆主持了一场文学助力龙江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受邀的第七届合同制作家,不约而同提到杨知寒。其实以专事小说创作者为例,这届合同制作家中的孔广钊、梁帅、赵仁庆、刘浪等,虽不在新东北文学的评论视野中,但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成绩可圈可点。来自佳木斯的农民作家王善常在座谈中说,新东北文学不应遗忘乡土文学,我说其实萧红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就是乡土的杰作。
任何一个创作流派的形成和演进,既需要有以石破天惊之力冲击出河流的标志性人物,也需要涓涓细流的浸润和汇入。在新东北文学创作的队伍中,以杨知寒为代表的黑龙江中青年作家,立足本土,以不同的姿态,融入这个洪流。但所有的汇入,都应是自然而然的,而任何一个文学流派能否长远,超越个人经验和地域观的更宏阔的视野,创作实绩的可持续性,也是关键所在。
梁启超先生曾慨叹过新文学运动对国学伤害过深,要知道他当时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文学运动和文学流派也让我想起一种罕见的垂筒花,它可以休眠多年,沉寂无语,最后会被一场意外的大火唤醒。而没有充分的准备和深厚的积淀,是迎不来这样的大火和涅槃的。我期待新东北文学更绚丽的花朵,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