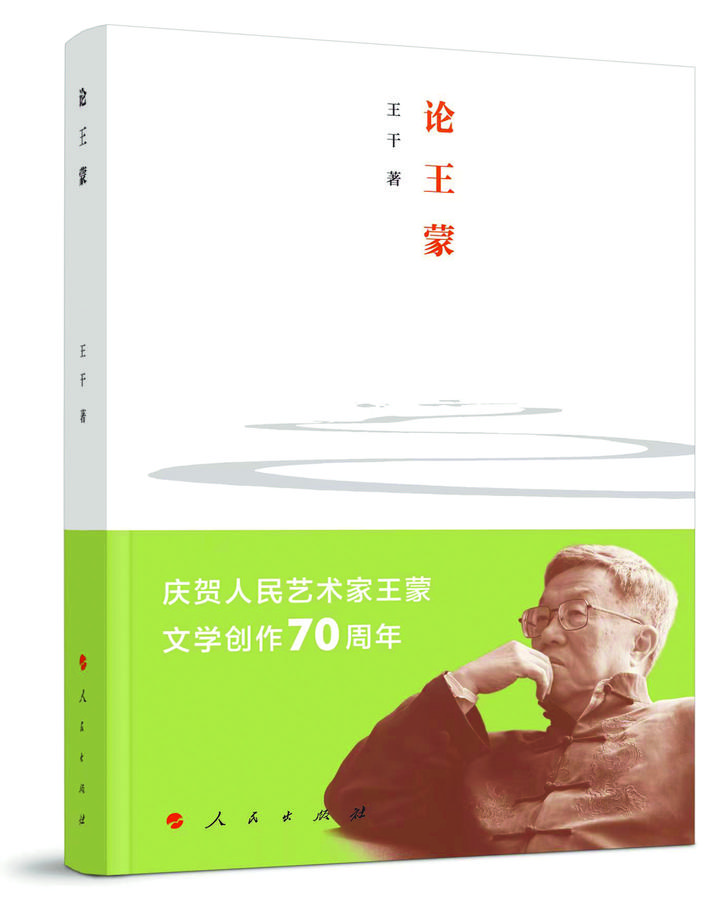□曹文轩
王蒙先生用70年的时间创造了一座辽阔的文学原野,这原野上有森林、草地、河流,还有丰饶的耕地。王干对这片原野崇拜至极,迷恋至极,犹如一只鸟,长久地盘旋于其上空,将这片原野的风景尽收眼底。不只是盘旋,更多的是将这片原野作为栖息之地、赏析之地,或树上树下,或顺流而下,或走马,或流连于各种作物。一本《论王蒙》,足可以看出他对这片原野的了解。这里既有宏观性的俯视,又有微观性的凝视。这是一张关于王蒙文学原野的地图。如果我没有预测错的话,关于王蒙研究的鼎盛时期还未到来,而那天终究是要到来的,因为丰富的、独特的、可以经得起无穷解读的文本在,植被上乘的王氏文学原野在,而当这一天到来时,王干的《论王蒙》必定会是这门研究的重要文献。
文学与政治
王干说:“新中国每一次风云兴起,似乎都会引起王蒙的沉浮。王蒙的作品也几乎完整地记录了个人的沉浮和社会的变迁,《青春万岁》的‘少共’情结,《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直面生活的倾向,《蝴蝶》对历史和个人的双重反思,《名医梁有志传奇》的‘部长心态’,《春堤六桥》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的咏叹与感慨,这些小说几乎囊括了他一生的经历,同时也是新中国几十年来风风雨雨多难历程的折射。”王蒙是“共和国的一面镜子”。可以称之为民族国家“镜子”的作家并不多。就配得上“镜子”这一意象,王蒙先生的文学史地位就已无法撼动了。
而这个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的民族国家。因此,我们看到了这面镜子里总有政治长河涌动的情景,而这一情景几乎是王蒙文学作品永远的情景。当我们的文学因为消极地接受历史的教训而回避政治、以为这是文学走向文学的选择时,王蒙先生从他创作生涯一开始,就一直在政治的语境中乐此不疲,他以他不断问世的文本证明了一个事实:政治也是文学当仁不让的涉足领域;政治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看遍王干的《论王蒙》,我们会形成一个深刻的印象:政治对于王蒙先生而言,永远充满魅力。它是王蒙先生的一个题材,一个主题,一个危机四伏却又饱含着挡不住的诱惑力的非凡地带。他与政治的纠缠不清乃至结下不解之缘,将会成为日后文学史家们的一个不衰的话题。当年,“文革”十年的话题已不再新鲜时,王蒙先生又以一部《狂欢的季节》旧事重提,然后以他一贯酣畅淋漓的笔触,再现了“文革”的历史图景,表现了畸形政治生态之下各色人等的命运与人性的变易。
王蒙先生是政治家吗?我说不好。但他对政治文化中的各种特殊现象的思考和理解却是极其精当与深刻的。他对中国政事的洞若观火,以及对中国政治沉疴之起因的直觉的和理性的见识,远在一般的思想家、政治家之上。
当然,政治显然并非是他的最终目的。他无非是想借用特定的政治环境,来思索有关人生、存在、人性之类的带有形而上意味的命题。而这些命题又是文学应当思考的命题——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基本命题。
王蒙先生的小说在说明一个文学事实:文学并非不能染指政治,问题仅仅在于用何种方式——是用文学的方式还是用非文学的方式。就像生活一样,政治也是可以被文学观照的。王蒙小说意义多多,而其中之一,就是这些小说关于人与政治的不落俗套的思考——在文学边界之内的思考。他从未越出这个边界。这是王干在分析王蒙先生的文本时,无声地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王蒙先生只是一个卓越的文学家。
文学变法
王干说,王蒙先生是“文学创新的旗帜”。在《论王蒙》一书中,王干有大量文字是用来分析王蒙先生的文学创新的,从发现新的主题领域到新的艺术技巧的借鉴与独自发明,都有淋漓尽致的分析,而关于这个话题的零星论述则随时出现在字里行间。新时期文学是在一种强烈的创新意识的推动下进行的,而王蒙先生是发起者、实践者、领军者之一。他宏大的文学世界,是在不断的变法中被建构的。
读《论王蒙》,总让我不时想起当年我在北大课堂上讲王蒙先生。当年我在北大课堂上说了一句话:他运用了几乎所有意识流小说的手段。比如“原发性联想”。
这种联想不是一般心理小说里写到的那种联想。那种联想是有次序的和有内在联系的。太阳光引起温暖的联想,这是正常的。因为阳光确实是温暖的。而美国诗人托马斯的“阳光是太阳踢出的足球”的联想,则是不正常的,然而,却又是人类的心理可能出现的联想方式。
《春之声》中有这样一段:
“那只是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来自这一节铁轨与那一节铁轨之间的缝隙。目前不是正在流行一支轻柔的歌曲吗?叫什么来着——《泉水叮咚响》。如果火车也叮咚叮咚响起来呢?……广州人的凉棚下面,垂挂着许许多多三角形的瓷板,它们伴随着风,发出叮叮咚咚的清音,愉悦着心灵。美国抽象派音乐叫人发狂,真不知道基辛格听我们杨子荣的咏叹调时有什么样的感受。京剧锣鼓里有噪音,所有噪音都是令人不愉快的吗?”
从车轮的撞击声,到对《泉水叮咚响》这支歌曲的联想,到对火车是否也能叮咚叮咚响起的联想,到对广州三角形瓷板的联想,到对美国抽象派音乐的联想,到对基辛格听杨子荣咏叹调是何感觉的联想,再到对京剧锣鼓的噪音和一般噪音是否都令人不愉快的联想,这之间,显然没有必然的逻辑,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和跳跃性。但,这又是一种自然真实的心理流动状态。王蒙在《蝴蝶》《风筝飘带》等小说中,都运用了这一手段。
还有“梦境”“内心独白”“弥漫性情绪呈现”等。
关于王蒙先生对“中国小说文体”作出巨大贡献的话题,是王干的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当我们说“语言大师”的时候,常常是因为这个作家有一种固定的语言风格,或老道,或凝练,而且这个风格只属于这个作家。而王干心目中显然还有另一种“语言大师”:色彩斑斓,意象叠起,谐趣横生,目不暇接,物象、语词、意义杂糅,“东拉西扯”,“胡搅蛮缠”,上下滑动,语流滚滚,泥沙俱下,挟裹着阅读者不能有一刻的停留。王蒙式的长句,竭尽事物与物理的细微层次,而“风筝飘带”式的回旋,使他的语言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美学色彩。王蒙先生就是这样的语言大师。
对于王蒙小说语言的理解,不应只停留在文体的层面上。应在语言的涌动、翻滚、喧哗、互相倾轧的背后读出“冲突”“矛盾”“消解”“解构”“荒诞”“讽喻”“存在的荒谬”等单词与短语。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这里就不一一引用王干细致入微的分析了。
小说是时间的艺术
王干独立一章(第三章),详细论述了王蒙的“时间观”。这一章,是《论王蒙》一书中最具学术性的一章。王干在认定“小说是时间的艺术”之定义后,从“物理时间”“心理时间”“量子时间”三个维度,详尽分析了王蒙先生如何操控小说时间的艺术。
时间无处不在。
可是时间在哪?时间是谁?
海德格尔在他的巨著《存在与时间》发表前三年,曾在一次以“时间的概念”为主题的大会上说:“‘什么是时间’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时间是谁’。确切地说,时间是否就是我们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是否就是我的时间?”对哲学很有研究的博尔赫斯,则用诗化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时间是一条把我卷走的河流,但我们自己就是河流;时间是一只将我撕成碎片的老虎,但我自己就是老虎;时间是一团将我烧成灰烬的火,但我自己就是火。世界很不幸,是真实的;我很不幸,是博尔赫斯。”
时间到底是什么?
时间到底是谁?
从古希腊与古中国的大哲们开始,时间问题就一直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一直是令哲学家们感到非常头疼的问题。他们曾无数次想抛弃它,但都未能如愿——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如幽灵徘徊于一切哲学的空间。
1633年,伽利略被送上宗教法庭,遭到严刑拷打,最后不得不宣布放弃他的“异端邪说”。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要做的事情却是:全身心地投入守时研究和利用钟摆来控制时钟结构。他将时间问题一直带进了坟墓。
时间问题像藤蔓一样,纠缠着哲学。
王干通过对王蒙先生作品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在哲学这里,时间完全是一个悲剧性的概念,而到了文学这里,时间的悲剧性完全消失了,王蒙先生在王干的笔下也就成了时间之马的自由驾驭者,一位随心所欲的骑士。时间的神秘性消失了。文学是对哲学的挽救,这也许正是文学存在的理由。王蒙先生一直在用他的文字追回时间——他的大量作品都是时间的追回——追忆似水年华,王蒙先生是中国的普鲁斯特。让消失在时间中的图景一一再现,贯穿了王蒙先生一生的文学创作。“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来到王蒙先生的文学原野。线性的时间在这里变成了圆形的旋转,五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相遇了。时间在王蒙先生手中成了纸牌。
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作者把前后百年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放在人物一天的回忆里。《春之声》中,火车从起点到主人公的目的地,只需运行两小时四十七分——在时间长河里可算是一瞬。然而,知觉时间却前后大大地扩展了——五十年前的童年到渺茫的无限。它对过去传统小说的单线性时间是一个明显的反叛。传统小说也有时间颠倒,但,它一定会留下明显的时间转换标志:“上面说到”“从前”“他想起了三十年前”“一日……”“一句未了”。而且这种颠倒不会频繁出现,回忆往往是大段的较为完整的事件。但王蒙的这类小说有意忽略他们似乎感到麻烦的时间标志,不作声明,便进行突然转换:“车身在轻轻地颤抖。人们在轻轻地摇摆。”——下面不另起一行,也不作时间转换暗示,紧接着就是一句:“多么甜蜜的童年的摇篮啊!”从而一声招呼不打地就将现实时间甩开,进入了已流逝的历史时间里。当再回到现实的两小时四十七分的时间里时,也不作任何提示。而且《春之声》和《蝴蝶》的过去时间和以后时间对现实时间的切入是十分频繁的,想切就切,来去自由,无拘无束,几行里就是几个时间。读者往往在几秒钟或者几分钟时间里领略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区域里所发生的事件。时间的形象不再是一个一步两步蹒跚着走向前去的老人,而是一个蹦蹦跳跳的活泼之极的小姑娘。自由——这是它的哲学。
与时间秩序被打破相联系的,是空间秩序也被打破。《春之声》中的闷罐子车并不闷,人物心灵的电光早已熔化了包裹他躯体的铁壳,像一位苏联评论家评论王蒙时说的,思想“扩展到宇宙中无限远的地方(在猎户星座和仙后星座里,都包括着春天的力量、春天的声音),更不用提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了,在意识中这些地方的印象不断同窗外的风景交织在一起”。在王蒙的作品中,“有大量的运动和广阔的空间”。
《蝴蝶》《春之声》《海的梦》莫不如此。
王干在一一分析了王蒙先生的时间把戏后,将王蒙先生的这些作品称为“神作”。我非常认可,也非常喜欢王干使用的这个词:神作。
周 旋
不久前,北大文学讲习所请王蒙先生到北大做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我主持了那天的讲座。我说,在与王蒙先生的接触交往过程中,在对他的人生与作品进行阅读时,不知何种缘故,我常常会想到一个词——周旋。
这个词几乎可以概括他的一生,也可以概括他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作品的基本题旨。
周旋含有盘旋、应酬、交道、较量、延宕、引而不发、审时度势、机智、相机进退等含义。似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有了这个概念,才可称得上周旋,这就是: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而悠远的。周旋者必须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很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深谋远虑、荣辱不惊的人,并且是一个有点狡黠的人。由于周旋含有盘旋、迂回、委婉等特征,因此,整个看上去,周旋这个动作是优美而潇洒的,甚至充满旋律和诗性。过程之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僵硬而机械的直线,而是令人迷惑的曲线与弧线。
王蒙先生十一岁时即与地下党建立了固定联系,不到十四岁就成为地下党员。周旋从此时就开始了。这个身份的基本动作就是周旋(王干使用了“少共情结”这个说法)。此后,地下党成为执政党,按理说,说事、做事、写文章就不必再周旋了,而当是直来直去、跃马挥戈、直取目标。但事实上,王蒙先生却是在半个多世纪中,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还是采取了周旋的存在方式。这几乎成了一个永恒的情结。与政治周旋,与世界周旋,与人性周旋,与生命周旋,与荣誉周旋,与文学思潮与文学技巧周旋。到了后来,这个动作已抵达潇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地步。
对于王蒙先生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的人生,对文学史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的文学。而周旋,正是文学的具有生命意义的特征与特质。当王蒙先生将周旋之人生方式幻化在他的作品中时,它却成全了文学、成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周旋,就是动机藏而不露,就是手段隐晦曲折,就是事物不见端倪,就是过程循环往复,就是推拉有度、扑朔迷离、难见分晓、纠缠环绕、危机四伏、运筹帷幄、暗藏杀机,就是青蛇绿草忽闪忽现,而所有这一切,正合上了文学主题的隐晦性、人物性格的多重性、情节结构的不确定性、语言的含蓄性等必需的特质。
王蒙先生在与文学周旋,而在王蒙先生的作品中,主题在与另一个主题或另几个主题周旋,力量在与力量周旋,人物在与环境、人物在与思想、人物在与人物周旋。如果说王蒙先生早期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还是一个分明的世界的话,那么越到后来的作品——如《活动变人形》,如“季节系列”,如大量的中短篇,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就越来越难以看清、越来越难以解读了。由于这种没有明确意思的意思,一些作品甚至被人穿凿附会(譬如《坚硬的稀粥》)。文学作品忌讳的正是袒胸露背、单刀直入、毫无遮拦、不留余地、不留悬念、大路朝天。文学需要的恰恰不是确定,而是摇摆。摇摆正是主题深化、人物前行、情节发展的动力。让我们来看自然界:风中之叶在摇摆着,水上扁舟在摇摆着,而鸟必须扇动双翅才能飞翔于高空,鱼必须摇动尾巴才能游动于水底。存在让我们看到了无数不同形式的摇摆——摇摆也是存在的基本状态。
如果文学本就是存在的一个大隐喻的话,对接两者的可能就是“周旋”二字了。
周旋不是后退,不是放弃,不是明哲保身。其实它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并且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才采取周旋的方式的。“杀身成仁”可歌可泣,但这不应当是唯一的方式。周旋背后是大道、大义。王蒙先生的作品在,他在人生苦旅中、在重大的历史时刻向世人所展现的那些重要的历史细节还没有被岁月的风尘所湮没,我们尽可以去咀嚼、去体会。
感谢王干的《论王蒙》,因为他的这本书,让我的“周旋”一说获得了无比充足的旁证。尽管,王干没有使用这个字眼。
最后,建议王干日后修订此书时,能再加两章。一章是论王蒙智慧。这一章一定要深入解读王蒙先生的幽默。能将幽默抵达智慧境界的,现代文学史上有钱锺书,而当代文学史上就是王蒙先生了。还有一章是论王蒙先生的哲学。因为他的许多作品是运行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的。王干实际上在书中已经多次涉及到了这两个话题。但我以为可以特设两章专门来论,因为这是王氏文学原野上的两大风景。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