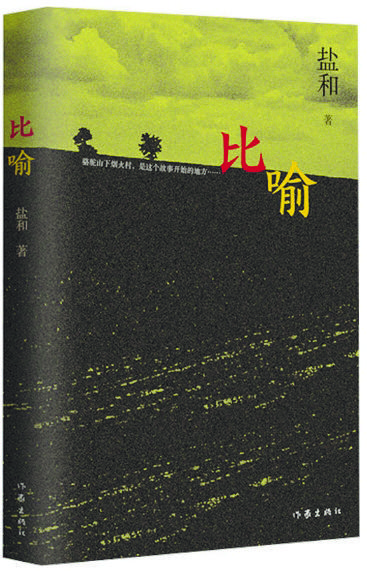□盐 和
某个意志将我投入世界,好像一粒麦种,向上的诉求迫使它首先落在一撮不起眼的土里。我选择了一个滨海小镇,石头和木头在那里竖起原始的偶像,古老的传统制造了无数单纯的幻景。
骆驼山、一星河、杨树林、南山、小石桥、大海和码头……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故乡这些实在的事物上,我最初学会了分别。经验被意识转化为知识,我借此尝试表达自我和他人。
孙灵问、孙莫问、梁先生、大皇姑、张楚云、雨霖、殊兰、兰若、孙灵灵、故新……《比喻》里所有的人物,都曾表达过这片土地。除和个别人有过亲密交往,他们和我,我们仅仅在同一个地方,让杨树林里滑过的风声同样动听。
当我步入大学,伊甸园渐行渐远,我像一个从洞穴里走到日光下的人。《理想国》描绘了人类永恒的抱负,我走近苏格拉底、黑格尔,听到了灵魂不死的传说。我看见时间、自由意志,还有上帝之城的骨架。是智慧使它们组织得那么精巧。
然而,智慧却不能使欲念长眠。40岁前我似乎拥有了一切,甚至更早就取得了商业上自以为是的成功,而性情胜过因果环境所造就的全部,时间和运动也不能改变其方向。船已经抛锚,却泊在了暗礁之处。我挣扎着要换个地方,但缺乏一种崇高力量的牵引。人的生命之中,总有那么神圣的一天,像闪电般闯进我们的习惯。一个傍晚,我遇到了我的花园奇迹。我意识到,要想获救,除非变成盐和,别无他法。
当意识把以往和现在的色调连成一个整体,我和故乡之间却产生了误会:故乡怀着柔情重新接纳她从未远离的游子,而我却在她陌生的肢体上真正认识了故乡。表达的欲望正好发生在这种对立的阶段。在现实和思想中间,那些形象投下了他们的影子。象征最终使《比喻》借助差异完成了某种同一。
我自知,它还不够完美。
作品本身的答辩往往比对它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但小说不同于哲学,是一种羞怯的艺术。任何小说都被它的作者所信奉的法则支配着。冒昧谈谈我所信奉的东西,因此成为一种必要。
在我看来,小说永远不会穷尽对心灵的表现,正如它无法穷尽对现实的表现一样。一部小说做不到,全部的小说也做不到。语言背负了这个责任,因为人们常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那么请问:建筑、绘画、音乐这些非自然语言的艺术,做到了吗?
事实上,错误并不在语言,它只是代人受过。任何一部小说都只是心灵的一个细节,然而人的意识是绵延的整体。
人的头脑里有比盛夏不计其数的花草还要多得多的色彩。我们有理由确信,人类一切知识的奥秘,甚至可以发自一个朴实农民的心灵。只要脚依然占据坚实的土地,一个人就把整个世界连在了一起。每个人的思想、行为或追求,在他自己看来,都表现了他尚未达到却可能达到的自我。凯撒所用的剑,在大学里读文学的青年觉得,若挂在他的腰间,也仿佛亲临了那种征服世界的壮丽时刻。人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他自己,特别是他渴望成为的那个样子。
同情也不能排除在外。同情是一种共鸣。真正的悲悯不是害怕受苦,而是愿意受苦。这种愿望极为微弱,几乎没人希望它变成现实,但情感可以左右意志,使其顺服这种愿望,好像世界对人做了坏事,我们必须要洗刷嫌疑似的。悲剧忠实于意识的戒律,从存在中获得它的高贵。在那里,冷漠无情的命运组装了生活,剧中的人物替他活了一回。在接受艺术诗意的同时,人渴望体验存在的苦涩。所有人都潜伏了一个伟大的本我。就共同的心灵而言,全世界无非只有一个人类。
然而,在共同的心灵里,只有一个恒定且真实的问题,那就是死亡。水能不能变成油,量子力学能走多远,时间究竟是什么,人真没必要在这种事上太纠缠。就算知道了时间是什么,也改变不了时间。人类尚未陷入这些困惑之前,种族也延续至今。崇尚减法的自然主义者倒认为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是历史的倒退。为此,要使人活得有尊严、有幸福感,首先要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而所有的基本问题都是由死亡这个必然结果所引发的。我从哪里来,是人在探求死亡的原因和逻辑;我是谁,是在死前寻找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如果没有死亡,没有对“我将到哪里去”的拷问,其余两个问题都无关紧要。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困境,但困境一定是问题。死亡的困境产生于意识的无限欲求与肉体有限存在之间的对立。世界无动于衷,这种形而上的焦虑越过数千年,依然充满敌意。我们可以设计这样一个命题:如果人永远不死,意味着无条件地活着;反之,只要死亡存在,必然有其条件存在。因为死亡存在,所以疾病、战争、瘟疫、灾害,甚至忧虑,无论什么都能构成死亡的逻辑。人一切的困境都源于这个元困境。
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也有焦虑。他和所有人一样,或短暂或持久地产生过无聊的感觉,以至于他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是无聊得要死。”相反,极度高兴时会说:“我高兴得要死。”一个死字,道尽了元困境无法摆脱的可怖。
人们只关注热爱的事物,而向自己隐瞒死亡的可怖。但真实的东西,不可能被那些试图回避它的人永远摆脱。
人坐在时间的列车上,在未来里旅行。我们总是靠明天或后天活着。未来把我们交给未来,而未来终有止境。站在楼宇间,人看到的还是楼宇。或者在办公桌前端起茶杯时,或者在一场睡眠之后,机械的生活就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人为什么会死?”“我赢得了全世界,又有何用呢?”意识的觉醒从质疑开始出发了。
大自然像圣人一样,也时刻唤醒我们。万物那种昙花一现的真实,使我们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卑微和尴尬。当我们把一块海绵握得更紧时,里面的每一滴水却都流了出去。除了死亡,我们一无所有。
形而上的焦虑就这样在日常的习惯中得以复活。恒定的真实使人开始重视黑夜,爱情、财富、权力,阳光和水,再也不能把觉醒的人送回到纯粹持久的感官快乐当中了。
如果焦虑是一种疾病,那么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带着这种病痛活着。哪怕是绝症,从起初到现在,人类也从未放弃治疗的努力。
“你既无青春,也无老年,而只像饭后的一场睡眠,把两者梦见。”莎士比亚为元困境提供了富有诗意的解决方案。人生如梦,中国更是早已有之。问题在于,主观唯心主义以为提出者果真认为人生从来不曾存在过,然而只要意识到是梦,就意味着存在不再是梦。事实上,这只是一种态度,是对死亡的轻蔑。
荒诞主义者似乎更具喜剧天赋。荒诞像尼采杀死上帝一样杀死了永恒,它倡导人要通过真实的生活,活到自己的未来。元困境被他们的果敢视为笑话,结果荒诞显出了坚不可摧的诚实。只有首先承认了存在,荒诞的感觉才得以产生,所以荒诞也是一种真实。
科学每天都在进步,人类从中获得了足够的自由,以至于坚信,若是找到时间的终点,也就找到了死亡的终点。数学符号被奉为律法,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未像今天一样受人尊崇。“请用数字说话”,几乎成了世界的通行证,好像数字的话都是可信的。人们企图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里搭建永恒的天梯,但科学误导人把假设当作真实,我不能苟同。我只能说,假设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真实。
时间把世界推向当代,思想以其多样化,赋予表象更多的活力。意识无时无刻都面对着丰富多彩的比喻。存在是辩证法,每个人都有权选择按照自己信以为真的东西来生活。这正是我要表明的主题:真实比什么都重要。一切真实都是意识的工作记录。它的组织由全部的时间和空间来阐明。无论哪种思想,都宣示了一个相同的真理:存在是真实的。
每个人都是一部关于真实的哲学。他用真实的心灵和行为,尝试体验、描述、解释和创造某种存在。逻辑是贯穿其中的唯一一条线,所有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东西,都像珠子一样串在上面。正是那条线的缘故,意识才具有了强大的绵延能力。
任何经典都不可能在无意识里诞生。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自觉地把自己在作品里变成人类真实的心灵。他们的作品是人类真实心灵的符号。模仿自然或生活,只是把过去和现在的局部报告给我们,他们却尝试用一个有希望或不绝望的明天来照亮世界。
小说倘若不能使现实升华,思想就会止于模仿。哲学家运用推理的语言解释和创造世界,好的小说家则借用现实的形象,来虚构形而上的心灵意象。意象也是一种语言,是暗示的语言。在那里,充满真实的逻辑,故事制造永恒的困境,逼人们自己做出选择。
直接与哲学对话并依靠哲学认识世界的想法不够亲切,在日常冲突中,它无法安抚我们的灵魂。好小说则不然,它借助意象说话,经验使故事内外的人同时成为真实的占有者。《忏悔录》从人的内部出发,奥古斯丁制造了一双属于所有人的眼睛。那里发生了奇迹,像一面特殊的镜子,我们从中看见了所有美的东西。
众多的文学流派并没有使人忘记那些好的小说。真实若是一则寓言,小说就构成了它的象征。捍卫了人的尊严,小说就捍卫了自己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