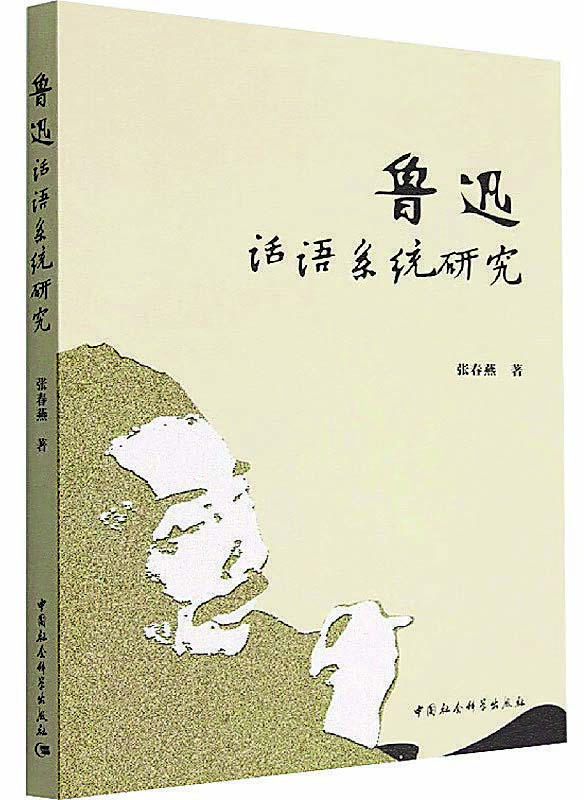鲁迅及其文学创作作为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吸引着诸多学者奋力开掘、探寻深意。对于研究者而言,采取何种方式深入探寻鲁迅作品世界的“中心”是重要的研究前提。张春燕《鲁迅话语系统研究》一书聚焦鲁迅的“话语”系统,研讨鲁迅话语的发生、建构、生成和范式,以此抵达鲁迅的文学世界和精神内核。
关于鲁迅的话语研究,李长之《鲁迅批判》、徐麟《鲁迅:在言说与生存的边缘》、钱理群《与鲁迅相遇》、郜元宝《鲁迅六讲》、孙郁《鲁迅话语的纬度》、朱崇科《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及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已有论述,但从话语系统整体出发来考察鲁迅的生存体验及精神原点,《鲁迅话语系统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在前人基础上,该书着重关注鲁迅的话语体系如何建立起来、生成了何种话语体系、建构出何种话语范式及其生命存在形式等议题,以开放、多元的学术视角考察鲁迅话语内部的动态生成,由此体现出三大特点。
突出“铁屋子”意象与“异乡人”身份在鲁迅话语建构的重要作用。书中将“铁屋子”视为鲁迅对生命个体与世界关系的建构,通过“铁屋子”寓言勾画出鲁迅话语系统的图谱。“铁屋子”凝结着鲁迅话语的“多面体”。首先,“铁屋子”作为其话语体系的核心,其构成元素在鲁迅话语世界中不断复制、变形和位移。“铁屋子”意象在鲁迅作品中屡见不鲜,诸如故乡式“铁屋子”(鲁镇、S城、未庄、吉光屯),公共场所中的密闭空间(咸亨酒店、茶馆、社庙),房屋式“铁屋子”(祖屋、土谷祠)以及狭窄逼仄的意象(“棺材”“坟墓”“独头茧”)。其次,“铁屋子”在有限空间中呈现复杂的关系结构,它蕴含着自我和世界的对立与同源、“铁屋子”的价值构成与“铁屋外”价值构成的对峙和抵抗、清醒者与“铁屋外”世界的关系、自我与“吃人的我”的关系等。最后,“铁屋子”又是中西交汇、新旧交错的“时空体”,既是中国近代遭遇的象征,又是个人精神的困境,充斥着启蒙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对峙,也同样指向哲学性的个体精神状态。因此,“铁屋子”结构成为鲁迅国民性话语与个人性话语关系体系建构路径的原型。同时,“铁屋子”中的异乡人与鲁迅话语空间的建构密不可分,作者在书中讨论“清醒者”与“铁屋子”的多维空间,而故乡作为“铁屋子”的重要变体,是鲁迅生命体验言说的出发点,“清醒者”即为“异乡人”。鲁迅小说多以“我”的还乡为线索,形成了不同关系交织的小说网。作者归纳出“我”与故人、故人与故事、“我”与故事三种稳定的结构关系,每一种关系维度上都形成独立的话语场。在“我”与故人关系中,以理性视角建构启蒙话语下的对象,又被故人的映射反推到自我存在的荒谬境遇;在故人与故事关系中,故事在言说着故乡的人生境遇与生命悲剧,又将故事的讲述者带入无法挣脱的亲缘关系中;在“我”与故事关系中,“我”拒绝与故事交流而阻断传统因袭,又从故事的亲缘中实现自我与故乡的修补。在还乡小说的建构图式中,鲁迅话语建构中的自反性力量得以凸显,而言说主体“异乡人”身份愈加突出。
富有创见地以“双漩涡”图式阐释鲁迅话语的“两个中心”。作者通过研究鲁迅的小说、散文与诗歌,发现对于同一命题,鲁迅往往从多重视角进行言说,其创作整体都存在着题旨的双重性,不同文本之间既有互证补充,又相互悖反。例如《狂人日记》与《长明灯》、《白光》与《孔乙己》、《明天》与《祝福》、《在酒楼上》与《孤独者》、《药》与《复仇(之二)》等作品。而鲁迅话语中的“两个中心”,就是“人吃人”的体验中心和鲁迅对于自己言说的自反中心。这两个中心共同组成鲁迅话语的整体,彼此之间不断进行话语衍生,向外推进至于无穷,呈现出“双漩涡”式的思维图式,这是作者的发现。这一体系包含三组辐射关系,其一是造境与反境,是鲁迅话语系统的初步展开,他营造出荒凉阴郁的世界,又极力突破这个世界,其话语体系内部纠结盘绕;其二是自我与反我,显示出鲁迅精神中的乖离意志,他致力于“立人”,开启民众对自我的意识,却又本能地逆反自我身份,在文本中反复出现自我厌弃的命题;其三是话语意志与反意志,鲁迅话语中的主题带有话语意志上的强力,同时主体内部又出现相异的话语因子,造成话语意志的质疑、偏离和扭转。因此,鲁迅话语的“两个中心”各自不断派生演变,彼此独立又融合互渗,造成鲁迅交错、运动的网状思想体系。通过鲁迅的话语系统,可以让大众逼近并还原他的独特精神世界,一方面是由个人的体验形成的对于吃人世界认知的恒定性,另一方面是个人意志对这种恒定性的打破,在纠结和矛盾的状态中窥见鲁迅的精神世界。作者在书中深植文本,细述历史,通过话语的细致研究形成通往鲁迅精神世界的别样路径。
从整体出发总括鲁迅话语范式并讨论其流变与整合。书中认为鲁迅的生命体系与话语体系合一,分为两大空间:“身外”世界与“身内”世界。鲁迅建构外向的话语空间时,其话语形式表现为向外的否定性,以否定式行为和意志介入并超越外在世界。而鲁迅在建构“身内”世界时,对象则是分裂生成的自我,话语形式呈现出向内的自省和自审定。因而,鲁迅建构的身外世界具有现实性和历史性,向内建构的身体空间具有哲学性和存在主义,从中可以看到鲁迅精神结构的双重性。作者借用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隐喻精神的三种变形来观照鲁迅的话语体系,认为也存在三种话语模式:“我应该”“我不”和“我需要”。作者对此有着精彩论述:“鲁迅有着像骆驼一样的负重精神,踽踽独行于荒漠中;在荒漠之中,骆驼变成狮子,就意味着,在负重之中自我被意识到了;而赤子正是鲁迅回到自身,回到世界。这是不同于尼采的三种变形。”体现出鲁迅生命阶段不断变化的“高低起伏”状态,鲁迅经过了日本时期激昂的“向外”的社会抱负,经历了“向内”的十年沉默,再一次“向外”的《呐喊》,再一次“向内”的《彷徨》和自我争战的《野草》,在《朝花夕拾》里灵魂得到疗愈,又再次投身于世界,诞生了《故事新编》。书中将《故事新编》视为鲁迅与自己文学世界的对话,是他回归行动的自我言说。鲁迅以荒诞的言说方式来对抗荒诞的话语,是他对自己一生文学创作整体的回顾和寓言性言说。因而,作者深刻地指出鲁迅就是自己的矛与盾,是自己的系铃人与解铃人,是一个文学者最终的宿命和完成,道出了鲁迅思想变化的精髓。
在《鲁迅话语系统研究》中,作者认为真正能够通往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内核的路径,正是鲁迅的话语,这是破译鲁迅精神的密码。全书挖掘鲁迅文本的多重话语,在抽丝剥茧、层层追问中还原鲁迅的思维特征与精神特质,在看似熟悉的文本背后钩沉出更为厚重的思想内容。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