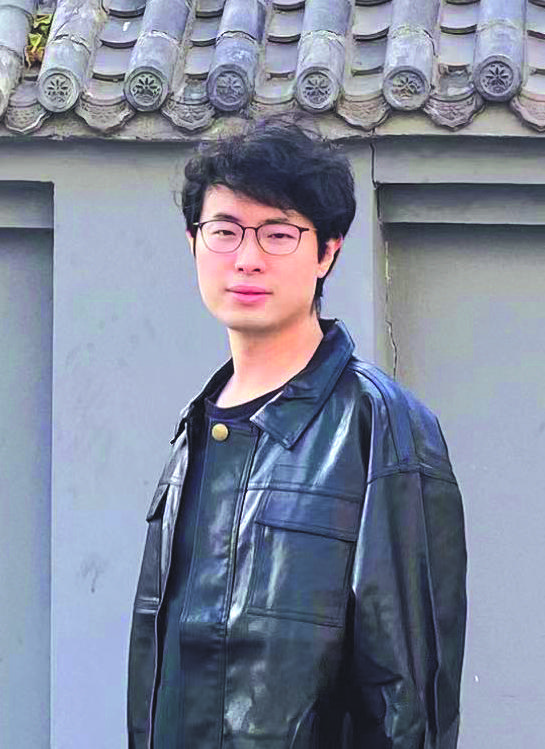毕业后的第五个春天,我把家搬到地铁站附近,60平的一居室变成了30平不到的小开间。起居面积缩水,但世界有所扩大,我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费了些时间清除墙角的霉斑和旧家具的气味,购入自动咖啡机、沙发床,以及一台音质过得去的智能播放器。没地方摆唱片,但有足够大的硬盘存储无损音频,按照风格和出版年份,我把海量的资源各归其位,添加封面,修修剪剪,从中体会到难以言明的乐趣。此外,我还养了一只猫。实际上是被骗了。前同事说她要换房子,托我帮忙喂养,谁知她很快离职回了老家,就此失联。我给弃猫取名蒙克,是我最喜欢的钢琴手的名字。蒙克不挑食,也不排斥吵闹的音乐,唯一喜好是蹲在窗前看小区里的野花和小鸟。我有时觉得蒙克很孤独,有时又觉得它自得其乐。
许久不联系的房娜约我见面,是双方父母的主意。作为同窗,我和房娜同时逃离家乡,来到国内最大的城市念书、工作,但都没有碰到过哪怕最小的运气。我们的父母是同事也是朋友,他们一致认为,我和房娜不该单打独斗。毕竟我俩年龄都不小了。在他们眼里,我们正在挥霍谈婚论嫁的本钱,终有一天会丧失掉对异性的吸引力。这种想法错得离谱。据我所知,房娜有固定的Dating对象,年纪有大有小。他们不大可能步入婚姻,但会相互陪伴度过一些乏味的日子。而我忙于接活挣钱,仅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和家里的智能播放器打交道。
房娜很会穿衣服,针对不同场合,呈现气质迥异的妆容,至少在朋友圈是这样。相比之下,我这个所谓的设计师显得过于潦草,总是衬衫加西裤。见面这天晚上,房娜裹一面格纹头巾,身穿色彩斑斓的连衣裙,远远看去像一棵灿烂的桃树。我提议挪到靠窗位置,视野好,能看夜景。房娜反对,这个时候,屋里的人恐怕才是夜景。我们分头扫码,点了自己爱吃的东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各自的状态。房娜放下手机说,你很擅长迟到。我说,设计师不打卡,平时懒散惯了。房娜说,气人是吧?——记得上次见面,大概十来年前吧,房娜在同学聚会上说过相同的话,就好像还是昨天。
房娜是我的初中同学。也就是说,我们掌握着对方某段人生的秘密。那时的房娜话少,成绩优异,虽然有点冷漠,但很受班上男生的欢迎。房娜的梦想是出国,大家还在啃课本的时候,她已经偷偷学了新概念和朗文,所以没时间和任何人闲扯。至于那时候的我,只能用一无是处来形容,如果哪天我消失了,都不会有人发现。有一次班里组织集体看电影,我迟到了,房娜一个人留下,负责在公交站等我。那天刮着大风,房娜用围脖遮住半张脸,厚厚的齐头发帘被横冲直撞的风掀起,露出瘦窄的额头。我说,对不住,耽误你看电影了。房娜说,那种电影,看了也是浪费生命。说完转过身,悄无声息地走在前面,像一个远去的旅人。
房娜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刚才说了,做设计。房娜让我展开说说。我说,怎么说呢,就是把模糊的理念具体化、视觉化。房娜眨着眼睛,不知是没理解,还是刻意表现出对我很感兴趣,总之,让我有些不知所措。这天晚上,房娜问了我很多问题,我有的回答了,有的只想埋在心里。比如她问我,如果你的爱人对猫毛过敏,你会不会主动把猫丢掉?
吃完饭已是10点。我答应房娜,到家后拍蒙克的照片给她看。打开家门,看到蒙克向我跑来的一刻,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仔细地洗完澡,把头发吹干后躺进沙发床里,喊了一声比尔·埃文斯,就像在呼唤一个老朋友的名字,“Skating in Central Park”浅浅地递到我的耳边,很快我便睡着了。
不久之前,我接到一个给市集活动做设计的私活,这两天拿到尾款的同时,还收到了主办方来函。他们邀请我以嘉宾身份赴宁,报酬还算可观。市集位于农场腹地。我见识了网友们说的金陵花海,高高低低的花冠如同麦浪涌来。但我实在怕热,在房间坐了好一会儿,汗才退去,没干透的部位隐隐发凉。我像个上了年纪的人,一觉睡到晚上,直到房娜发微信把我震醒。她问我,怎么还不发蒙克的照片,该不会是忘了吧。我从手机里挑了一张,发给对方。房娜回复:你这个人不老实,照片里明明是白天。
这次出门,我给蒙克准备了吐粮机和充足的水,即便一周没人照顾,蒙克也能安然度过。我打开App,链接家里的摄像头。加载之后,黑糊糊的视频跳到眼前。我调整角度,巡视一遍家里,蒙克守在吐粮机旁边,扭头看着摄像头,两只眼睛发出饥饿的绿光。放大一看,吐粮机下面的碗是空的。我尝试手动吐粮,碗里依然空空如也。我忘了给机器添粮。蒙克饿了一天,而我过两天才能回家。正想着,突然收到房娜的留言:记得给我拍蒙克的照片。我赶紧说:朋友,帮我个忙。
我约了车。黑暗中,房娜化身为手机地图上一粒孤独的小点,从四环外缓慢游向城市的心脏,继而折向东面,一点点靠近目的地。在我的提示下,房娜从水门里摸到钥匙。接着,门被打开,视频中出现穿着白色连帽卫衣的女孩,她把自己裹得很紧,仿佛走了很远的路。房娜扭开昏暗的壁灯,来到摄像头下面,冲我挥了挥手,她好像瘦了一圈,有点初中时候的样子。我想看清房娜的脸,但觉得这样做是一种冒犯,于是关闭摄像头,拨通了她的手机。
房娜说,你的猫没事。我说,谢谢啊。房娜说,是吐粮机卡粮了。我说,谢谢你,回去请你吃饭。房娜说,没想到我和它第一次是这样见面的。安顿好蒙克,房娜说她有点困,问我冰箱里有没有饮料。我说,没有饮料,你可以做咖啡喝,在电脑桌后面。
房娜又问我,能否借沙发一用?我说当然可以。不知怎地,我俩的对话,突然唤醒了沙发旁边的智能播放器。手机那头传来了汉克·莫布利的“The Best Things in Life Are Free”,音符很快像深夜的花香一样挤满狭小的房间。
房娜喝了一口热咖啡,说,来,谈谈你的音乐吧。我猜她已经坐在沙发上,因为她的声音放松了一些。汉克·莫布利,被乐评家称为次高音萨克斯界的中量级冠军,他的演奏风格比较特别,介于冷爵士和硬波普之间,我认真说道。房娜顿了顿说,挺有意思,然后把剩下的咖啡灌进喉咙,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嗯……莫布利很有天分,我继续说道,但仅止于此。无论他怎么证明自己,也不会成为像斯坦·盖茨或切特·贝克那样的巨星,更无法成为约翰·科川那样的大师。
房娜嗯了一声,声音有些微弱。她说,可是,这些曲子听着明明都差不多的,为什么要一直听?我又对此解释了一番。但不重要了,房娜蜷在沙发上睡着了。她可能真的很疲惫。我小心翼翼打开摄像头,吃饱喝足的蒙克也睡了,在房娜脚边,团成一个紧致的毛球,身体有节奏地起伏着。
第三天晚上,我回到家,快步走向沙发,瞥见旁边猫碗里的水依然清澈,想到房娜可能换过。我抱起睡眼惺忪的蒙克,它吧唧几下嘴转醒。这时,外面突然传来电梯门关闭的声音,蒙克一脚蹬向我的胸口,朝门外冲去。我愣住了,重新穿鞋,锁上门,拿出手机,给房娜发消息说了推迟吃饭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找了很久都没看见蒙克。后来我在小区里贴了寻猫启事,半个月过去了,没接到任何电话。因为忙于找猫,我也没再约房娜吃饭。有一天我点开朋友圈,看到了房娜刚发的照片,一捧精心搭配的鲜花,配的文字是surprise。我站在窗前望去,蒙克经常望的应该正好是斜前方那片野花,黄色的花蕊被包裹在浅紫色的花瓣中,微微颤动。我打算去那边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