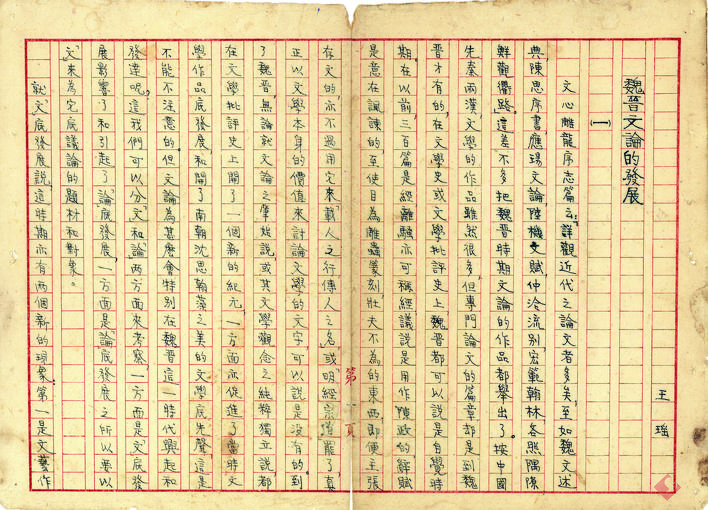从时代印记的角度而言,王瑶先生的文学史著作最明显的印记是其基本的框架和体例。在基本的框架和体例上,《中古文学史论》和《中国新文学史稿》别无二致,虽然两部文学史专著论述对象各别,研究者与对象的关系也有别,《中国新文学史稿》是“唐人选唐诗”,《中古文学史论》则是“宋人选唐诗”,但都是从政治社会情形述起,次及社会风貌,最后论述作家作品,并且论述作家作品时侧重于主题和文体。在《中古文学史论》的自序中,王瑶先生表示,“我们和前人不同的,是心中并没有宗散宗骈的先见,因之也就没有‘衰’与‘不衰’的问题。即使是衰的,也自有它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而阐发这些史实的关联,却正是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底最重要的职责”,这种意见正是其文学史框架和体例的观念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瑶先生依循唯物史观的理解将对文学作品的文体理解和美学判断都相对客观化了。不过,在具体的论述中,他似乎察觉到了这种历史叙述可能带来的问题,在论述中古作家的门第和文学成色的关系时表示,“我们当然不能依作者的门第品评作品的高下,但作者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却是依他的门阀和官位而定的;文义之事固不能说毫无关系,但确乎是很微,是间接的。我们虽然不能说名门大族出身的人底诗文一定好,但文学的时代潮流却的确是由他们领导着的”。由于注意到门阀官位这种社会政治现实与文学潮流的直接关系,王瑶的文学史框架和体例就免不了要论述文学流派以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而由于注意到“文义之事”与门阀官位关系“很微,是间接的”,他的文学史框架和体例就免不了专章或专节论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这就使得其文学史框架和体例具有辩证性,他也透过历史的针脚阐发作家作品的独立价值,而并不专在阐发文学与时代、社会的历史关联。
王瑶先生的上述特点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该书第二编“左联十年(一九二八-一九三七)”中,“左联十年”的命名是具体时代的政治观念和时代气氛下的一种特殊表达,只能理解为左联起主导作用的十年,而不是左联存续了十年。该编第一章“鲁迅领导的方向”也应作相应理解,不是十年间只有鲁迅起到了领导方向的作用,而是鲁迅的作用被特别强调了。但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在这种明显露出历史针脚和时代印记的地方,王瑶先生并不只是在应和新民主主义论的革命史观,他凸显鲁迅其实意味着凸显中国新文学史及左翼文学作为文学史的独立性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编关于文学现象的论述中,王瑶先生大体上采取了主题学式的分类法,尤其是第八章“多样的小说”,分为“热情的憧憬”“透视现实”“城市生活的面影”“农村破产的影像”“东北作家群”“历史小说”六节,没有一节说明了归类的理据,却有意无意地把并非左联的作家作品都组织进历史叙述中。这样一种模糊而暧昧的处理使得文学的品评深隐在历史的针脚中,而一定时代下的历史观与文学史事实之间的错位也就显得极为醒目。以其中“城市生活的面影”一节为例,该节论述了老舍、巴金、靳以、沈从文、张天翼、欧阳山、草明、葛琴八位作家,老舍和张天翼的篇幅最多,巴金次之,沈从文略多于靳以,其次是欧阳山和葛琴,草明是论述欧阳山时连带着述及。在这一组合中,老舍、巴金主要在写“城市生活的面影”是不错的,王瑶先生也注意到了沈从文主要在写湘西,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显然不是“农村破产的影像”,而是将其视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写“城市生活的面影”的作家,由此增添了有别于左翼文学的乡土叙事。王瑶先生强调沈从文“文字自成一种风格”,认为他的才能使他在说故事方面比较成功。这种独具魅力的文学慧心,使得王瑶先生的文学史研究透过历史的针脚,留下了作家作品耐人寻味的文学魅力,文学之为文学,到底是与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有所不同的。
事实上,即便在《中古文学史论》和《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框架和体例下,王瑶先生在缝密历史针脚的同时,也发挥了他对于作家作品的体贴,展现了文学之慧心。例如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他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读者欢迎与否的角度来论述巴金小说的价值,认为巴金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很健全”,“但就在读者中所发生的影响说,仍是有积极的启发作用的”。这种论调在1957年写的《论巴金的小说》中延续下来,王瑶先生仍然强调巴金小说的社会影响大、读者多,客观上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但同时也颇多体贴之语,见出其文学之慧心。例如王瑶先生认为《新生》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之类的表达独立成篇,“对于革命者牺牲的积极意义就多少突出了一些”,而“作者也用生活本身,即情节开展的逻辑性来事实上对于那种单纯献身的观点做出了一些批判”,这就对《新生》的形式和巴金的用心颇有体贴。又如王瑶先生在依着巴金自己的小说写“性格”说分析“爱情三部曲”时表示:“就小说的动人程度和艺术成就来看,我以为在‘爱情三部曲’中以《雨》为最好;不简陋,不枝蔓,虽然充满了一种霪雨式的阴郁凄凉的情调,但读来是会感到真实和动人的。”这就颇见出文学之慧心,既有作品优劣之品评,又对叙述形式和小说情调有独到的把握。而且,那种从反面说出来的话,即“虽然充满了一种霪雨式的阴郁凄凉的情调”,其实直指小说《雨》的核心,暗示了王瑶先生对文学的浸润之深。洵可谓非浸润日久,不足以养成其文学慧心也。
最好的例子也许是王瑶先生对鲁迅的研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王瑶先生主要勾勒鲁迅文学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认为“鲁迅从他的创作开始起,就是以战斗姿态出现的:他一面揭发着社会丑恶的一面,一面也表现了他的改革愿望和战斗热情。在这二者的统一上,不只他作品的艺术水平高出了当时的作家,就在思想性的强度上也远远地走在了当时的前面。当作文化革命的旗帜,三十年来多少进步的作家都是追踪着他的足迹前进的”。这种看法应和着新民主主义论的革命史观,“艺术水平”近乎“思想性”的附庸,似乎不值得专门论述。但王瑶先生显然清楚自己的文学史论述受制于具体的框架和体例,此后在《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和他所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论〈野草〉》《〈故事新编〉散论》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文中留下了一个文学史大家对于作家作品独到的体贴和会心。除了学界早有揄扬的一些关节,如王瑶先生发现《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与魏晋人物阮籍、嵇康的行迹和精神关联,发现《故事新编》的“油滑”与二丑艺术的关联,王瑶对《儒林外史》和鲁迅小说之关系的理解,也是发人深省,足见其文学慧心的。在《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一文中,王瑶先生谈到鲁迅推崇《儒林外史》的原因包括“士林”风习的深切体会、讽刺艺术的热爱及小说形式结构的接近三个方面,其中关于小说形式结构的分析尤为精到。他认为鲁迅技巧圆熟的小说《肥皂》《离婚》与《儒林外史》一样是“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而“《阿Q正传》《孤独者》等首尾毕具,人物性格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展开的作品中,那种以突出的生活插曲来互相连接的写法也不是传奇体或演义体的,而更接近于《儒林外史》的方法”,这种观察可谓颇具慧心。而更为重要的是,王瑶先生表示:“鲁迅小说的形式结构,因为它是短篇,并受了外国近代短篇小说的影响,因此在向民族传统去探索时,就更容易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了。”这就堪称神来之笔了,鲁迅小说形式自身的历史不仅联系着“外国近代短篇小说的影响”,而且联系着《儒林外史》标识的民族传统;在中西交汇处,鲁迅小说获得了其自身的历史。这是真正的文学史研究,一切历史的针脚,不管是隐是显,都不那么重要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