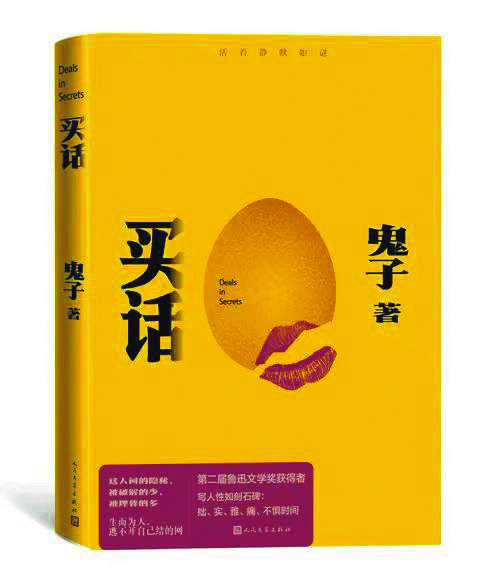许多年以前,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瓦城上空的麦田》等小说,创造了我们文学绝美的风景。那里似乎也没有什么先声夺人的奇异观念和方法,但读过之后就是让你怦然心动挥之难去;许多年以后,《买话》如苍老的浮云,那个叫刘耳的老人选择了返乡,故乡有味蕾的深刻记忆,有他初次体会的男女之事,也有他少年和青年时代不曾示人的诸多隐秘。当然,刘耳返乡的口实是要疗治他老年人常见的前列腺疾病。于是刘耳还乡了。
小说从刘耳对一碗玉米粥和与青梅竹马的竹子的男女肌肤之亲写起,那是刘耳挥之难去的乡愁和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他要回乡寻找他的过去。回忆是时间的逆向之旅,也是人生只可想象不能经验的过去。但刘耳的尴尬在于,返乡也与他一次不光彩的经历有关:儿子的秘书黄秘书安排他体验一次按摩,结果被警察执法发现有伤风化,黄秘书通过人脉将其救了出来。因此,刘耳的返乡也有难以言说的逃避心理。但是,乡下并没有成为刘耳的避难所。对个人来说,他临时起意的返乡是一种“试错”行为;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现代性没有归途,他重返乡里是一种“逆向”的选择。他的双重“试错”,注定了乡下经历的尴尬和苦痛。
刘耳还乡,最先想起的是瓦村的玉米粥和腌制的辣椒酸,瓦村最好的玉米粥是“老人家”熬制的,老人家是竹子的母亲。21岁那年,刘耳和竹子有过一次“闪电般”的亲密接触。前后大约一小时,在刘耳的记忆里,“那真的就是一道闪电”。刘耳和竹子的关系,让人想起高加林和巧珍的关系。高加林和巧珍确立了恋爱关系,当高加林要进城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巧珍;不同的是,在刘耳即将进城的前夜,他和竹子发生了真实的男女关系。虽然讲述者云淡风轻,但竹子的决绝和义无反顾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乡村女子对爱情的坚定和隐忍,那里甚至隐含了某种惨烈。给竹子的笔墨极为简略,但竹子和她的情感及行为,是小说最为动人的篇章。小说对女性,包括竹子、二妹、香女、贩鸡的小女孩以及受伤的女战士在内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小说最有情感力量的章节。
刘耳到竹子母亲“老人家”家里讨一碗玉米粥,那份卑微隐含了他对竹子的愧对和歉疚。老人家真是不给面子,居然没有满足刘耳一碗玉米粥的要求,她甚至给狗吃了也不给刘耳吃。这该是多大的仇怨啊。这里有老人家对刘耳“始乱终弃”的厌恶和不屑,也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母亲对刘耳能够实施的最严厉惩处——她还能做什么呢?对刘耳来说,这还不是刘耳还乡最坏的经历。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这个曾经的瓦村人,在村里无人理睬,他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甚至怀疑自己“算不算村里人”。这时一个叫扁豆的小男孩出现了。人称“牧民”的孙子扁豆的出现,是来找刘耳借钱的。小孩子扁豆借钱,刘耳询问因由是正常的,可扁豆的执着着实让刘耳疑窦丛生。最后扁豆说明了缘由,他是和别人打赌:如果借到了,扁豆就赢了,如果借不到就输了。扁豆看到了香女转送给刘耳的钱,他知道刘耳有钱。和他打赌的是村里一个名叫“光棍委员会”的十几个光棍。如果扁豆输了,就用扁豆家的大肥鸭下酒,刘耳先后抽出了十张百元钞票,500元让扁豆去换回他的大肥鸭,500元给扁豆的爷爷买酒。刘耳说是给的,不是借的:“你刚才给我说了那么多真话,我用钱买还买不来呢。这点钱呀,就当是买了你的话吧!”这是小说“买话”的由来。当扁豆把刘耳“买话”的事情告诉爷爷“老牧民”时,爷爷说:“他用钱买话这个事,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一个结果!你就想想吧,他不是从来都不给别人借钱吗,他现在老了,回到村里来了,想吃一碗玉米粥,人家老人家都不给他。这是为什么?他心里不清楚吗?他心里要是不清楚, 他会跟你说这钱是买了你的话吗?”无论现实还是过去,刘耳的经历没有风起云涌,但那些波诡云谲的历史改写了刘耳风光无限的过去。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刘耳。
刘耳还乡后重新经历了“过去”,但物是人非事事休,瓦村已经不是过去的瓦村,重要的是刘耳也不是过去的刘耳。刘耳“重返”过去,是“重返”了他当年不被人知的“秘密”。他隐瞒了置换明通可调到县里做记者的名额,隐瞒了和竹子那道“闪电般”的经历,隐瞒了14岁明树惨死的过程,隐瞒了明通和他一起用7个鸡蛋慰问女战士,而宣传时只有刘耳一个人的事实,那是改写明通命运的“鸡蛋事件”。刘耳院子里出现的7个空鸡蛋壳,意在表明,事实尽管被隐瞒,谎言也必定会揭穿。在这七个鸡蛋壳面前,那时狡诈的刘耳现在应该羞愧难当。当时的刘耳恰恰成了“标兵”,成了红极一时的“名人”,他还曾得意地警告明通:“现在的情况是,你出名了,我却快累死了。我这个累,是你给害的吧?你害了我,你就得帮帮我,你要是不帮,那可是天理不容!我现在就告诉你吧,我刘耳真要是这样累死了,我会天天深夜去敲你们家的门,敲你的,也敲二妹的。我让你们到死都成不了夫妻,你信不信?”荒诞的生活是被组装起来的。除了刘耳和明通命运的对比,还有刘耳和竹子命运的巨大差异。那道“闪电”过后,刘耳可能偶尔会想起竹子,但他对竹子的命运一无所知,刘耳后来看到了竹子写给他的“刘耳收”的十封信。这十封信给了刘耳最沉重的一击:他辜负了也伤害了一个痴情又自尊、忍受过巨大伤痛女子的心。竹子因那晚“闪电般”的经历怀孕了,她打掉了孩子便不再有生育能力。这时刘耳的心理处境可想而知。诸如此类,是他还乡后浮现出来的。这是一个人挥之难去的创伤记忆。这个记忆才是真实的刘耳。
我们还看到了《买话》对现实的批判。乡村中国经历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在文学作品中有不同的讲述,那是《人生》《陈奂生上城》《种包谷的老人》《命案高悬》《世间已无陈金芳》,也是现在的《买话》。是高加林、陈奂生、冯幺爸,是尹小梅、陈金芳和刘耳,构成40多年来乡村人物的序列形象。当然,还有《买话》中的十几个光棍,还有竹子、香女、老人家等。只有走进生活的细部,我们才会了解真实的乡村中国。《买话》的生活化弥漫四方,小说就像一条生活之河,瓦村的生活细节在河流中不时泛起,我们仿佛就置身在瓦村的人物和生活之中,他们因鲜活生动而被赋予了生命。我注意到,《买话》的细节真实和整体性荒诞构成了它的“先锋”品格和精神。如果说80年代的“先锋文学”更多的是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为僵硬的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以《买话》为代表的、表达当下中国生活的小说,示喻了来自中国本土生活的“先锋文学”,正式登场了。这些作品包括李宏伟的《信天翁要发芽》、李修文的《猛虎下山》、郑小驴的《南方巴赫》、牛建哲的《耳朵还有什么用》等,当然也包括鬼子的《买话》;另一方面,《买话》的价值更在于它用隐喻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当下乡村中国的故事。表面上它波澜不惊,但只要认真阅读,你就会知道什么是惊心动魄。
《买话》的成功,是一切都在云淡风轻的讲述中,生活的力量无比巨大。对普通人来说,他们就生活在历史的皱褶里,历史不会讲述他们,但细节构成的历史是难以颠覆的。曾经光鲜的刘耳,在“重述历史”中轰然倒塌,个人的历史也是经不起考问的,我们自己也曾想忘记或抹去某些历史,一如史官讲述历史一样。而他要疗治的“前列腺炎”,是老人家用一个葱叶和一支竹筷子治愈的,他的尿道通了也是一个隐喻,那是他自青年时代开始的纠结和谎言被彻底戳穿也就彻底地疗治了。当竹子的母亲、“乡村郎中”老人家去世时,瓦村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所有的人都来了,他们去为一个“老人家”送葬,就是在对一种再也难以经验的生活的凭吊。那里隐含的巨大感伤如惊雷滚地。现代性改变了乡村中国,但现代性的两面性我们并没有充分认知,特别是它的“另一种面孔”。另一方面,现代性是一个未竟的方案,当我们在批判这个不确定性的时候,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合目的性”。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