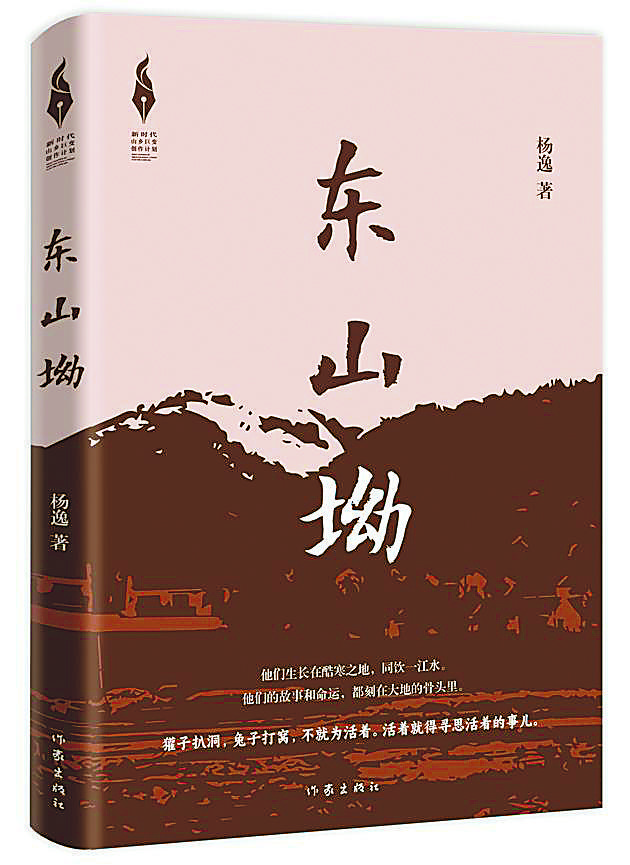人们乐于把过去的事叫作故事,不管大小,只要已经过去的,都是故事。
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东北。具体点说,东经126度交叉上北纬43度,叉出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韩屯。韩屯不大,在普通地图上还不够画个顿号。有村户百十来家、村民四百余口。韩屯有座山,名叫东山,它像道高大的屏障,挡在韩屯东面。韩屯就囫囵个儿地窝在东山坳里——我所讲的人和事,都在东山坳。
原先,村头有口老井,井边有几棵老榆树,头很大,发量浓密。每到夏天,老榆树顶着满头墨绿,给身旁生产队大院儿撑出块荫盖。荫盖下边是牲口棚,长长的一趟,里边一排木槽,槽头上拴着二三十头牛马。生产队的牲口都住集体宿舍,吃大锅饭。就外边有个单间儿小灶,招风惹眼,也不怕遭妒忌。
单间儿住的非牛非马,是头灰毛长耳驴。这驴骟过,未婚未育。别的牲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它不光上白班,还常上夜班;别的牲口都有外号,它只有大号;别的牲口每天一进一出,这驴几进几出。还有个不同之处:它有个铜铃铛,脖子下挂着,走起路来叮当响。
就要问了,啥驴这么特殊?就会答了,拉磨驴,专给女人当帮手,拉碾子拉磨,满耳朵张家长李家短。
这驴吃过百家饭,谁家牵去干活儿,都会喂些上好的草料。这驴也挨过百家揍,最窝囊的童养媳踢过它,最老的小脚老太捶过它,连刚会走路的淘气娃娃,也在它蹄子上撒过尿。早先这驴每天都要患得患失几回,一会儿觉得自己重要,一会儿又感觉自己卑贱。它的毛病在生产队来了另一头骟驴那天,忽然就好了。它去拉碾子,不再懒洋洋。路过村里小破庙,不再东张西望。路上遇见红事,不再斜着眼偷看新郎的大红花。遇上白事,驴脸也能挂出一脸悲伤。谁喂它吃草,它就用柔软的鼻子去蹭人家的手。没多长时间,后来那只骟驴又被带走了。
就这样,生产队的拉磨驴一直都是它。驴的木槽子上刻着几个歪扭的字:为全体社员服务。
这头驴有个癖好。它干活时不叫,走路时不叫,专门在傍晚收工回来,老半天不迈单间儿的门,可地打滚,嘴里“咴儿咴儿”地一个劲儿叫。就为这,到它老死,留在韩屯的大号没变过——叫驴。
叫驴走后第二年,生产队解散了。韩屯家家又有了地,队里的牲口也被分了个七零八散,有三家分到一头牛的,也有四家分到一匹马的。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种地又离不开牲口,牛鞅子、马鞭子自然都成了稀罕物。张三家捞着了,李四家没捞着,火药味儿就往外冒。分到最后争抢起来的正是叫驴脖子上那个铃铛。许是起初觉得小,不起眼,许是大伙儿都盯着大物件抢,总之最后没啥可分了,才想起还有个铃铛。就为这副驴铃铛,一帮人从生产队屋里吵吵到院儿里。
一个脑瓜尖尖的瘦高个子说:“那驴,一直我喂,对我多有感情就不用说了吧?单说这铃铛,要不是我护着,那年不就扔炉里炼钢炼铁啦!”这人叫郑万山,原先是生产队饲养员。屯里人说到他,不管说的啥,临了总会带上一句:“那姓郑的可是牛角上抹油——又尖(奸)又滑呀!”
郑万山话音刚落,另一个说道:“要这么说,这铃铛最早可是我入社时带进来的,你知啥是物归原主?”说话的叫韩富贵,四十开外,浓眉大眼却含胸佝背。不过嗓门儿煞是洪亮,人称“韩屯第一穷”。韩富贵这话不无道理。入社时,是他牵来一头青骡子,这铃铛就在那头青骡脖子上。
韩富贵仨闺女,没儿子,家里有个病婆娘。他媳妇先天哮喘,除了嘴巴不饶人,身子骨要多糠有多糠。韩富贵身子也不瓷实,胎带的风湿病,关节全都变了形。他家也分了几垧地,可惜种不动。舍不得过去的生产队,可惜又回不去。
郑万山就不服了:“韩富贵,少耍埋汰——你说的那是哪年月的事?”
韩富贵更不服:“耍埋汰谁能耍过你?你咋当的饲养员,谁还不知道?”谁都知道饲养员是队里挣工分最多的,但棒劳力当不上,郑万山当年从山坡上滚下来,一瘸一拐了半年多,就当上了。一提这话茬儿,郑万山鼻子沟都泛白,眼看着汗就要冒出来。韩富贵身边站着的老铁匠,这时赶紧拍了拍韩富贵肩膀,说道:“富贵呀,说铃铛,你不是想要铃铛?”韩富贵从不跟老铁匠斗嘴,又说回了铃铛:“我不要,谁也不要。我一要,全都想要。都他妈的——眼皮子浅、腚沟子深!”
院儿里又是一片七吵八嚷。
一个鼓眼珠子的老头,嘴巴松开烟袋锅,像是鼻子里哼了一声,对老铁匠低声说道:“他们几个,争啥争呢?要那么论,这铃铛最早是人老阚家的。”这老头姓庞,脖子上有个瘿袋。
“老庞头,你个老粗脖儿,”韩富贵不光嗓门儿大,耳朵也机敏,冲着老庞头嚷,“分老阚家浮财那前儿你多大?三四十有吧?我才十来岁,咋还没我有记性?那头青骡子不是分给我家了?”老阚家是当年第一大乡绅,家财万贯,整个东山都是他家的。斗阚大地主最积极的就是韩富贵他爹,分财产分得最多的,也是韩富贵他爹。
老庞头被损得灰头土脸,举着烟袋锅,不敢吭气儿了。这人平时话挺少,老两口儿拉扯个外孙子,名叫庞大海,日子紧巴巴。倒是郑万山,心也不服嘴也不服,又戗戗道:“韩富贵,你嗓门儿大,你倒是问问铃铛那物件儿,它想跟谁?”
院儿里舞马玄天,正在难分难解,村小学左校长走了过来。迈着四方步,不紧不慢。
左校长细眉细眼,架副眼镜。走路挺胸抬头,颇有几分文气。怪就怪在常年只戴一只套袖,有时藏蓝,有时墨绿,弄得总有一只胳膊失真。那天他左胳膊一半浅灰(衬衫是灰的)一半藏蓝,抬起来扶了扶眼镜,站住了。
“乡里乡亲的,大家不要吵嘛!”
“左校长,来得正好,您给评评理,韩富贵是不耍埋汰?”
左校长温和地笑了笑,“多大个事儿,说来听听。”
“嘻,屁大个事儿。”郑万山儿子叫郑四方,正在村小念书,数他最知道见啥人说啥话。
“你个孬种!左校长,斗大个事儿。”韩富贵脾气直,总说自己下辈子再起名就叫韩正义。
“说说看,松花她爸。”韩富贵大闺女叫韩松花,也在村小念书。韩富贵跟谁都敢耍驴,就跟两个人不耍:一个左校长,一个老铁匠。要不是这位左校长,韩松花怕是连学都没的上。每学年那五块钱学费,在老韩家是天大个数。眼瞅着别人都上学了,韩松花跪在地上,央求韩富贵让她也去上学。韩富贵差点把牙咬碎,骂了半晌,出门去找了左校长。见了面先骂自己混蛋,明明养不起,还一个接一个,连生了三个。生完又塞不回去,连五保户都没资格申请。两口子像俩废人,一丁点来钱道儿也没有,每天太阳一出来就愁,月亮挂头顶时继续愁。左校长知道他家啥样儿,二话没说就去大队开证明,又是申请又是上报,韩松花的学费一分也不用交了。韩富贵一琢磨,老二老三离上学也不远了,就把那两个减免学费的事,提前对左校长千恩万谢了一番。左校长最怕村里哪个娃没学上,韩富贵等于用自己的娃戳了左校长的软肋。校长答应了——万一申请不下来,那俩娃学费,他从工资里掏。
韩富贵围着左校长转了五六圈,抢铃铛的事才算说清楚,正要继续转,有人受不了了。
“韩富贵,你让叫驴附体啦?那是左校长,你当磨盘啦?”
有人哄笑,有人加纲,说叫驴回来了,给自己转迷糊了。韩富贵借这话表现出一副勃然大怒的样儿,抓起拴着铃铛的绳套,二话不说,自脑瓜顶一套,叮叮当当,把自个儿拴住了。
“松花她爸,你这气性,还真是挺大。”左校长到底有文化,憋住了,仅带一丝微笑,别人没这功夫。一时间,老榆树的荫盖里没了好动静,大笑声连成片,听着像野鹅狂叫。韩富贵丢了面子,却捞到了实惠,象征性地又喊了两嗓子,两条腿一高一低,把自己拐回家去了。
这位左校长不是别人,正是我爸。他回家学抢铃铛那件事时,我七岁,读村小一年级,跟韩松花、郑四方还有老庞头的外孙庞大海一个班。我爸那天说完那事儿,加了句总结:“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有矛盾就需要有解决矛盾的人。”我觉得我爸有吹嘘他自个儿的成分,我妈说那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我想,既然是通病,我爸肯定也得上了。不过我还是抱了一线希望,问我妈:“所有通病都有疫苗吗?”我妈以会计对待账本的认真态度对我说:“哪能呢?我听说外国有个什么滋病就没疫苗!”我对我妈的回答不太满意,又说不出不满意在哪儿,于是又问:“妈,你算知识分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