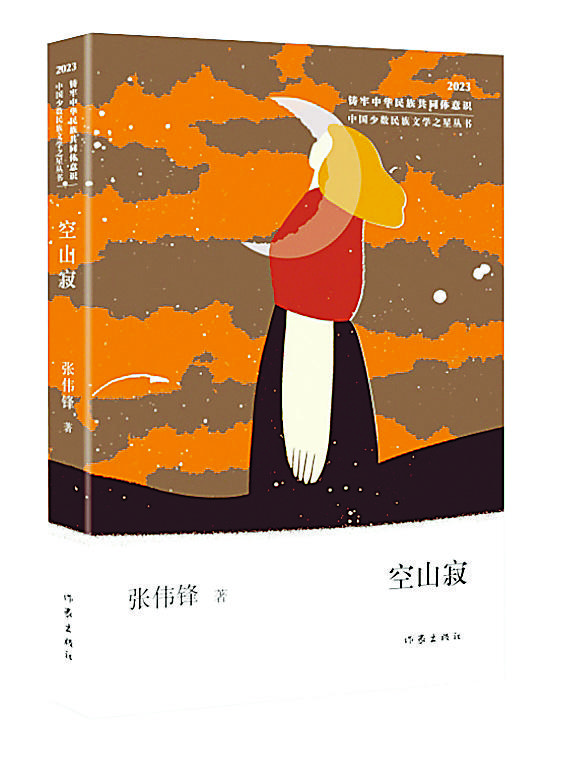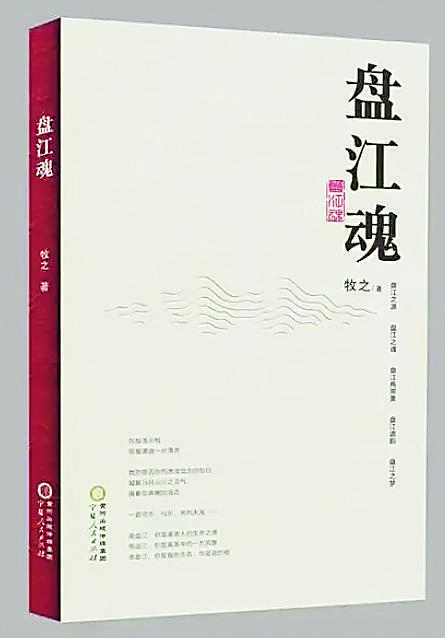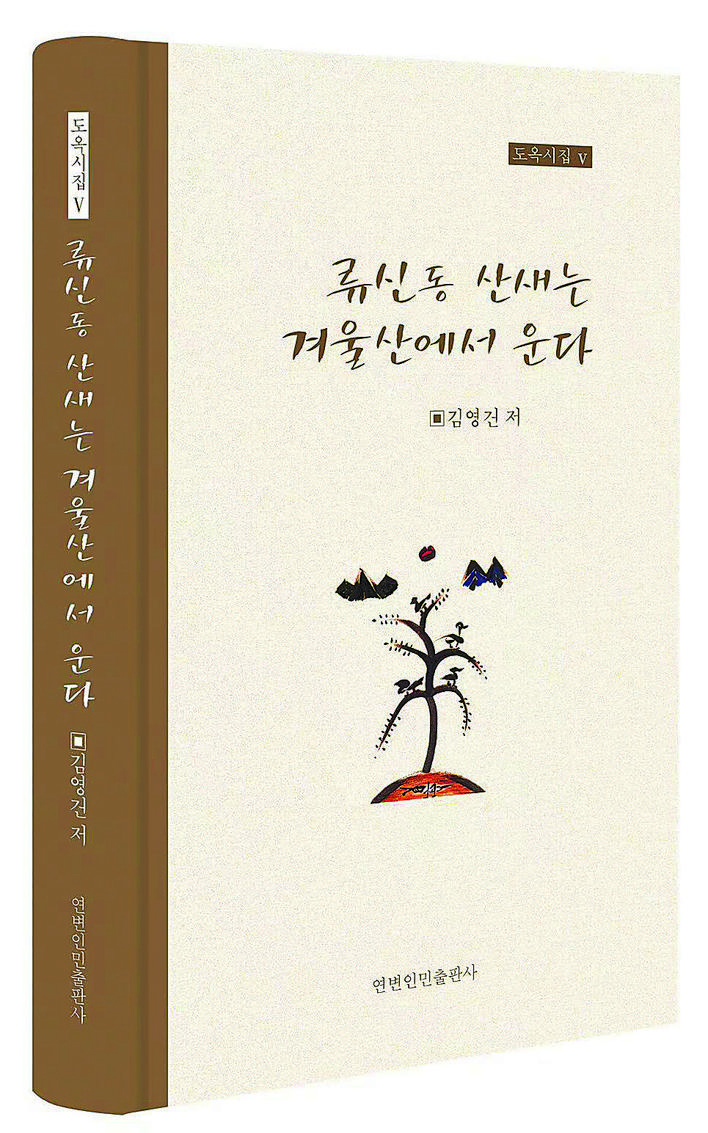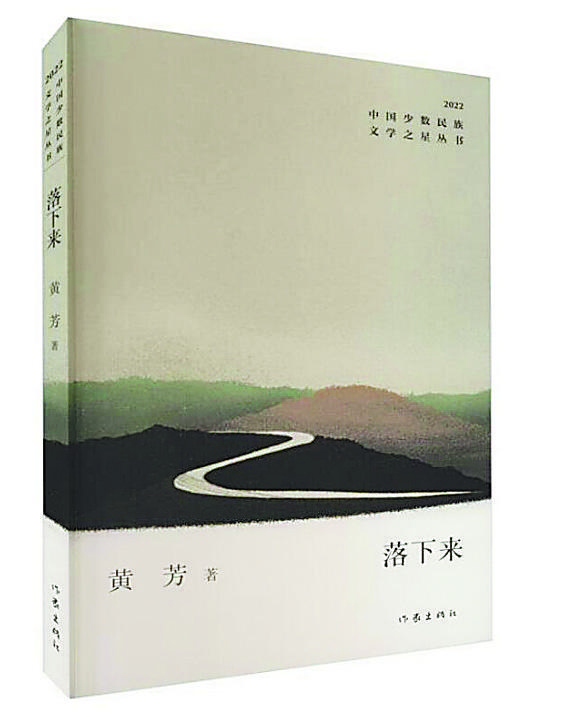□霍俊明
少数民族诗人的96部诗集参评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其中民文作品10部,参评诗人涉及20多个民族。它们整体反映了2020年至2023年四年间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和多元文化景观。这些涉及生命、文化、区域、历史、民族、宗教的诗歌带有向传统致敬的本源性特质。这些来自不同民族、区域的诗人,通过异彩纷呈的诗歌文本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成为万古星辰与大江大河。
民族历史、区域文化、族裔信仰、属地性格、精神图谱、地方性知识在当前的少数民族诗歌中被反复抒写,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这些精神向度和文化载力变得愈发重要。具体到个体主体性以及创作个性来说,每一个民族诗人又从情感、经验、语言、技艺等方面提供了差异性的多元化空间。这些充满难度与可能性的民族之诗、时代之诗、现实之诗、命运之诗为当下少数民族诗歌繁荣带来持续的活力与深刻启示。
很多少数民族诗人自觉地沿用了民族特质和文化元素,在一部分诗人那里,“诗”与“歌”比肩同在、相互融合。这些诗人站在雪山之巅、白云之下、草原之上、河流之侧、火塘之畔展开喉咙歌唱,词语搭载音乐的翅膀飞翔或低缓掠过。朝鲜族诗人金荣健的诗集《鸟声呖呖鸣冬山》在民文作品中最终脱颖而出,其独特的抒写方式、深沉的情感、动人的旋律反映了朝鲜族诗歌的特殊魅力,有力印证了当代民族诗人对悠久诗歌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再造。
此次参评作品文体多样、风格繁复,现代诗、古体诗词、散文诗共生发展,长诗、组诗与短章彼此辉映。在写作的碎片化、无方向感越来越突出的写作情势下,优秀的诗人必须具备总体化的视野和写作襟怀,而长诗就成为诸多诗人的选择。对于当下少数民族诗歌的发展而言,长诗总是能够在超大的精神体量、思想载力、繁复结构、内在机质、修辞技巧等方面展现厚重、深邃、大气的艺术魅力,能够在宏阔视野中更为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和诗学的诸多命题。以布依族诗人牧之的《盘江魂》等为代表的长诗体现了少数民族诗人在融合民族、地方、历史和时代方面所做出的可贵探索。在抒情、叙事、摹写、还原、想象的合力参与下,诗人通过对“民族史诗”梦想的书写实践,体现了对“总体性写作”诗歌美学的追求与抱负。《盘江魂》分为序诗、正文、尾声三个部分,主体分为盘江之源、盘江之魂、盘江两岸美、盘江遗韵、盘江之梦五个部分。牧之笔下的盘江是宏阔的、激荡的、高扬的、深情的、繁复的。这条江是诗人的记忆之根与生命之魂,是诗人的精神出口和来路,是古调和新声交织的和声。北盘江、南盘江已然成为地方性知识的诗化档案,成为新时代的精神场域。它们对应的不只是自然、地理、生态、物象、事态,更涉及对生命、故乡、祖先、族裔、原型、历史、民俗、文化以及现实新变的深沉思考与深情礼赞,“我们内心的悸动,在一场暴雨之后/把祖先们遗留的缆绳一拉/所有的痛苦不再拖泥带水/所有的回忆都布满我们无言的迷宫/而岁月的此时此刻/正在高原之巅,在盘江两岸/追赶滔滔江水,不舍昼夜……”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少数民族诗人一次次写到了祖国大地上的河流。千百年来,河流在很多伟大文学作品中成为文明、历史、民族、故乡的化身与象征,成为流淌不息的精神母体与生命之源,成为波澜壮阔或静水流深的寓言,正如佤族诗人张伟锋所抒写的那样,“这些年来/无论是在上游的金沙江,还是在下游的澜沧江/我曾几次说起,要在夜里/在江边听一听水流的声音”(《夜色变深了》)。在诗人这里,水既是元素化的又是生命性的,既是感受性的又是想象化的,它是各种质素综合在一起的精神共时体,也是诗人保持个体主体性前提下盘诘、对谈和深度参与的复调。水的流淌、奔涌、漫溯与精神主体性的漫游、迟疑和伫望形成了主客对应关系,其间既有对立也有融汇,既有真相也有幻象,既有现世也有彼岸,既有永恒也有瞬间,既有斑驳命运感也有时间前景的瞻望。
“大诗”“史诗”性质的文本既可以是鸿篇巨制,也可以经由诸多“小文本”最终累积、转换和提升而成,所谓积沙成塔是也。
出生于云南临沧市永德县的佤族诗人张伟锋是目前国内青年诗人群体中的优秀代表,他的诗歌安静、内敛、深沉、盘桓、真挚,当然也有孤独、裂变、空寂、虚幻之感,这正如他身后绵延起伏的佤山一样。永德地区山谷多样,深切亚高山宽谷、深切中山宽谷、深切中山窄谷、中切中山宽谷、中切中山窄谷使得佤族儿女形成了沉静多思、踏实勇毅的地方性格,“高山之上,力度相同的两场雨。一次完成/生命催生。一次完成,对野草的暗杀。我像个路人/我看见,并见证这一切”(《佤山之雨》)。在不事张扬的性格以及收放自如的文本风格中,张伟锋的诗歌充满张力与内蕴,充满效力与活力,充满难度与可能性,充满磅礴之气与新见之力。在诗集《空山寂》中,张伟锋是一个田野考察者和坚执的返乡者。他以松弛、平静而又深入、精简的笔调抒写出云南边地空间的内在构造以及精神原乡机制,穿透表象对携带显豁的文化元素的地方、空间、物象予以重新发现、叩访、勘测。与此同时,佤族的诗歌文化传统在张伟锋这里得到深沉回响与有力印证,歌唱与叙事交织,外放与内收平衡,感性与智性兼顾。张伟锋的诗歌镌刻了丰富的精神肖像和地方胎记,在对现实、城市空间的观照中携带了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以及求真意志,在对生活、情感、自我、命运、乡土、城市的深度探询与诘问中展现出独特的语言魅力与精神重力。
以那萨(藏族)《留在纸上的心》和黄芳(壮族)《落下来》为代表的女性诗歌在情感、经验、智性的表达以及性别、思想、文化的观照上更为注重个人性、内在化且不乏张力的静水流深式的表达。
在那萨这里,由于藏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她更为关注自我和生活背后那些幽微不察的命运、未知空间以及精神世界。她的诗歌总是让我们看到关于自我、生命以及万物寻求觉悟和自在的过程。由此,诗歌成为生命诗学的载体,成为特殊的精神信使。隔着世事的幕布和时间的栅栏,信使正在朝向诗人这一边走来。那萨低缓的语调、虔敬的表情、自在的内核、俯身向下的凝视以及深沉幽邃的精神空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凝恒、深思、精敏、细密、幽微的内视者,不断化除执念的觉悟者,不断挣脱肉身的冥想者,不断涉渡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朝圣者。那萨诗歌中的背景、空间是主体、自然与世界融通之后的精神、元素、原型的化身。这些化身又在日常化空间、自然环境以及冥想型的深邃文化情景中对应于一个个物象、心象与幻象,对应于真实不虚的情感、经验、感受的多棱镜,对应于生命中的终极问题与未解之谜,“雪山拉下雾色帷幕,我行走其中/像一件自由漏失的器皿/天因为放空而高贵了起来”。由此,个人命运、精神情势与地方知识、民族元素完成一次次的对话与融合,诗人的生命意志力和包容的襟怀也由此得到磨砺与拓展。
黄芳与其他同时代女性诗人一样,一度在文本中反复强化女性的身份、经验、意识以及文化想象,她们通过理解、“扮演”、重组、建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来抵达“永恒的女性”,用文字试探命运的深浅。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一生都是在准备、创作、修改自画像,由此诗歌分担了自白、祷辞、安慰剂和白日梦的功能。在诗人与自我、事物、空间、元素的对话、磋商、盘诘中,我们看到,一个女性在不断地回望、面对、直视、打量、凝视中,过去时的我、此刻的我以及未来的我相互交织、彼此探寻。在《落下来》这本诗集中,黄芳的诗歌已经随着“中年经验”的到来,越来越专注于日常化的生存现场,以及不容回避的围绕家族展开的死亡意识。她也总是能在细节和幽微中激活出想象的闪电与低沉的雷鸣,能够在司空见惯的表象背后上演戏剧化的灵魂舞蹈。黄芳有些诗歌不乏紧张与锐利:“那天黄昏/我在报纸的空白处/写了一小行字:在风雨中/抱紧良知的骨头”。这再次验证了女性诗人天然携带的自白品质和自画像的质素。诗歌是精神能见度的产物,从而她们的写作也携带了深深的精神史的印记。
在阅读此次参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歌作品的过程中,从诗人与环境的深度互动来看,我们会发现当下一大部分少数民族诗人仍延续了抒写标志性的民族空间和标识化的地方景观的路径。这些空间、景观作为民族的文化元素、地方胎记、族裔信仰、精神资源深入到每一位写作者的血脉和记忆之中。这一类型化写作的空间优势是显豁的,这些意象、场景以及空间也携带了民族记忆的根系,写作的地基也是长久而稳固的,写作者在无形当中也获得了地方性知识的有力支撑。
在日常处境、地方元素、民族文化、母题意识与幽微内心、精神型构、命运主题、语言方式、修辞策略的深度对话与发现中,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闪现出异常动人的光亮。这些少数民族诗人印证了无论是宏阔的诗还是幽微的诗,它们都应该具有可贵的精神能见度和发现能力,具有发幽烛微的目光,具备打通更多人的精神共时体结构,具有将个体经验、现实经验、地方经验最终提升为民族经验、历史经验、人类经验的求真意志和写作能力。
对于所有诗人而言,他们最终一起站在了历史、文化、诗学以及现实、自我空间的复合体当中,接受读者、批评家以及时间法则审慎选择的精锐目光。
(作者系《诗刊》副主编,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