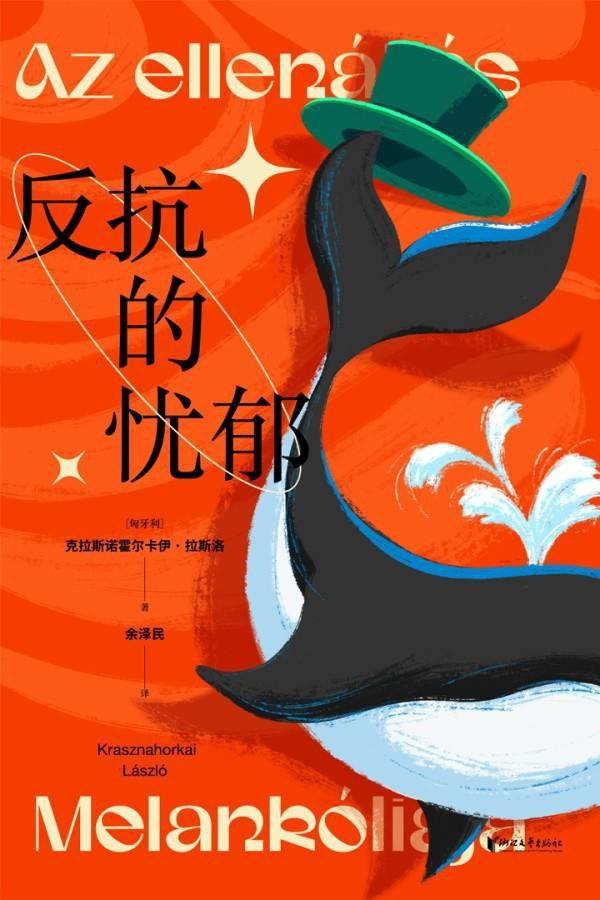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在完成《撒旦探戈》四年之后,又写出了《反抗的忧郁》(1989)。如果没读过《撒旦探戈》,人们肯定不知道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是谁,这部小说使他一夜成名。而一旦读过《反抗的忧郁》,人们又会猛然发现这位匈牙利作家的深刻与复杂,进而使其成为能够进入到匈牙利文学史序列的小说家。与前作相同,这部小说讲述的依然是一个关于心灵、政治、哲学和混乱、失序、欺骗的故事:远道而来的“鲸鱼马戏团”驻扎在城里的科舒特广场,为城市带来一系列奇怪异象的同时也使之弥散着关于暴力的传说,可悲的是,传说终成现实,小城里的人因为迷失在马戏团领导者“王子”的谣言和谎言中,打破平静,发动暴动,使城市的一切都成为废墟,虽然暴力终被制止,但是小城里的人们也都深陷心灵的枯井。
作为短语的“反抗的忧郁”
这显然又是一部使读者很难理解的小说。所以阅读《反抗的忧郁》,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作为短语的“反抗的忧郁”,是一个定中结构还是一个述补结构?换句话说,是“反抗”修饰“忧郁”?还是“忧郁”补充“反抗”?如果不一点一滴从细节入手对小说进行文本细读并归纳出这部小说的诠释学意义,似乎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小说第一部分的题目是“紧急情况”。不由得使读者发问:是什么“紧急情况”呢?这部分用极为精细的笔墨讲述了弗劳姆夫人乘车返乡的场景,堪称照相机现实主义的典范。下车之后,她穿过市区,看见一张关于“世界上最大的巨鲸”的广告牌,与此同时感受到了城市的异样。这位善良且屡遭厄运的女人回到家中,小说的重要人物艾斯泰尔夫人就来找她,希望弗劳姆夫人的儿子能够通过个人情感“唤醒”她丈夫艾斯泰尔先生以“拯救”城市,遭到拒绝后艾斯泰尔夫人自尊心受到伤害,第二天早起又亲自来请弗劳姆夫人的儿子,即小说的主人公瓦卢什卡。小说的第一部分像是一个引子或楔子,看似无厘头或没有意义,但是却在有意无意间介绍了几乎每一位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关系,而所谓“紧急情况”无疑是指“鲸鱼马戏团”带给整个城市的异象。在这里,拉斯洛显然为小说埋下了深沉且神秘的伏笔,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欲罢不能。更重要的是,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开篇部分,在艺术上延续着与《撒旦探戈》一样的独特风格。
长句子已经成为拉斯洛的文学标签,以至于在《反抗的忧郁》的第一页,就出现了长达八行的超长句,这固然存在匈牙利语作为较难习得语言语法本身的原因,但同时拉斯洛将这种语法发挥到了极致,他似乎深知,只有长到极致的句子才能使故事“慢”下来,并降低读者的阅读速度,进而在诠释学的意义上使小说更为深沉。虽然距离《墙上的斑点》《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几近70年,拉斯洛依然秉持着20世纪以来意识流小说的古老传统,不厌其烦地呈现出小说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无论是内心独白还是叙事者主观上任由小说人物的思绪无边无际地绵延,都致力于通过心灵跃动的细节构建他们的内宇宙。所不同的是,拉斯洛笔下的人物大多离奇而古怪、抽象且多义,意识流恰恰能够强化这种复杂性,使小说人物具有很强的诠释学意义。小说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性格和个性使他们呈现出某种不可言说或描述的“高深莫测”,话语的能指和所指看上去都另有所指,意识流和内心独白更加深了这种神秘的张力。不仅如此,在洋洋洒洒的长句子中,拉斯洛以一种格式塔心理学中“填空”或“留白”方式“讲”故事,使小说形成若隐若现的故事和情节,而且内中布满了令人不解甚至费解的“玄机”,使读者不得不翻动书页,继续阅读。
小说第二部分名为“韦可麦斯特和声”,是小说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拉斯洛似乎忘记了小说的楔子,而重新入题。主人公瓦卢什卡在小酒馆引导众人表演太阳系的天体运动直到后夜,然后经车站、广场回家,见到来请他帮忙的艾斯泰尔夫人。作为艾斯泰尔忠实的门徒,瓦卢什卡来到艾斯泰尔家,并和后者一起走向科舒特广场,看到因“鲸鱼马戏团”而窃窃私语的人们。出于好奇,瓦卢什卡开始偷听马戏团团长关于“暴动”的呼吁,不得不因为恐惧将“预言”通知给大家。与此同时,艾斯泰尔像是先知一样封起自己家里的门窗,并进一步思考世界的意义和价值。暴动开始,瓦卢什卡不知不觉参与其中而变得身心俱疲,最终经哈莱尔指点与警察局长的两个儿子一起沿铁路逃遁。这部分的最后,艾斯泰尔苦苦找寻生死未卜的瓦卢什卡,被哈莱尔告知他的“仆人”并没有死去。
毋庸置疑,这部分是《反抗的忧郁》的重中之重,正因如此,匈牙利电影导演贝拉·塔尔才直接以“韦可麦斯特和声”为蓝本对小说加以改编并完成了他的长镜头杰作《鲸鱼马戏团》。然而就像法国思想家朗西埃声称《撒旦探戈》“除了一场骗局一无所有”一样,读过《反抗的忧郁》的第二部分,也能微微感觉到这部小说的故事或情节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作家经由小说或故事对人物尤其是他们内心世界的文本指向。这是因为,拉斯洛无意长篇大论地言说小说的情节,而是在情节和情节的关联处用大量的笔墨刻画小说中的人,这种“刻画”不是表现,也不是再现,而是一种对人物人格、性格、思想和头脑的诠释,或者说类似一个关于人物的注释,以更全面立体地介绍小说中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抗的忧郁》甚至可以被看成是一部“脚注小说”:情节是海明威“冰山理论”中的1/8,而注释是另外的7/8。具体言之,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无疑是艾斯泰尔和瓦卢什卡。
艾斯泰尔是一位钻研音乐的隐遁校长形象,也是小说中的先知,他能够看穿一切,但在主观上却因为对世界的认识与大部分人格格不入而与社会断联,究其根本,是因为他认识到,“世界上既不存在最后审判,也不存在世界末日……这种事根本就没有必要发生,因为一切都会自行衰败,走向毁灭,以便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然后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下去,事实毫无疑问将会这样发生,就像我们无助地在宇宙中转圈:一旦开始,就不可能停下来。”这种带有反基督教色彩的言论与尼采的“上帝死了”如出一辙,既是对小说事件走向的预言,又是对世界走向、社会变迁、历史循环的判断。相比之下,瓦卢什卡是年轻的送报员,虽然时常接受艾斯泰尔的“洗礼”,看上去应然成为他的门徒,但是实际上他思维发散、缺少主见、人云亦云,他的母亲善良温柔,他的导师博学真诚,本应该正义且有定力,然而他也在不知不觉间被暴动的洪流裹挟,走上不归路。这种处理方式使他成为千千万万人的象征,拉斯洛想向读者传达的是,在“事件”面前,普通人往往普遍盲从。虽然这是瓦卢什卡的个人选择,但是却代表了人们在历史选择面前的“集体无意识”。
小说第三部分名为“墓前致辞”,是大结局:暴乱被制止;一位当事人发表长篇大论回忆事件的经过;弗劳姆夫人在打砸中去世,故事在她的葬礼中结束。这部分的特点在于,省略了暴徒“打砸抢事件”的政府处置环节,使小说直接来到了故事结尾。如果说拉斯洛在之前的描述中采用某种“重”的策略,那么这部分他则将策略转换为“轻”,如译者余泽民所言,这部分“留下了尘埃落定后的喑哑”。艾斯泰尔夫人在小说结尾处摇身一变,成为女书记,名望“将她推到了反抗运动的领袖位置”,拉斯洛也暗戳戳地告诉读者,这一切背后其实也充斥着阴谋和谎言,“鲸鱼马戏团”的“团长”招摇撞骗,而战胜“鲸鱼马戏团”的女书记同样招摇撞骗,所谓的“骗局”颇有向《撒旦探戈》致敬之意。遗憾的是,小城并没有因为“暴乱”被制止而存在任何向好的迹象,一将功成万骨枯,艾斯泰尔夫人虽然赢得上位,其代价是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黯然落幕,而且,城市从毁灭走向新的毁灭。小说最后,拉斯洛用长达五页半的篇幅完成了弗劳姆夫人尸体的化学分解描述,使她所含全部原子再度按热力学第二定律回归自然。如果说人的血肉是一座帝国,那么到了最后,尘归尘,土归土,恰然印证了艾斯泰尔关于世界与生命的预言。
穿过语言与思想的屏障
回过头来会发现,《反抗的忧郁》所讲述的故事极为简单,混乱与失序背后无非是小人物在历史和政治的洪流中何去何从的问题。由此而观之,即便反抗之后,带来的仍是无边无际的忧郁,因为反抗之后,依然存在其他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反抗的结果是忧郁,“忧郁”成为“反抗”的结果补语。“反抗”和“忧郁”,作为故事的进程和结果看上去都颇为简单,而在故事之外,拉斯洛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和策略将《反抗的忧郁》中的人物、思想、意义形塑得极为复杂,使这部小说成为具有很强阐释学意义的复杂文本。一个看上去简单实际上很重要的问题是,拉斯洛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冗长、多义且复杂的小说呢?或者说,《反抗的忧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从思想上说,拉斯洛想要通过《反抗的忧郁》告诉读者,世界的无序状态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而且是一个天然的循环,没有必要因此而悲观。自1882年尼采大声疾呼“上帝死了”之后,西方以基督教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渐渐瓦解,一战、二战、冷战在之后的100年里加速了这种瓦解,及至拉斯洛完成《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的时代,他已经深深意识到历史的不断循环,而且在这种循环中,世界的意义往往被消解。因此,在这部小说中,读者既找不到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人,又找不到具有终极意义的世界。一方面,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福柯《疯癫与文明》中所谓的“疯癫诸相”,超越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人物设定本身就给世界带来了某种不安的因素,他们反抗,他们忧郁,他们成为那个混乱世界和时代的最小单元,理性不复存在,秩序随即湮没。另一方面,由人物构筑起来的社会和世界同样难以理解,在这个如世界末日般凄凉的城市,天气寒冷、异象不断、色调幽暗、关系凉薄,人们不知道已经、正在、将要发生什么,无论城市有无政府管理或经营,都已经处在失去控制或自控能力的边缘。在拉斯洛那里,“世界最本质的自然状态就是混乱”,小城的秩序俨然成为世界秩序的象征,尤其是在1980年代末期冷战行将结束的时代,而以冷战结束之后30年的世界经验回看,能够进一步发现拉斯洛作为小说家的政治敏锐性和历史洞察力。
从艺术上说,《反抗的忧郁》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拉斯洛在创作的过程中依然将小说创作视为一种文学实验,在遥远的1989年,这种实验在东欧国家非但没有过时,反而相对先锋。纳博科夫在言及《包法利夫人》时曾言,“世间从未有过艾玛·包法利这个女人,小说《包法利夫人》却将万古流芳。一本书的生命远远超过一个女子的寿命。”在指出《包法利夫人》不朽的同时也揭橥了小说与想象的互文与互洽关系。其实,拉斯洛洋洋洒洒用几十万字虚构一个本不存在的“事件”本身也在践行“文学即想象”的古老箴言,比如,弗劳姆夫人乘火车回家的场景之所以被他描摹得如此细致而深刻,就是在通过巴尔扎克式的真实性建构这种想象。此外,受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及其惯性的影响,拉斯洛同样在小说中运用了诸多后现代主义创作观念,比如象征和隐喻的修辞格,水塔摇晃、教堂异响、老树倒伏,都与《圣经》中世界末日的场景颇为相似,无疑是对小城新旧时代更迭的隐喻;再如小说中存在诸多用以阐释文本并被加上括号的长句子,在形式上增强了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张力,又凸显出文本的多义性和复杂性。这些并非孤例,但却都在使拉斯洛成为匈牙利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同时塑造着他自己的文风。
几百年来,从塞万提斯到巴尔扎克,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加缪,小说从某种意义上变得越来越复杂,抛去其自身发展的自律性,即便是与历史、社会、哲学及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也能推进这种复杂性。以此为理论支点,不难理解拉斯洛小说的复杂结构和思想,他一方面继承了中东欧文学的隐秘传统,思考这片土地上因历史和社会原因所产生的断裂问题;一方面将自己对文学和时代的理解深深嵌入到文本深处,建构具有极强个性化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世界。对于读者来说,拉斯洛的复杂性为阅读带来了诸多不适和困难,以至于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穿过一道又一道语言与思想的屏障,才能最终抵达小说的终点。阅读复杂如拉斯洛《反抗的忧郁》样的小说,既需要面对文本的勇气,又需要任劳任怨的态度,还需要抽丝剥茧的耐心,惟其如此,阅读才能长久,创作也才能永恒。
(作者系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