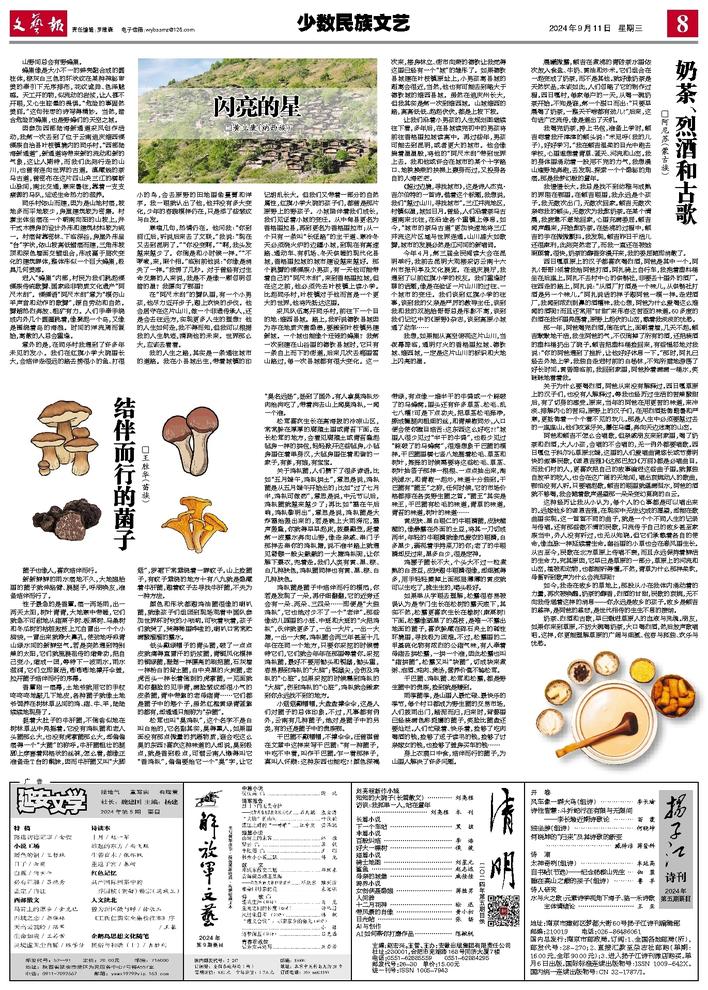晨曦微露,额吉在煮沸的青砖茶水里依次放入食盐、牛奶、黄油和炒米。它们组合在一起变成了奶茶,而不是其他。就好像奶茶是天然饮品,本该如此,人们忽略了它的制作过程。西日嘎村,每家每户的一天,从喝一碗奶茶开始。不知是谁,第一个脱口而出:“只要早晨喝了奶茶,一整天干啥都有劲儿!”后来,这句话广泛流传,像是道出了天机。
我喝完奶茶,挎上书包,准备上学时,额吉吻着我汗津津的额头说:“米尼呼(我的儿子),好好学习。”我在额吉温柔的目光中跑去学校,心里遐想着青草、蓝天、河流和山峦。我的身体里涌动着一股用不完的力气,我想漫山遍野地奔跑,去发现、探索一个个隐秘的角落。那是我梦幻般的童年。
我慢慢长大。我总是找不到幼稚与成熟的界限在哪里。在额吉眼里,我永远是个孩子。我无数次出门,无数次回家。额吉无数次亲吻我的额头,无数次为我熬奶茶。在某个清晨,我疲惫不堪地回家,心里充满委屈。额吉闻声醒来,开始熬奶茶。在扬沸的过程中,额吉的手在微微颤抖。我发现,额吉昨日干活儿还很麻利,此刻突然老了,而我一直还在被她照顾着。很快,奶茶的醇香弥漫开来,我的委屈随即消散了。
西日嘎草原上的汉子都喜欢喝烈酒,阿爸是其中一个。阿扎(哥哥)领着我给阿爸打酒。阿扎骑上自行车,我抱着塑料桶坐在后座上。阿扎不去村中心的供销社,非要去十里外的酒厂。往西走的路上,阿扎说:“从酒厂打酒是一个味儿,从供销社打酒是另一个味儿。”阿扎说话的样子跟阿爸一模一样。走进酒厂,我闻到浓烈刺鼻的酒糟味。我心想,阿爸为什么爱喝这么难闻的酒呢?而且还常用“甘甜”来形容这苦涩的味道。60多度的烈酒在我怀里晃荡着,原野上起伏的山峦,载着我淡淡的忧愁。
那一年,阿爸喝完烈酒,倒在炕上,面朝着墙,几天不起。额吉默默地干活,我生阿爸的气,不仅倒掉了所有的酒,还把装酒的塑料桶扔出了院子。额吉把塑料桶捡回来,有些愠怒地对我说:“你的阿爸遇到了挫折,让他好好休息一下。”那时,阿扎已经去外地上学。我独自走进村前的白杨林,不知所措地游荡了好长时间。黄昏降临前,我回到家里,阿爸拎着满满一桶水,笑眯眯地看着我。
关于为什么要喝烈酒,阿爸从来没有解释过。西日嘎草原上的汉子们,也没有人解释过。等我也经历过生活的苦辣酸甜后,有了切身的感受。原来,当年的阿爸在用更苦的味道,来冲淡、排解内心的苦闷。原野上的汉子们,在用烈酒抵御酷暑和严寒,更抵御着一个个看不见的坎儿。那是人生中必须要越过去的一座座山。他们咬紧牙关,攥住马缰,奔向天边迷离的山峦。
阿爸和额吉不怎么会唱歌,但亲戚朋友来到家里,喝了奶茶和烈酒,大人小孩,会唱的不会唱的,无一例外都要唱歌。西日嘎位于科尔沁草原北端,这里的人们爱唱曲调悠长或节奏明快的叙事民歌,《诺恩吉雅》《达那巴拉》《万丽》都是必唱曲目。而我们村的人,更喜欢把自己的故事编进这些曲子里。就算独自放羊的牧人,也会在这广阔的天地间,唱出哀婉动人的歌曲,哪怕没有人听。只要唱起歌,额吉的眼里就蕴满泪水,阿爸的酒就不够喝,我会随着歌声遥望那一朵朵变幻莫测的白云。
这种经历让我从小认为,每个人的心事都是可以唱出来的。远嫁他乡的诺恩吉雅,在现实中无法达成的愿望,却能在歌曲里实现。这一首首不同的曲子,就是一个个不同人生的记录与传唱。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民歌,只流传于自己的故乡甚至家族当中,外人没有听过,也无从知晓。但它们承载着各自的使命,像血脉一样延续着生命。幽谷里的小草也会在春风里生长。从古至今,民歌在北方草原上传唱不衰,而且永远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究其原因,它早已是草原的一部分,草原上的河流和山峦,植被和动物,也都能听得懂。不然,青草为什么那样柔软,母畜听到歌声为什么会流泪呢?
如今,我走在故乡的草地上,那股从小在我体内涌动着的力量,再次被唤醒。奶茶的醇香,烈酒的甘甜,民歌的哀婉,无不向我传递着这样的消息——你永远是故乡的孩子。故乡是额吉的慈祥,是阿爸的慈悲,是世代相传的生生不息的接纳。
奶茶、烈酒和古歌,早已融进草原人的血液与灵魂。朋友,如果你来到草原,不妨大碗喝奶茶,大口喝烈酒,然后放声歌唱吧。这样,你更能理解草原的广阔与细腻、包容与孤独、欢乐与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