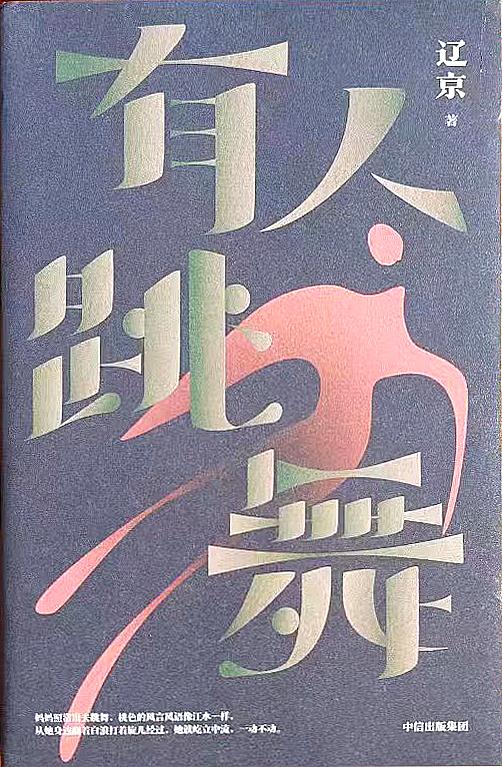小说就是要写平常我们不说的,或者说不清楚的那些话
李婧婧:辽京你好,首先祝贺《白露春分》出版。小说的一个核心关键词是“衰老”,我们现在已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在家庭中,如何赡养老人也成为中国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白露春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也好奇,你为什么会把“衰老”作为这部长篇的核心?
辽 京: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是一个终极的问题。人类的共通点已经不多了,死亡是其中之一,对所有人而言这都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永远说不完的。
我自己也曾面对过亲人衰老和去世。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听说和亲眼所见是完全不同的,死亡会在生者的记忆中留下痕迹。对我来说,写这个故事也是回顾这些痕迹的时候。
衰老和成长一样,都是一个迷茫又漫长的过程,是人生的原路返回,风景却完全不同了。关于成长的故事有很多,一个年轻人怎样碰壁,迷茫,痛苦,最后成长了,但是衰老似乎更少被提起,不知是否因为作家总是在壮年写作,总是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衰老总是显得遥远,而且并不美好,不像青春有着说不完的灿烂故事,衰老在每个人身上都是相似的。在生活中,死亡是一个禁忌话题,我们很少能够认真地、不带恐惧地谈论死亡,遑论那些通向死亡的衰老的细节,小说中有许多这样的细节,身体的感受,心理的感受,旁观者的感受,都说青春的肉体是有热度的,其实衰老也有温度,衰老会散发寒气,周围的人也会感知,但是总是避而不谈。小说就是要写平常我们不说的,或者说不清楚的那些话。
李婧婧:在阅读《白露春分》的过程中,我有一种巨大的震动感,你在非常日常的环境、非常平凡的个体中写出了生活惊心动魄的、不为人知的一面,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但实际上你写的是家庭里的暴力、人心的四散和生活的溃败,就像你在后记里写“一松手他们就要滑落下去,滑向死亡或者别离”,那么我想问,你如何看待生活的表相和本相?
辽 京:我觉得生活不分表里,只是生活本身。谜题和答案其实是同时出现的,只是常常被我们忽略了。这本小说有很多在时间线上回溯的部分,所谓的真实,其实是一种记忆中的真实,而人的记忆是会塑造现实的,同一件事在每个人的记忆中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模样。身处同一时空并不意味着面对同样的现实,人在此时此刻是非常孤独的,因为没有人与自己共享一份相同的记忆。
小说要呈现这种孤独,或者隔绝的生存状态,每个人都有不可避免的、朝着某个方向滑落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共同构成了一个家庭的拼图,没有大奸大恶,也没有大风大浪,只是一个普通家庭,每个人的困境也都是常见的困境,经济的,婚姻的,有些是时代的作弄,有些是个人的选择,秀梅的衰老就是在儿女离散、纷纷溃败的环境下发生的,她无声地衰退下去,其他人则是无声地消散,他们逃避自己的老母亲就像逃避一种可怕的现实。
李婧婧:小说最打动我的地方来源于你的诚实,诚实地面对生活、面对你笔下的人物,他们也许有各自的毛病和缺点,但也有他们善良、明亮的另一面,同时我也能感受到,你对小说里的人物抱有极大的温情,你写出了他们的困苦和不易,因此哪怕他们不完美,但他们让我们感到真实,仿佛他们就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人,你是如何塑造和理解你笔下的人物的?
辽 京:我希望他们是真的,在小说中,他们是真正存在的,作者和他们一样面对着他们即将到来的命运,并不比他们更有办法,和他们一样无奈,我是走在他们身边而不是在前面引领他们的人。
人物的塑造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他们是在写作中成型的,面对空白文档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也是一张白纸,小说是写出来,不是想出来的,这也是写作最有意思的地方,用文字去探索未知。这并不是什么玄学,而是作者的一种无奈,承认自己是无知的,眼前是白茫茫什么也没有的,才有可能和这些人物同行。从这个角度看,作者并不是上帝,只是一个傀儡。
因此,与其说真实,不如说自然,真实常常是不合逻辑的,现实生活是不按规律出牌的,但是小说叙事中的“自然”,是要这些人物有来处,有结果,人各有命,因果相应,各自承担各自的命运。其中秀梅的死是一早就注定的,读者和作者都知道,故事中的其他人也都知道,围绕着这个结果,许多故事情节就会沾上宿命的意味,死亡是已知数,那么其他未知数呢?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写到秀梅,就是朝着已知的终点前进,而写到佳圆、佳月和其他人时,是朝向未知的前途,这也和我们的生活经验是一致的,年轻人总有许多选择,而衰老只有一个结局。
一个写作者的“诚实”不是道德上的“诚实”,虚构就意味着要讲一些合理的谎话,是夸大和淡化,甚至无视一些现实,再真实的叙事也是裁剪过的,是作者的执念与偏见的产物,这是不可避免的。
衰老是无底的坠落,而成长是不停地向外逃离
李婧婧:小说里家庭的核心是秀梅,春天做槐花饼、炸香椿,夏天煮红豆、包粽子,冬天包饺子,这个家因为秀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讽刺的是似乎除了佳月没有人真正在意她的想法,她抓住机会就告诉儿女们“不要并骨,不要并骨”,但是最终在秀梅的坟前,儿女们只说那是秀梅的玩笑话,“哪有夫妻不并骨的”。看似是一个家庭主心骨、大家长,但大家只把她的遗愿当笑话,你如何看待家庭中隐形的暴力?
辽 京:与其说暴力,不如说是冷漠。暴力有一个特定的对象,使用暴力的人往往欺软怕硬,换一个对象说不定就变得温驯起来,而冷漠不是这样,冷漠是对周围人与环境的漠不关心,看不到人的复杂,只活在刻板的观念和印象中,任何不符合这些既有习俗和规范的人和事都被忽略掉了,或者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不值一提的,秀梅说她“不要并骨”,是破坏了他们对这件事的刻板印象,他们眼里没有那个活着的真正的母亲,只有一个母亲的形象而已,这个形象必须符合传统习俗,所谓的“面子”。这种冷漠,便是一种隐形的暴力。
李婧婧:家庭中的暴力也指向权力结构关系,这是家庭生活中很难被看到的部分,因为被亲密关系包裹了。但实际上衰老的老人、年幼的儿女,他们在家庭中常常就是失语乃至失权的一方,你怎样理解这种隐秘的权力结构关系?
辽 京:在写作中,我不太想像做手术一样去剖析亲密关系之下的权力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批评视角,但是创作者过于清醒或者执着的话,可能会忽略掉生活本身的那种模糊,写作者不需要去分析,这些人物也不是为了体现权力关系而存在的,在他们的生活中,我们看到了这些结构的痕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权力关系,是流动的,文学是要先找到那种流动感,再去刻画一些有意义的瞬间。
在中国家庭中,老人占据着礼节上最受尊重的位置,实际上并非如此。大家庭生活在一起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没有共同劳作的土地,共同居住的房屋,只剩下薄弱的亲情和血缘联结,势必走向离散,儿女离散的过程中,老人被留下来,独自面对死亡。秀梅晚年的悲剧是因为她既处在传统家庭观念中的“长者”地位,又处于现实生活中的“弱者”地位,构成传统观念的生活方式早不存在了,维系亲子关系的只有真正的感情,而温情恰恰是这个家庭最缺少的东西。
在《白露春分》中,秀梅与她的两个孙女构成一个相对温暖的小宇宙,她们一起生活过,一起出游,是她们各自生活中的温暖记忆,是大家庭中相对弱势的三个人抱团取暖,直到一方的衰老和另一方的成长将她们分开。权力关系是一种描述家庭关系的方式,但是并不能包涵全部,人与人的关系是动态的、变化的,很难用笼统的方式去总结,更不存在一个标准范式,秀梅曾经是对佳圆和佳月有影响力的人,这种关系随着时间推移也在不断变化,衰老是无底的坠落,而成长是不停地向外逃离。
李婧婧:年初的时候你发表了一篇小说,《我奶奶的故事及其他》,小说里的“我”更喜欢爷爷,因为爷爷当过兵,见识过热血和真正的武器,是英雄一样的人,奶奶是沉默的,她总是在厨房,忙着做一顿又一顿饭,直到有一天奶奶早早起床到厨房烙了十三张饼,救护车来了,把她接走了。小说里写爷爷的故事说了千百遍,奶奶的故事却从来没提起,是空白的。我们总觉得战场、刺刀是史诗的符号,是宏大的、值得被记录的历史,但是厨房里的菜刀养育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滋养了人类文明,当然也应该是史诗的符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这篇小说里的奶奶,还是《白露春分》里的秀梅,她们都让我们看到历史叙事的另一面,你在讲述这些故事时的动力来源是什么,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故事?
辽 京:写作者总是需要找一些写得比较少的领域去尝试。在旧的框架里,很容易走入前人讲过的故事、写过的人物,在一个新的领域,则可以放开手脚。我是一个女人,我的记忆是一个女人的记忆,我的未来也注定是一个女人的未来,在自己熟悉的生活里,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这个应该是命定的。
同时,写作也有各种各样的尝试空间,比如从一个男孩的视角去讲他奶奶的故事,在这个被爷爷的故事熏陶长大的男孩子眼里,他奶奶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来历,有什么才能或者梦想,都是一个谜。女性的故事总是显得像一个谜,因为被讲得太少,或者说,被用失真的方式讲太多了,小说总是需要一些手段或者悬念吸引人读下去,但是作者始终要当一个努力解谜的人,可能一辈子都解不开。我的动力就是写一些生活“背面”的东西,直到“背面”也成了“正面”为止。
对人物的兴趣,就是对历史的兴趣,因为总想知道这个人物是怎么来的。把一个人物放在更长的时空背景中去看,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奶奶”,在主角眼里一开始她只是“奶奶”,似乎自己不存在,“奶奶”也就不存在了,怎么可能呢?随着成长,他慢慢知道自己不是“奶奶”存在的基础,在奶奶的符号之下,藏着一个真实的有血肉的人,这个人是他的至亲,他却对她的历史一无所知。他笨拙地想要发现她,寻找她的身世,像侦探一样去推理,像小说家一样去编故事,这些努力无不是他进入另一段生命历程的方式,这些路或许根本走不通,重要的是这个建构的过程。在“我奶奶的故事”中,“我”是非常重要的,奶奶是“我”想象的对象,以“我”的方式去补全“奶奶”的形象,想要讲一个传奇故事,最终还是失败了,“我奶奶”身上并没有传奇,她再次隐入平凡。然而,那个真实的女人究竟在哪里呢?
真实的女人在真实的生活里,不在传奇中。这就是为什么小说的结尾,“我”要走向一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老人,他的继父的母亲,标志着他将走出想象“我奶奶”的小房间,走向一个更开阔的人生阶段——看见他人,理解他人,超越了血缘与私人情感。他学会了同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奶奶的故事及其他》也是一个成长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