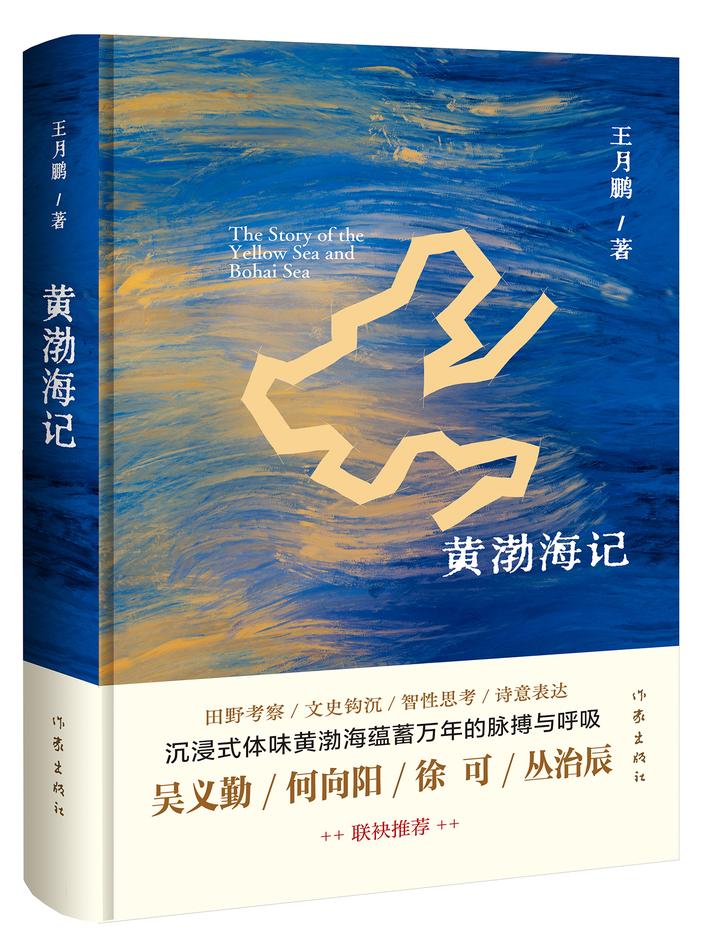□李永涛
“海渐行渐远”,大概是王月鹏新作《黄渤海记》的中心句,也是贯穿全书并辐射到字里行间的情感线。其所述及的位居半岛南北两个向度的海岸线变动频仍,如利津和丁字湾,恰与我们祖先于明朝永乐年间从东营利津搬迁至莱阳丁字湾的轨迹如出一辙。河海赐予我们养殖、种植、繁殖的沃土,最终归于沧海桑田。
正如《黄渤海记》所述,烟台是一座有着古老历史的滨海新城,远古时期即为东夷族所居之地,至明代设立卫所制度,烟台名谓从此固定,并遐迩闻名。这里又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区域,是古代的重要枢纽,更是中西交流和南北海运的必经之路。
“蓬莱神话”这一古典叙事母题,发展至刘鹗《老残游记》开篇所浮现的那个蕴藏晚清大变局缩影的梦时,已然昭示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转捩和发端,那就是家国情怀与民族复兴。至“五四”时期,“烟台叙事”开始栩然成型,并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史绵延不绝的支流。1949年为新政协会议召开而组织的知名人士“北上”,如叶圣陶等同船人士,即由烟台登陆,循此前往北平;早在1923年,叶圣陶即为烟台山写过妙句:“一座花园,一条路,一丛花,一所房屋,一个车夫,都有诗意,尤其可爱的是晚阳淡淡的时候。”读《黄渤海记》,亦为吟咏胶东半岛风土人情、谱写黄渤海前世今生的诗意盎然、情志葱茏的文学佳作。
当代文学中,作家萧平让“海滨的孩子”在黄渤海滩上留下了浅浅深深的脚印,王润滋记录着“赶小海”的小插曲,山曼则让风俗礼俗接通民间地气。张炜家族小说中的“海北”(胶东人渤海湾对面的辽东半岛)与同时期大连籍作家邓刚的书写,进入新世纪后,又成为两个半岛一爿海共有的文学资源,只是邓刚笔下的“海碰子”,成了《黄渤海记》中的“重潜”,“龙兵过”则是“过龙兵”,所指无有不同。
统观“烟台叙事”,黄海渤海总会若隐若现地萦绕其中,或背景,或场景,或味道,或形象,王月鹏孜孜不倦地对其进行了发掘深耕。《黄渤海记》形神俱不散,其集锦式的结构,如八角湾海岸线一样分形,却又有一个集中点,那就是聆听的心态、交互的时态和互动式的话语伦理。
《黄渤海记》并非人文纪录片脚本或风光介绍,而更趋近他所谓的“地质”属性,即不满足于描摹现实中的黄海与渤海,而是将其作为“背景板”“故事板”,将全书的情感逻辑、叙写风格、表达框架和深层主题纳入其中,最终“写下了海边人的生存境遇”。这境遇关乎神话及各种历史传说,犹若黄渤海鱼谱一样涉及各种海鱼,也牵系着其他神奇的海生动物。单论王月鹏对神奇海洋生物的相关叙述,已臻至动物寓言体小说的范畴。当然,这境遇更关乎那些拆迁的渔村、渔民及其传颂的奇人异人,若以鱼为引子,自然会进入岛屿和陆地,那些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人民,祖祖辈辈所秉持信奉的“民俗中的怕和爱”,既契符胶东人的“集体无意识”,又属于农家子弟特有的质朴情愫。可以说,王月鹏是首位将黄渤海的海湾“八角湾”作为书写主体的作家。
身居八角湾,西渡黄河口,南航丁字湾,王月鹏以其灵动丰盈的想象、穿插藏闪的技术、穿针引线的手法,使得整部作品经纬分明、凹凸有致。它不但串联起初旺、八角、芦洋等渔村,织缀起夹河入海口、黄渤海分界线、防护林和葡萄园,更挖掘出渔民对以风浪为背景的生活的理解:“海是他们讨生活的‘田地’。人在海上,就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命运,他们知道,一个人,甚至再多的人,也是没有力量跟大海抗衡的。他们知道大海的力量。”
关于胶东半岛、港城烟台及黄渤海区人民的生活方式,关于世代渔民的生存境遇,关于半岛周边环境的变迁,诸如此类的感喟与思考,最终造就了王月鹏写作特有的生命美学体验与生态伦理关怀,正如文中所言:“生命的坚韧,尊严与自由,都在一条肺鱼的遭遇里了。越是在狭窄的境况里,追求自由越是重要的。一条被砌在墙里的鱼,它不期待投入海洋,只要一滴水。它在一滴水与一个海之间,成为一个不被发现的传奇。”
节日与习俗的记录是本书一大亮点,堪比胶东民俗学大全。无论鱼灯节还是年节,乃至于各种食物,莫不周全备至,令人口味顿开。除在新农村建设中展现的人及故事外,《黄渤海记》还打捞出比如“芙蓉坡”这样已经消泯的民间地理名物,即便它们本身已经空无所指,却成为作家文学想象的遥指。
海与鱼、与渔网舟船、与人的关系,正如土地与人的关系,这种基于生态文明的朴素思想,始终充斥在王月鹏的“地质书写”中。《黄渤海记》从流传于胶东渔家的各种民俗中,剥离出敬畏与仪式之间的文化互动结构,继而敞露出人与海洋之间基于鱼水情深、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关系,疏通并靓丽了富于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大树的根系与枝叶。“人的不当行为导致海洋环境的变迁,最终反作用于人类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最先受到影响的自然是渔民自己。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是从对自我的约束开始的,他们相信只有做到日常中有所禁忌,才会最大限度地规避那些不可预料也不可控制的灾难。他们跪拜大海,在祭海的仪式感中,自有一份敬畏。不仅仅是敬,敬到一定的程度,还产生了畏。因为有敬畏,他们有所讳,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都有很清晰明确的自我要求。”细究“敬畏感”的生成之源,或是因流逝的生命体验与流变的生命意识而发,并隐含着对生死轮回的深刻理解。“逝者如斯夫”,由此沧海变桑田,由此蓝色复黄绿,由此海岸线退缩再延展,由此岛屿海滩渔村换了新颜,人及故事也角色轮换。
当时间成为《黄渤海记》真正的话语主体、叙述主体、声音主体,也就意味着“渔民说”才是浓墨重彩的篇章,“交互性叙事”是王月鹏散文叙事才能的全力展现。无论是船型、船上作业、捕捞用具,抑或渔村和生活方式、娱乐仪式的变迁,诸种过往与当下的参差对照,悄然完成了话语和声音的行文转换和腔调转译。此时的“散文”已经逾越了常规的文类壁垒,它不仅向说话主体的叙事声音转移,更让聆听者与记录者的姿态变得谦卑诚恳,洋溢着亲和力,弥漫着温煦风,在文本中实现了原生态的记录。
(作者系浙江丽水学院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