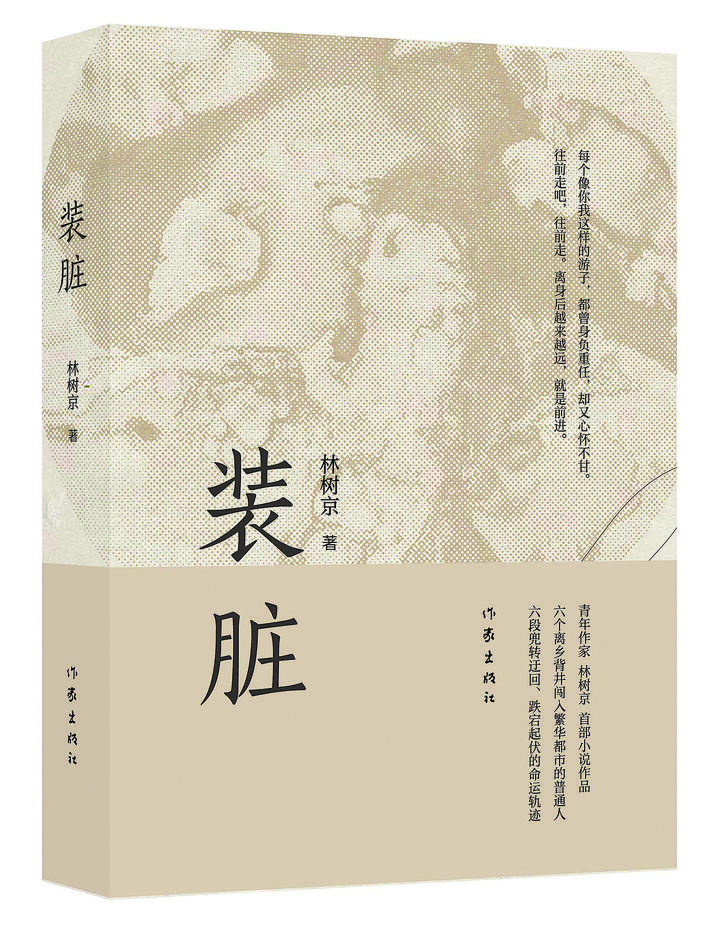□林树京
1 就算是在两年前,我都未曾想到过,自己能写出这么一本书。
那时我已经38岁,年近不惑,脑子里却被繁忙的工作、琐碎的家庭生活,以及各种各样令人焦虑的信息所塞满。身形臃肿,眼睛开始老花,连续几年不敢去医院体检。越来越懒得说话,越来越不爱社交。简而言之,中年男人会有的迷茫无措突如其来,降落到了我头上。
我早做好了准备:这是应该的,所谓代价,正是如此。
直到如今,我仍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写的第一篇作文。
那是一篇关于喂鸡的作文。我写道:我在地上撒米,小鸡们像赛跑运动员似的,争先恐后地跑过来。
这篇作文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贴到了墙上。
语文老师叫林建福。用浆糊贴完作文,他把我喊到跟前,递给我几毛钱,让我帮他去校门口小卖部买包香烟。我仍深刻记得香烟的名字——乘风,因为后来几年里,上课时建福先生总会突然喊我名字,让我出去帮他买烟。他还邀请我和他一起参加镇上的唱歌比赛,他拉二胡,我唱《浏阳河》。虽然这些事情和作文没有任何关系,但因为建福先生的偏爱,我对写作文这件事产生了格外的兴趣。不能在“专业”上令他失望,是我关于写作最原始的初衷。
真正促使我确立文学梦想的,是高一时的语文老师何建群。那是他来这个中学任教的第一年,也是唯一的一年。那年他成立了校文学社,让我担任副社长。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师生会在办公楼一个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编社刊。社刊名叫《纤夫》,很简陋的一份刊物。我在社刊上发表了一些作文,还有几首散文诗。那几期刊物,曾被我视若珍宝,收藏许久。
语文课上,何老师说:“要想写,须先会读。”从此,每天午休时,我便往图书馆跑,疯狂阅读黑塞、加缪、海明威、福克纳,等等。在长龙般蜿蜒的书架前,我暗暗立誓:终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作家,借文字之力,时刻审视内心,做一个清醒的人。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靠杀猪卖肉为生。我曾在无数个深夜,随他和母亲到某户农家,看他俩从猪圈里赶出一头三四百斤的猪,接着将它掀翻到两条并排的长椅上。在猪的奋力挣扎中,冒着被踢踹的风险,两人咬牙挥汗,好不容易才把四个猪蹄紧紧捆绑到椅面上。接着,在猪震天的嘶吼声中,父亲将短刀捅进猪颈,鲜血涌出。等猪断了气,我的父母便要开启下一个流程:烫猪刮毛,剖开猪肚,掏出内脏,肢解整猪,分离骨肉……每晚,他俩要用这样原始的方式,杀掉至少两头猪,逢年过节,七八头也是常有的事。等一切处理妥当,天还未亮。父亲把猪肉、骨头、内脏等,装到悬在摩托车后座两旁的篾篮里,分几趟,运到村里那个偌大的菜市场。天刚露曙色,菜市场就已开市。在肉摊前,父亲母亲招徕顾客,切肉、剁骨,站着,小腿发抖,直到午后闭市。
我小时候,母亲就对我说:“等你能挣钱养家了,我和你爸就马上退休!”从这句经年重复的话里,我听得出她对这份活计的疲惫和恐惧。
2007年,我研究生毕业,被长沙一家报社录用。出发去长沙前,我在饭桌上对父亲母亲说:“我能挣钱了,你们退休吧。”
此时父亲已年过花甲,头发斑白,满手刀伤;而母亲两眼混浊,身体因过度劳累而肿胀不堪。母亲摇头,说:“怎么也得等你娶了媳妇吧?娶媳妇要花好多钱,你自己一个人应付不来。”见我沉默,她又说:“不用太着急的,慢慢来,每个人不都这样子?赚钱,娶媳妇,生孩子,养家,最紧要是得一心一意地,踏踏实实地,安安稳稳地。”
那晚我辗转反侧。天快亮时,我得出一个结论:人这一生,最难的,不是在现实和梦想中做出选择,而是在你做出选择后,应该秉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你可以选择梦想,并终生为之颠沛;也可以放弃它,去按部就班、心无旁骛地演绎人生中的每一个角色。倘若选择了放弃,你就应该彻头彻尾地掐掉一切有关梦想的念头,从此心安理得,享受现实生活带给你的每一次微小的满足——只有这样,你才不会感到痛苦焦灼。
我起身,打开硕大的行李箱,把占了一半空间的书拿出来,放回纸箱,塞进床底。
2 说来奇怪,在20多岁的年纪,如此轻易地将所谓梦想弃如敝屣,实在与“追逐梦想”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却又与俗世评判不谋而合。
4年后,我的婚礼在我们那幢两层的石头厝里热热闹闹地举办。婚礼第二天,父亲母亲兑现诺言,去菜市场退掉了摊租,收起刀具、篾篮和麻绳,从此结束这段长达30年、无比劳苦的屠户生涯。
后来的十几年里,如同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我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值得称道的角色:通过努力使父母得以安度晚年的儿子,悉心照料家庭的丈夫、父亲,拿了多年优秀员工奖的打工人,以及一家经营了10年的小公司的老板……
你完全可以想象,这是一条缓缓行驶在人生河流上的小船,安稳适意,优哉游哉。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满足、快活,莫过于此。
3 我记得那是2022年春天,疫情仍在肆虐,封锁住所有人的脚步。春寒料峭,所幸阳光还能透过落地窗,光明正大地闯进阳台,在这方寸之地生造出一片温暖祥和。
我和两个女儿各据阳台一角。她们安静地坐着翻书,而我则以一种怪异而舒适的姿态躺卧在懒人沙发上,无所事事刷着手机。没多久,老二放下书,径直走到我跟前,用稚嫩的嗓音问:“爸爸,我们都在看书,你怎么不看呢?”
我怎么不看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太复杂了。但若要用三言两语总结,也不是不行。我知道,要是重新拿起书,我就再也不能像此时此刻这样,慵懒地躺平在阳光下,就再也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这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没等我回答,老大接过话头,说:“你不看书,我也不看了,我也想玩手机。”
那条河流,就是这时在我眼前铺展开来的:开阔,无风无浪,我的小船行驶在水平如镜、闪烁着金色阳光的河面上。
那晚我很早就睡下了,胡乱地做了许多醒后即忘的梦。半夜又突然醒来,像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几乎是无意识地,黑暗中,我摸出手机随机下单了几本小说。接下来,我盯着晦暗的天花板,再无睡意。几乎能想象,几天后书寄到时,我将会用一种故作轻松的口吻,对女儿说:“爸爸也要看书了哦。看书是好事,我们都要好好看书。”
4 我家地下室有个10来平方米的储物间,无窗,密闭。我仓促收拾出房间一角,摆上电脑,使它成为我的书房。
2022年3月,就是在这个杂乱而幽静的地方,我与久别的文学梦想重逢了。
在储物间的电脑上,我敲下了第一个句子:“我18岁那年,家门口有条土路直直通往村供销社,路边种着成片的针叶树木麻黄……”
从那个多梦的夜晚开始,我就知道,对我的河流来说,这次重逢将无异于一场再难止息的风暴。它或许不至于颠覆河面上那条贪恋平静、怠惰太久的小船,但从此以后,这条小船将永无宁日,飘摇在一发不可收拾的惊涛骇浪之上。
5 我即将开启一段漫长的跋涉,但我并未对这场跋涉提前做任何规划。没有故事,没有主题,而写作已经开始。我知道这很荒唐。然而,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底气的写作,向来不都这样荒唐吗?
后来我才意识到,不是我在创作,而是我把自己交给了文字。
随着写作的深入,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被裹挟进一个巨大的漩涡。这个漩涡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也许,我这一路走得太过顺遂,太过心安理得,因此从未有过察觉:河流底下其实早已暗流涌动。无数等着下笔的故事,无数等着思考的问题,早已淤积成这些暗流,直至汇成这个漩涡。
我明白了,对一个作者来说,你要采用哪些题材,思考什么主题,通常是不自觉且没有选择余地的。因为你已深陷其中,所以你笔下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会跟着被卷进这个漩涡里;因为始终放不下一件事或一种情绪,所以你才会不自控地想要记录,想要表达。
这种表达需要坦诚。
只有坦诚,才能真正审视自己的内心。
于是我只能把这些情绪很坦诚地记录下来。而这些情绪关于梦想与现实,关于逃离与坚守,关于自由与安定。
我暗自庆幸,在我的笔下,主人公林北树慢慢有了属于自己的轨迹。他将如我一般,在经历过诸多人生命题的抉择后,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6 就这样,我一边漫无章法地写作,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
那一阵子,我买了数百本书。其中,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使我感到深深的震撼。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英国管家,在人生的暮年,为时已晚地认识到他的一生一直遵循着一套错误的价值观……认识到……他在某种深层意义上浪费了人生”。
那晚,当我读完《长日将尽》时,已接近零点。我放下书,走进卫生间,开始洗漱。从洗脸台的镜子里,我看到了一个被我忽视和压抑已久的自己,看到了一张即将迈入不惑大关的灰败的脸。
其实我早该知道,这样的状态一旦持续太久,人就会成为一块僵硬的水泥,封住所有的思考、怀疑和挣扎——而这,正是一个我从不愿意正视的自己。
我原以为,我是如此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因此,我这前半生也才如此顺风顺水。我始终秉持着一个健康的心态,我是多么地享受其中,我也该如此享受其中。然而这一切,却又是如此地不堪一击——一本外国小说就能轻易将其击溃。
一直以来,我都在对一个事实进行闪躲和回避:在我身体内,还有另一颗心脏在跳动。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曾自以为很坦诚的记录和表达,毫无疑问,是自欺欺人。意识到这一点时,这本小说的写作已接近尾声——我的主人公林北树,已经找到了那条“正确”的道路,意气风发,得意洋洋,他从未认识到自己“在某种深层意义上浪费了人生”,也浑然忘记了那个他从不愿意正视的自己。
我想起当时自己青葱年少,在图书馆里暗暗立誓,要借文字之力,时刻审视内心,做一个清醒的人。
而清醒的人,绝不会在文字中、在自省中,蓄意掩盖。
我决定推翻重写。
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痛苦不在于决定本身,痛苦在于:做完决定后,要去真正坦诚地审视自己,去勇敢正视许多年来所遵循的价值体系的崩溃,去细致地剖析身体里另一颗跳动着的心脏。
7 这本小说前前后后写了两年,相当于我跟真正的自己进行了一场长达两年的对话。
如今这场对话,终于通过这本书传递到了读者手上。我希望它能有足够的力量,使得一些像我这样的人,找到跳动在身体里的另一颗心脏,找到真正的那个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