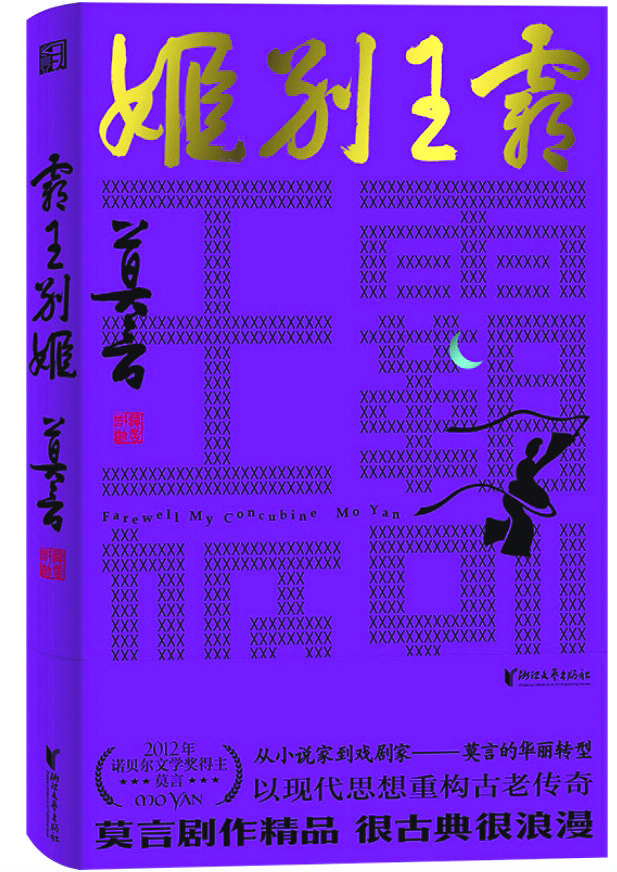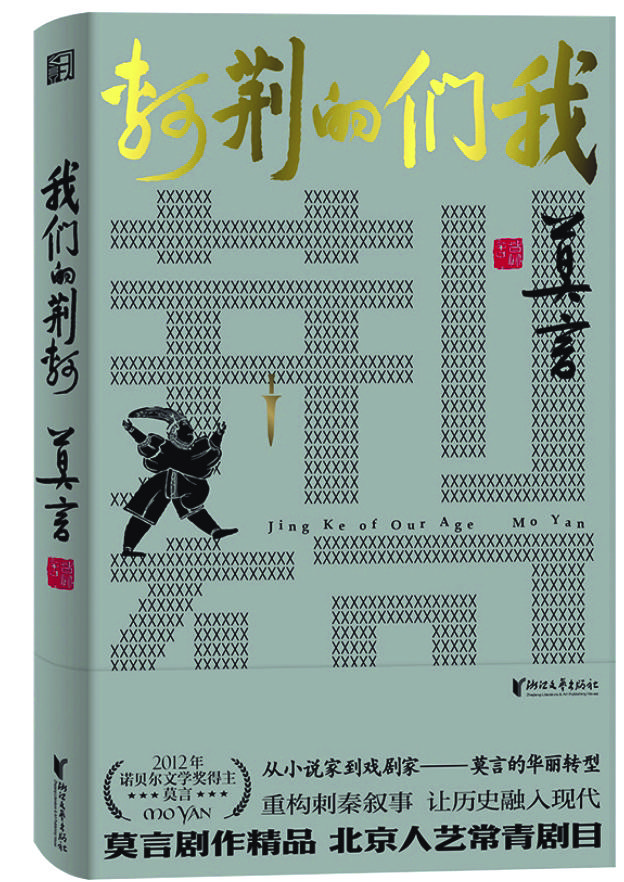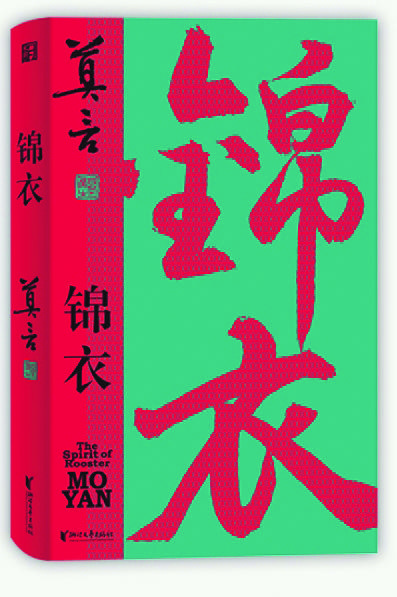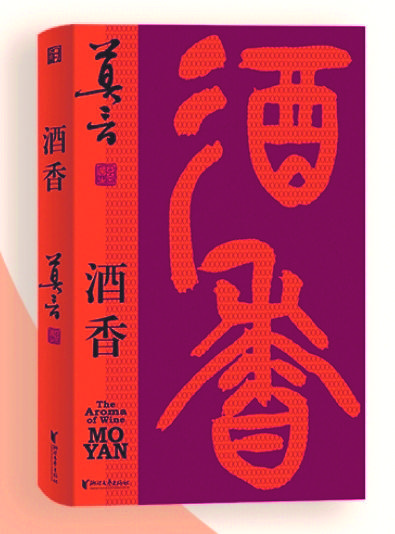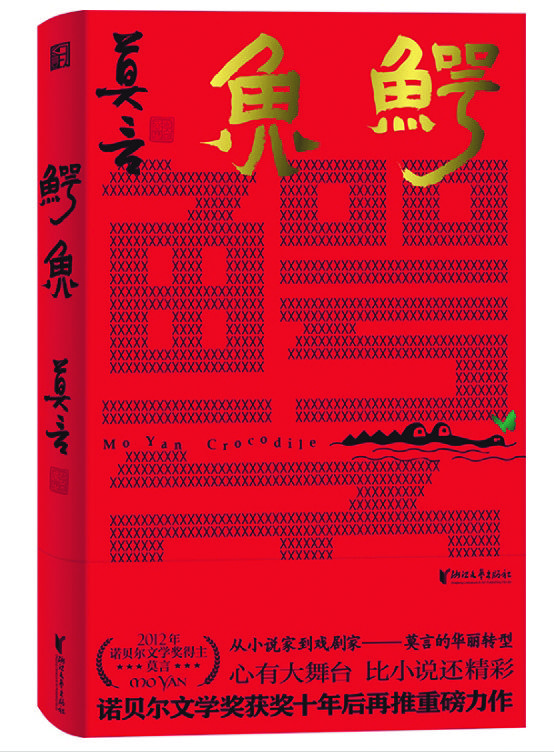毫无疑问,莫言几十年的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动缩影和重要表征,巨大而持续的影响力贯穿于40年的当代文学发展历史。莫言早在80年代即开疆拓土,以“红高粱”系列声名鹊起,形成了他自己的“风云初记”,而后一路势如破竹,佳作迭出,其主导风格在乡野传奇之外,不断地寻求新变和突破。即使在获得诺奖殊荣之后,也从未懈怠。《晚熟的人》所集结的中短篇小说,呈现出前所未见的“现代感”,契合于当下的时代律动。不仅打破了“诺奖之后,无以为继”的“魔咒”,更令人油然而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之慨。这或可谓萨义德所说的“晚期风格”,或可谓“中年变法”。唯有活力充沛,不愿自我重复之人,才有坚强的心志实现“文学变法”。莫言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壮心不已、身体力行的大作家。
“新领地”与“旧园子”
戏剧创作是莫言文学生涯的起点,也是他念兹在兹、一直未曾放弃的文体。他的早期作品善于调用歌谣、茂腔、话剧等戏剧形式,此前也创作过不少戏剧作品,近年来更是将创作重心从小说转向戏剧。这是他“文学变法”中的新领地,也是旧园子
莫言为人瞩目的“文学变法”的另一个新领地,也可以说是旧园子,当然是他的戏剧创作。之所以说也是旧园子,是因为戏剧创作不仅是其文学生涯的起点,也是他念兹在兹一直未曾放弃的文体。早在《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等作品中,莫言就不断调用歌谣、茂腔、话剧等戏剧形式,给小说文本带来奇妙的美学效果。莫言此前已经创作过不少戏剧作品,比如《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锅炉工的妻子》等。这些年他干脆宣布把创作重心从小说转向戏剧,一定程度上是回归亦是再出发。莫言之所以要在本色当行的小说之外,全情投入戏剧之阵,固然有其个人兴趣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戏剧与小说两种不同的文体功能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戏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有着更为迅疾的传播速度、更加广大的读者观众、更趋先锋的表达能力。它在形象塑造、能量迸发和创新出奇的直接性、即时性和参与性等诸多方面,都可补小说叙述之不足。小说是静态的文本,戏剧是动态的实践,无论是行动力和表现力,还是社会影响力与感染力,后者显然都较前者更易收到即时性的反馈,更有利于作者的自我校正,维持更强劲的戏剧续航力。
剧本者,一剧之本也。作为小说家出身的剧作者,莫言在人物塑形、情节铺排和场面调度上无疑有更多得天独厚的经验与优势,但是戏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比小说更加快捷、直接、光亮,人物开口,价值缠斗,激烈的矛盾冲突往来眉睫之间。小说可以冷淬收场,戏剧却难以兵不血刃。小说委婉铺叙的草蛇灰线,到了剧本中则必须短兵相接,五步之内,必要见出个分晓来。而且戏剧从作者戛戛独造的“案头本”,到剧组群策群力的“演出本”,其间也得经过诸般变身、协商与斡旋。有些剧作者事必躬亲,坚持原作的权威性,也有些剧作者则对自己的剧本充分放手,享受“演出本”挑战和激荡的快意。莫言显然是不拘一格、从善如流的后者,总是满面微笑地应对建议和改变,乐在其中地参与剧本的搬演。
“古典资源”与“现实经验”
莫言善于从古典资源出发,对“荆轲刺秦”“霸王别姬”等经典历史故事进行重写和新编。此外,他也怀着热辣滚烫的百姓立场,敏锐地处理飞速前进的大时代中闪闪发光的当代题材,书写具有现实关怀的“人民文学”
在当代小剧场艺术蓬勃兴盛的北京,莫言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得时空人事风气之助,《我们的荆轲》就成为北京人艺榜上有名的保留剧目。“荆轲刺秦”这样的经典新编,是每一位戏剧高手见猎心喜的题材,而今《霸王别姬》,也是类似的从古典资源出发的尝试和重写。
古典资源重写之外,莫言对当代题材的处理更是出手不俗,比如《锅炉工的妻子》就敏锐地捕捉了飞速前进的大时代中被抛落的手艺人,感慨旧时整个行当的式微没落。集中供暖的实行,使得锅炉工们无事可做,面临着下岗失业的困局。无法接受自己空有一身好本事,却要惨遭时代淘汰的锅炉工,发出悲伤愤怒的嚎叫,就像受伤的野兽那般,使出浑身解数来做最后的控诉。这种直抒胸臆的写法令人印象深刻,悼念那些已不可挽留、默默逝去的旧行当,点染出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时代巨变对升斗小民生计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影响。莫言的抒写具备一种热辣滚烫的百姓立场,是属性鲜明的“人民文学”,因而分外得到广大观众和读者的喜爱与认同。
至于现实讽喻题材的《鳄鱼》,在人物命名上与莫言小说命名的习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望可知剧本所蕴含的浓厚的寓言意味。《鳄鱼》中每个人物的言行极尽夸张,可静下心来回味,又是日常生活中应有之义。我们仿佛不经意间会在某个街角,迎面撞上与单无惮面貌相似之人,甚至可能认识不只一位牛布。或者这些在阳光下没有影子的、行尸走肉般的游魂人物,有时竟是某些时刻的我们自身。每个人的内心,可能都深藏着欲望的鳄鱼,一如《彼得潘》里的老鳄鱼某次意外吞下了钟表,从此以后,时间就在它肚子里嘀嗒作响。虽然每次和铁钩手胡克船长过招,它都占了不少便宜而令船长头疼不已,然而这经由时间带来的无比具象化的“惘惘的威胁”,个中滋味只有鳄鱼自己才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困境吗?还是可以更狡黠、更轻盈地对此避而不谈,索性从自个儿的头上一跃而过呢?莫言并不急于给出答案,而是步步惊心地引导我们不得不面对心中的鳄鱼。这是他的高明,也是老辣凌厉之处。
“生面”与“熟面”
莫言绝非舍小说而就戏剧,而是在其小说的独擅胜场之外,孜孜开拓了戏剧别样的“生面”,又由生面很快转至熟口熟面,融百花而自成一味,以返璞归真的姿态实现了自我与文本的双重突破
《锦衣》《酒香》二题,都是莫言“唱”出来的剧作。歌诗合为时而作,一旦抵达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程度,即可见莫言已经深入戏剧创作的酣畅淋漓之境,达到了我手写我口、我口唱我心的境界。钱锺书曾经讨论过“心手难应”的现象,指出“自心言之,则发乎心者得乎手,出于手者形于物;而自物言之,则手以顺物,心以应手。一艺之成,内与心符,而复外与物契,匠心能运,而复因物得宜。”(《管锥编》)莫言的心、手、口的圆融,正可谓得诸巧心而应以妍手。在情不自禁的歌咏之中,在酒饮微醺的美好时刻,莫言保留了足够的书写清醒,可见“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之说,诚不我欺。《酒香》一册巧妙从《高粱酒》和《檀香刑》两部剧本中各取一字,戏剧版《高粱酒》(以小说《红高粱家族》为底本)和《檀香刑》的酷炫登场,昭示着剧作家莫言对小说家莫言的“征用”和“改造”,漂亮地完成了跨文体的自我变革、自我更新也是自我互文。转化为戏剧的《高粱酒》和《檀香刑》,比之“基础小说版”更为鲜活生猛,狂言无忌,“悲歌痛饮忘生死,儿女英雄在我乡”(莫言《题〈高粱酒〉》),端的是一个痛快。莫言的戏剧语言宜古宜今,嬉笑怒骂俱成文章。他就以这样的语言风格,风风火火带着他的戏剧人物闪亮登场,让小说读者们又获得了迥然不同的深度戏剧体验。
莫言以其一贯的幽默,尝言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两位那边都发过誓,后半生将穷尽一己之力,好好完成从小说家到戏剧家的华丽转型。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毕竟是小说家言,个中的揶揄意味和修辞策略其实不能轻易弃置。莫言绝非舍小说而就戏剧,而是在其小说的独擅胜场之外,孜孜开拓了戏剧别样的“生面”,又由生面很快转至熟口熟面,成为大家广泛认可的剧作家。诚如我在另一篇文章所说,“剧作家莫言对小说开放性的借鉴,以有限的舞台兼容了小说的开放性。莫言浸染于欧美戏剧与中国戏剧传统,融百花而自成一味,以返璞归真的姿态实现了自我与文本的双重突破,也为当代戏剧创作拓展了未来发展的可能与空间。”与此同时,复数的莫言也在不知不觉中于焉生成:小说家莫言、剧作家莫言,甚至科幻作者莫言——君不见《球状闪电》的前瞻和预流可以一直追溯到1985年。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作为复数作者的莫言正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多重身份的“莫言们”纷至沓来,这不是魔幻,而是无比真实的现实。
多能文事的文体家莫言,有滋有味又不无游戏地不断拓展疆界,施展着他的文学雄心和文体突破。其间,万变不离其宗的则是那颗来自山东高密乡与红高粱同呼吸共命运的淳朴之心。环顾当今文坛,如此丰富复杂、变化多端、词理弘通、文采焕发者,并不多见,对莫言的理解与阐释也就成了“说不尽的哈姆莱特”。如此说来,我们倒不妨借用学者王德威的那句名言:
“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