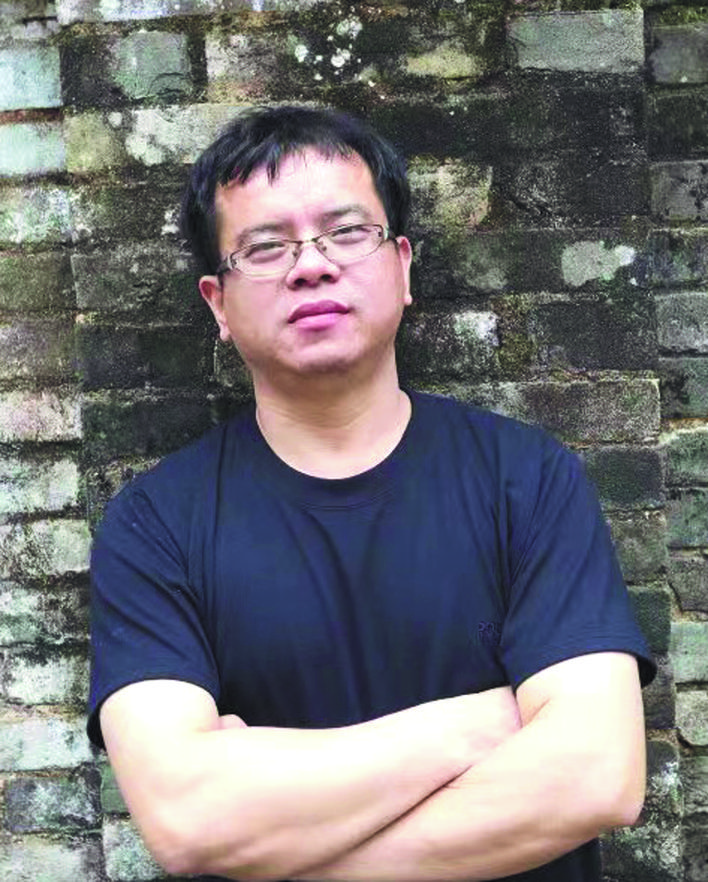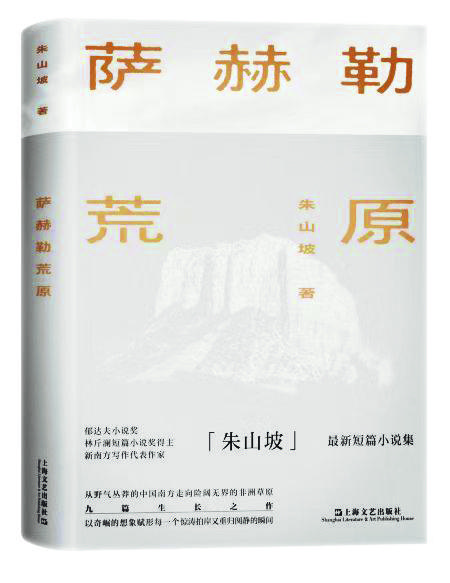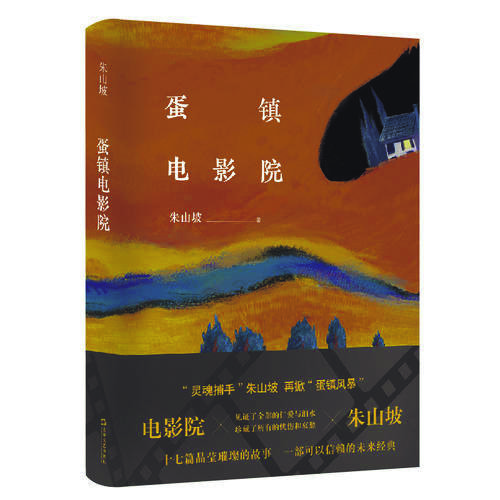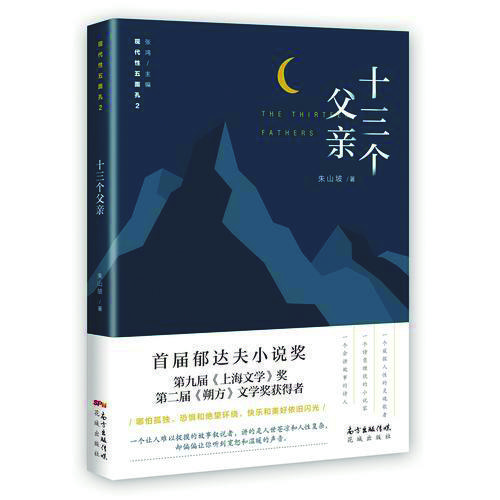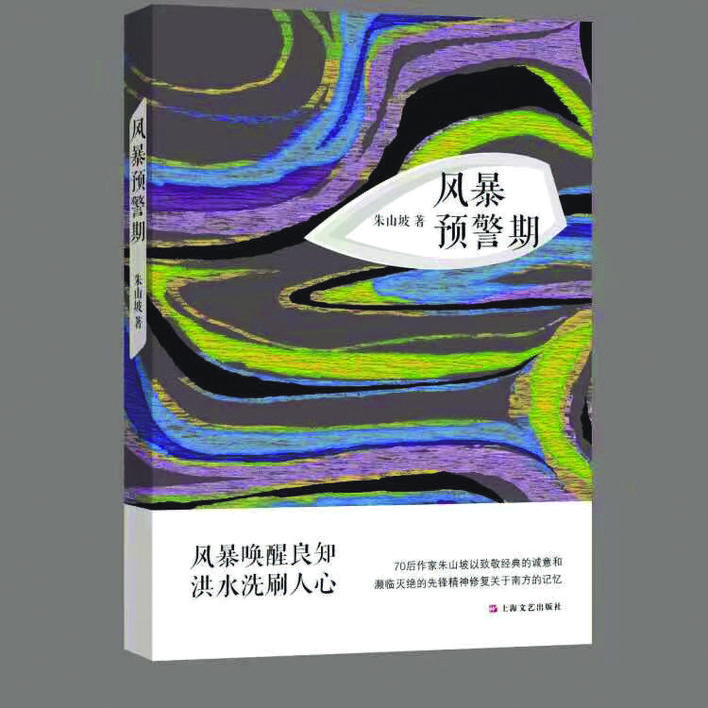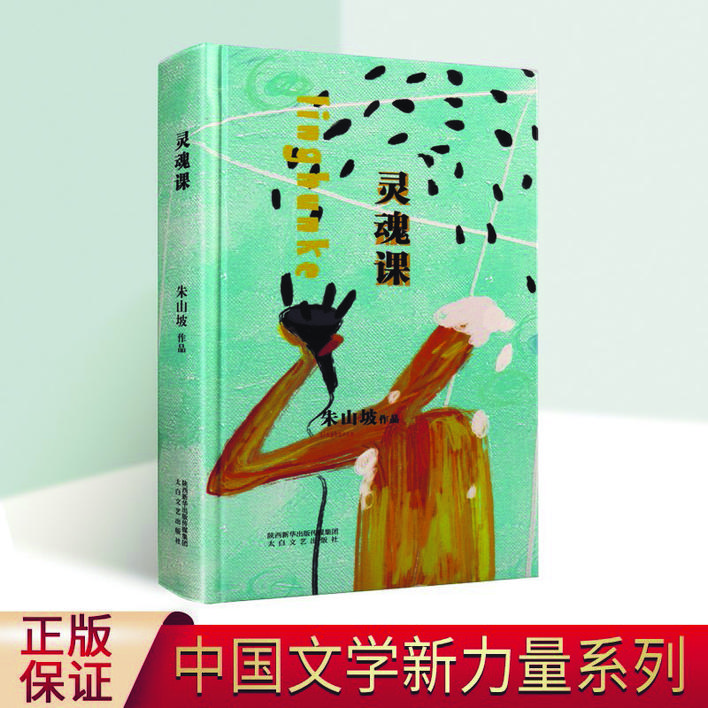把每一篇都当“成名作”“代表作”甚至最后一篇去写
林 森:山坡,你好,让我们从诗歌开始吧!我总感觉,你虽然一直以小说家尤其是短篇小说家为大家所称道,但我在阅读你的作品之时,总感觉到其中蕴含着浓郁的诗意。我知道,你早期有过狂热的诗歌岁月,这些年也陆陆续续发了一些诗歌,最近还发表了反映地方诗社兴衰的长篇小说《蛋镇诗社》,可以说,诗歌是铭刻在你的内心深处的,你可以先说说自己跟诗歌的渊源。
朱山坡:我怀疑所有的诗人最初都是突然地、毫无先兆地喜欢上写诗的。1986年上初中,有一天我从杂志上读到几首诗,回到教室便开始写诗了。后来,同学们沉迷于金庸、琼瑶,我喜欢读席慕蓉和朦胧诗。当时正好学校有一个老师写诗,镇上有一个叫谢夷珊的高中生也写诗。我从他们那里借阅到大量的《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绿风》等诗歌杂志,狂热地爱上了诗歌。那时候,听说镇上成立了一个诗社,还铅印了一份诗报,虽然我从没有参加过这个组织,也没见过诗报,但我对诗社无限向往,希望等我把诗写好了他们就能吸收我入社,我将成为诗社的得力干将。然而,诗社很快便“作鸟兽散”,原因不明。后来也从没有见过他们,只是从谢夷珊口中知道他们的点点滴滴。然而,正是这些碎片式的信息让我对他们充满了想象。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把他们“养”在脑海里。2000年左右,家乡北流一帮朋友创建了一个叫“漆”的诗社,我加入其中又重新疯狂地写诗,办诗歌活动,编印内部诗刊(又称民刊),玩得不亦乐乎。那时候互联网刚兴起,我热衷混迹各类诗歌论坛、小说论坛,参与争论、吵架,好生热闹,视野和思路一下子打开了。那段时间没有持续几年,却对我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我十分怀念那些日子,同时也经历了很多有趣、好玩的事情。诗歌是诗人的冲锋号,诗社是诗人的集结号。没“玩”过诗歌,永远不知道诗人的幼稚、可爱和疯狂。我向来敬畏诗歌,敬重诗人。长篇小说《蛋镇诗社》就是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现在我依然读诗、写诗,我希望自己能像诗人那样思考,像诗人那样生活。
林 森:确实,对于一个立志写作的人来讲,年轻时候的诗歌经历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你最早为文坛所熟知,却是通过小说,比如,二十年前在《花城》杂志的“花城出发”栏目推出的两篇小说,之后在《天涯》发表的《陪夜的女人》《跟范宏大告别》等,给人一种出手不凡眼前一亮的惊艳感。可以说,一个作家早期的登场方式,对其后来的写作,是会产生极大影响的。你可以说一说“出道”的经历。
朱山坡:诗歌虽好,却不是久留之地。因为我发现诗歌并不能满足我虚构故事和塑造人物的热情。一起“捣鼓”诗社的伙计们仍在热火朝天地写诗,而我悄然转赛道开始写小说了。但我对小说写作几乎一无所知,疯狂地补课,从网上下载打印传说中最好的短篇小说,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慢慢开窍,知道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然后朝着心目中的经典去写。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岁“高龄”,又在政府办公室忙于写公文,觉得留给我写小说的时间不多了,不能跟同行拼数量,所以每写一篇都把它当成“成名作”“代表作”甚至最后一篇去写,奔着“经典”去写,用尽心思,拼尽全力,一辈子写好这一篇就够了。直到现在,我仍然这样怀揣这样的想法。
林 森:我很好奇,到了2017年,你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了,为什么在2017年,你还选择回到校园,到北京师范大学再读一个作家班的硕士?而且,可以看到,读完这个作家班后,你的生活还有了诸多变化。重回校园,到底出于什么考虑?
朱山坡:我自认为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读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大学是一个学习氛围很浓的地方,我一直很向往。而且,我有知识恐慌症,总觉得自己读书少,需要补课,犹如空中加油。相对于其他来说,闲下来集中时间学习是最好的选择。2016年年底,突然接到邱华栋老师打来的电话,动员我报考鲁院北师大联办研究生班,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还担心考不上呢。在北师大读书期间,很自律地挤地铁去上课,在学校图书馆里转悠,看黑压压的乌鸦……我的考勤是不错的。没课的时候,待在鲁院睡觉、写作,走路去电影院、火锅店、大悦城、红领巾公园,都挺好。离开北京返回工作单位,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似乎又成长了,朋友们说我的书呆气又加重了。意犹未尽,很快我从作协调到了广西民族大学工作,办公地点就在图书馆大楼里。除非必须外出,否则我几乎每天都在办公室,即便是寒暑假期间。
林 森:在北师大期间,你写出了《蛋镇电影院》和《南国佳人》等作品,其中,《蛋镇电影院》的影响是挺大的,其中的多个短篇,在各期刊发表时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结集成书后,既是一个短篇小说集,也可以当作一个长篇来看待。这部作品延续了你之前《风暴预警期》的风格,地方性的独特幽默与情感的共通性相互融合,感人至深,被称为“坡式小说”。你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在风格、表现形式上有什么考虑?
朱山坡:写《蛋镇电影院》跟你脱离不了干系。你还记得在北师大最后一堂英语课吧,我讲了我小时候的理想,荒唐而有意味,你鼓动我写出来。我问你,我写出来你们《天涯》敢发吗?你认真地说:“有什么不敢的?”于是我便写了短篇小说《胖子,去吧,把美国吃穷》。写完这个后,“电影院”在我的脑海里一下子波涛汹涌,浪花激荡。那几天,我把题目列了出来,然后按部就班一篇一篇往下写,一共写了17篇。我骨子里是一个幽默和忧郁互相拉扯的人,在这部小说里体现得比较充分。这是一部围绕电影院来讲故事的主题小说集,有时候我把它当成长篇小说,但又有些胆怯,直到后来读到毕飞宇评论奈保尔《米格尔街》时的一段话,我才没那么纠结:“不好的作家可以将长篇写成短篇,好作家可以把短篇集子写成长篇。”以短篇的形式写长篇固然有它的局限和缺憾,但我认为自己短篇写起来更得心应手,更有力量,更体现自己的风格。我追求有力量有爆发力的小说,像在拳击台上比赛。
“新南方写作”并非狭隘地强调地域的意义,而是找到写作的态度和方式
林 森:你前面也谈到,北师大毕业后,你的职业生涯发生了很大转变,你先是进入广西民族大学,之后不久,你又从高校离开,前往广州当专业作家,这种身份的频频改变,对于写作者来讲,其实是很影响写作状态的。你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的?或者说,你是出于什么理由,在这个年纪,不断变换身份和工作地点?
朱山坡:我一直喜欢“漂泊感”。我在粤语文化区长大,广州是我从小就十分向往的城市、大地方,它像一个巨大的谜横亘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机缘巧合让我有机会到广州工作。我在广西生活五十年,觉得挺好的,离开广西我还是纠结了许久的。待在广州,并不全是为了文学。文学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世界很宽阔,不一定要偏安一隅,与舒适相比我更想丰富自己的人生。无论在哪,都是换个地方生活而已。没有哪段经历是白费的。在广州当专业作家也将是一段难得的经历,一个全新的环境,五湖四海,人潮涌动,川流不息。我对写作环境并不十分挑剔,在广州也很宅,基本上都待在大学城,买了一辆小电驴,北亭村菜市场几乎是我每天要去的地方。住在工作室,连租房都省了,经常整天都在工作室。随遇而安,不必想太多,把自己照顾好,过好每一天,有余力而著文。
林 森:当然,从某种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你的迁徙,仍然是在所谓“新南方”的范围内。这就不能不说到,这几年和你的写作贴得比较紧的“新南方写作”这个说法。还记得我们在北京读硕士研究生时一起“回望”南方的那些散发性想法,我们都写了一系列“南方”特点更显著的小说……关于这个话题,你谈得也比较多了,这一次你可以切换一下角度,谈一谈当“新南方写作”和你产生联结之后,你感觉到你的写作或者说文学界对你的看法、期待,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
朱山坡:我们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哪怕站在十里堡俯瞰南方,距离感和边远感都会油然而生。因此我和你、陈崇正等对“南方”有比较深入的交流。后来我们都参与了“新南方写作”的讨论,大家的观点和论述很有见地和启发性,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自我“定位”更自觉了,方位感更强了,身份的确认更坚定,我就是一个“南派”作家,不必自惭形秽,也不值得沾沾自喜,既不俯视,也不仰望。南方博大而浩瀚,细密而真实。但我们不能狭隘地强调地域的意义,而是找到写作的态度和方式。无论在哪里写作,都必须面对世界,不仅仅是在南方或中国写作,而是“在世界写作”。我在努力加强“南方”的特点,写出新意,提高辨识度。我注意到了你的海洋题材小说,就是一种“很南方”的新小说。我十分期待在南方写作的作家有更多更有标志性的文本,为“新南方”添砖加瓦。
林 森:是的,对于作家来讲,最重要的是出作品而不是被加冕。从作品的角度来讲,毫无疑问,你在短篇上的努力最为大家所称道。近年来,你的《深山来客》《萨赫勒荒原》《日出日落》《一个夜晚,有贼来访》等短篇,都在各个向度上,探索了当代短篇写作的可能性。但你也知道,在当下的小说领域,无论是阅读、评论还是市场,都更加青睐有命运感的长篇;从改编的角度来讲,也更加关注把故事讲得风生水起的中篇——书写短篇,稍不留神,就会被错过、被无视,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更加吃亏的。而你如此专注于短篇小说,是出于什么考虑?
朱山坡:我对短篇小说特别上心。在刚开始学写小说之初,我受到了全世界的短篇小说杰作的影响和鼓舞。比如福克纳、马尔克斯、契诃夫这些大师的短篇令我着迷。那时候,莫言、苏童、余华、王朔各推荐了二十篇世界上最好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成了我反复阅读、解剖、玩味的对象,我觉得它们是皇冠,是钻石,是炸裂的闪电,是我“毕生有此一篇足矣”的追求。我也是这样做的,一直在努力写出那样“好到极致”的短篇,希望能一步步地接近,感受触摸到顶尖的感觉。写着写着,不知不觉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于几乎荒废了中、长篇。尽管对中长篇很羡慕,大部头摆在那里,市场收益、影响力俱佳,谁不羡慕呀,短篇就像是散兵游勇,不排山倒海,不摧枯拉朽,很难写出“史”的浩瀚。连影视公司都不太在意短篇小说。但我是执着于把短篇“玩”到极致,正如一个剑客,埋头专注于磨一把短刀,年过半百还没磨成,心仍不甘,仍有耐心,只能继续磨下去。
林 森:《风暴预警期》《蛋镇电影院》和刚刚面世的《蛋镇诗社》,可以说,你通过这三部既有短篇精巧又有长篇厚重的独特作品,构建了自己的“蛋镇”世界,亮出了自己的“蛋镇”坐标,完成了“蛋镇三部曲”的书写。之前的《蛋镇电影院》还被很多同行羡慕。可以说,你的“蛋镇三部曲”,不仅仅在文学地理上有延续性,其风格也有延续性,那就是“以短篇的形式写长篇”,这样的结构,当然可以很好发挥你短篇写作的才能,但也会有人提出疑问,这样的写作,会不会是在结构上回避长篇小说写作的难度?你自己对当前中国的短篇、长篇的看法又如何?
朱山坡:我相信小说有一万种写法。结构很重要,但结构也有很多种。我并非不屑线性叙事,只是有时候对严格遵守“公序良俗”小说规范的写作感到厌倦。我试图用一种蓬松、杂芜、不规整的方式讲述一段过往,像经营一块菜园,菜苗固然重要,但对杂草也很珍惜,让它们各自生长,彼此映衬,一枝一叶皆是春色。《蛋镇电影院》《蛋镇诗社》都是以短篇的形式写长篇,实际上是主题短篇集,这种写法并不新鲜,国外有很多。这样的写作难度也很大,像做一个拼盘,设计一座花圃,对每一个细节的极致追求已经竭尽所能、倾尽所有,有时候无暇顾及其他。当前烂短篇很多,烂长篇也不少。我阅读长篇的时候也像阅读短篇那样细读,如果读完一部被捧得老高的长篇却大失所望的话,我会生气。但读了一个烂短篇不会生气,因为没有浪费我多少时间。世界上只有好作品和烂作品之分,跟长短没有多大的关系。
“面向世界写作”是一种姿态和自觉
林 森:你刚刚发表的长篇小说《蛋镇诗社》,跟你文学里的故乡蛋镇有关,更跟诗歌有关。我们都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诗歌曾经在中国引发过诸多狂热,从年龄上来讲,你没有赶上诗歌狂热期的最高潮,但也赶上了一个尾巴。你的《蛋镇诗社》写了一个小地方一群尴尬的无名诗人,又在某种程度上,写下了那个时期一代中国人的隐秘心灵史。这段心灵史,很多作家是不愿去提的,总觉得回头去看,少年时的诗歌岁月太傻、太笨、太稚嫩、太癫狂……总之,就是说起来,总是避免不了尴尬,可你把那一段傻里傻气又无比珍贵的内心历程书写了出来,这在中国的长篇小说里,是少见的。我们都知道,近年来有些小说缺少轻盈、诗意和想象,而你这部长篇的独特性也就在这里,你从现实的污泥中拔腿,告诉读者,我们还可以诗意地飞翔——即使飞翔的姿势有点傻。可以说,这部长篇,在中国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当中,是一个特例,你怎么定位自己这个长篇?
朱山坡:在我的少年时代,我觉得诗人是至高无上的称号。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我一定会无比自豪地走过家乡的每一寸地方,我才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正在家乡小镇上读初中,接触到了诗歌,但并不知道诗歌在中国引发过诸多狂热。镇上还有人因为在公开刊物发表了几首诗竟被著名大学免试录取,我也曾幻想“步其后尘”,未果。多年后,我参加了诗社,参与了跟随互联网时代到来的诗歌浪潮,见识了以诗歌名义奔走呼喊的各式人等,他们身上有天真可爱、闪烁着理想主义光芒的一面,也有幼稚、癫狂和低俗的一面。相比之下,八十年代那批诗人可能更纯粹更奔放更无畏,也更执着更荒唐更悲壮,内心更波澜壮阔,他们真有改变世界的冲动和莽撞。我想把他们的心灵深处的隐秘挖出来,通过他们再现那个野性勃勃、朝气冲天、敢想敢做的特定时代,为他们立传、为“荒唐”正名。但我并不想把它写成文人小说,而且刻意避免。我不喜欢文人小说,更不愿意调侃、嘲讽、轻慢文人。《蛋镇诗社》里的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诗社解散后大部分成员各奔东西,远离诗歌,销声匿迹,成为芸芸众生的一员。我就想告诉大家,那个时代,是一个诗意蓬勃的时代,是一个满大街散发着理想主义的时代,哪怕轻如蝼蚁的普通人对未来也充满希望和信心。“怀念八十年代”这个话题很小资很矫情,我无意为它增补什么,我只是单纯想为当代文学增加一部关于诗意和理想的小说。从写法上看我觉得有新意,独具一格,我希望它不是一部烂长篇,读者读完后不生气。
林 森:在写作上,回到故乡与远望世界,其实是同步存在的,在不断挖掘地方经验的同时,也需要具备一个望向世界的视野,观察你近年的写作,其实也是在这两个向度上不断交融、延伸。你认为应该怎么秉承文学的审美?
朱山坡:“面向世界写作”是一种姿态和自觉。大家都在眺望世界,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为什么那么热爱翻译作品、那么关注世界文坛。虽然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也不必过于焦虑,但确实也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写作,是否受到了浮躁、喧嚣的影响。跟风式、揣摩式、趋利式写作是多年的风气,无可厚非,我没有那么清高,但我总想写一些“孤芳自赏”式的小说,心目中理想的小说。吾道不孤,面对世界经典,不忘初心,以它们为标杆,像朝圣一样匍匐前行。自然,越往前越艰难,越孤独,要不断自加“难度”。走平坦的路、走下坡路是容易的,遇到难关、险关绕道走就是了,这样的写作有意义吗?值得我们去努力一辈子吗?
林 森:最后一个问题,我发现你经常回到你的老家北流,经常跟老伙计一起玩,很松弛的状态,这是因为专业作家相对松弛的时间管理所带来的“福利”吗?反正,对于我来讲,被困于编辑工作与日常生活,常常有没法抽身的疲惫感,你怎么看待目前自己的生活状态?换句话说,你建不建议我也找个地方去当一当专业作家?
朱山坡:我现在是专业作家,相对自由多了,因此经常回老家跟那帮喜欢文学、曾经一起捣鼓诗社的老伙计一起,喝喝茶,蹲路边摊吃碗猪杂粉,去大排档喝点小酒,聊聊世事家常,也聊点文学,互相打打气,互相提醒“保命第一,写作第二”。有时候到乡下去闲逛,看看残存的儿时痕迹。如果有空,我便想回家看看,可能是到了思乡怀旧的年纪。有时候觉得多写一篇少写一篇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也改变不了什么,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我理解你现在的状态,中年人的疲惫,左肩右肩都压着担子,扛着很累,撒手又可惜,甚至无从撒手。但当专业作家也并非完美的选择,专业写作相当于“退休”状态,与文学现场慢慢会疏离,甚至接触的人都会越来越少,时间管理全靠自觉,慢慢就会过于松弛,对个人的自控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人到中年,任何选择都有得有失。有时候,我竟然认为写作跟时间关系不太大,关键还是靠才华。给再多的时间和自由未必能写出好作品。产量高也是才华的一部分,我们经常以某某某先生为例,就此早已经达成共识。因此,虽然你才华横溢,但我并不建议你在是否“专业”上过于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