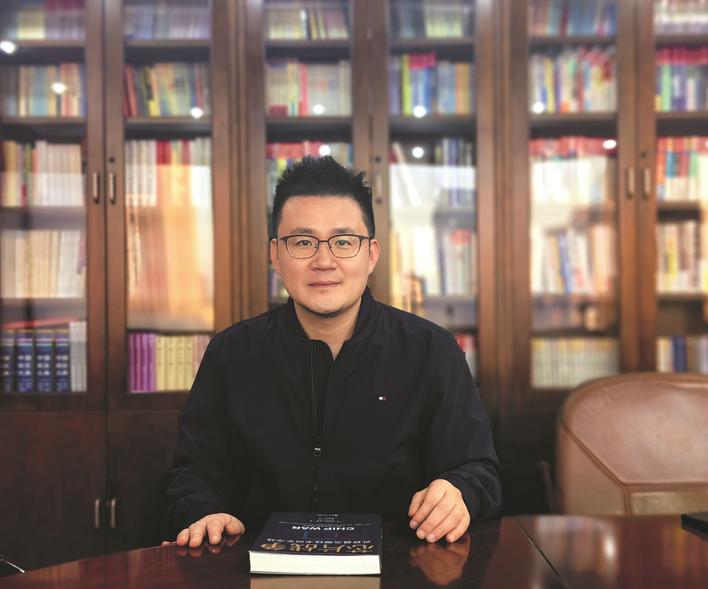作为一个2002年入职出版社的编辑,入行也算久了。编辑的本职工作是帮人出书,属于替人作嫁衣的。图书市场这个大舞台,最璀璨的光芒肯定是聚焦在作者身上的;而编辑只能躲在幕后,不能喧宾夺主。读者看了一本书,可能会产生冲动见见作者,但不会癫狂地要去见那本书的责任编辑。套用钱锺书的话说,觉得这个鸡蛋好吃,想见那只下蛋的母鸡还是可理解的,要去见那个垒鸡窝的人就有点不可救药了。
可出身于中文系,我身上总有一股创造的冲动,四年学术科班训练的折磨,常年柴米油盐的繁琐,都磨不去这股劲。看创作的舞台上,人头攒动,便也想着从幕后冲出来,唱两句,舞两段。这便是一个编辑的写作梦。有时,我还常有这么个歪理——一个不想当作家的编辑不是个好编辑。
我最早进的是教育出版社,干的是小学语文学科图书的编辑,整整十年,日复一日跟拼音字母和那一千个常用字较劲。这活,但凡高中毕业,认真负责点,都能干得好。我痛感年华虚度,但又无力挣扎。就这样,偶然间混到了天涯社区。
天涯那时确实藏龙卧虎,煮酒版块是专攻大众历史写作的,一群历史票友在里头纵横古今。那时赫连勃勃大王是台柱子,后来当年明月风头更劲,都是在那里连载自己的文章。我选择了南北朝,以北魏、北齐、梁(陈)的人物和故事作为切口,写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还自作聪明地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二个三国鼎立时期,取了个名字叫《后三国风云》。以我当时的市场感觉看,以为日后能大卖,因为从古至今没人写过这样的选题。但后来事实上打了脸,大部分读者对南北朝历史都模糊不清,你又闭门造车自创了一个“后三国”概念,那更是云里雾里。认定方向后,我便大量购买相关书籍,囤积了《资治通鉴》《北史》《南史》等一堆史料著作,加起来有百十来本了。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写2000字,天涯上的网友每天会催促你更新,这也是写作的动力。白天,昏头昏脑地在单位里跟“a、o、e”死磕;晚上回到书房,便进入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这种冲突的撕裂感还是很强烈的。
每天都是晚上8点开始写作,常规是到12点,晚点也会磨到凌晨1点。每天笔耕2000字,除特殊情况外,几乎雷打不动。每次写完,便到阳台上小坐。我家在17楼,四周并无高楼,能俯瞰到整个滨江。那时万家灯火已灭,夜静寂、深沉得和我笔下的那段历史一样,根本看不到光亮。
日复一日,共写了60万字。写到十来万字的时候,磨铁的一个编辑便来签约了。那时的条件尚可,像我这种素人作者,都能给到首印15000册,8个点的版税。辛苦劳作了一年半,上下两册都出了,拿到了七八万块钱,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不过,这一年半下来,把我写伤了。最后定稿那天,我关上书房的门,大声呼喊着,把校订完的书稿向上空扬去,纸片如雪般纷纷飘落,算是跟那段沉重的时光作了郑重的告别。我感觉靠写书挣钱,养家糊口,这事太不靠谱——不是人人都有当年明月那种讲故事的天赋。我老老实实又回到编辑本行,继续充当小学生的良师益友,小心翼翼地处理他们的来信——敬爱的赵波爷爷,您责编的这本书有个地方错了,把里头的小猴画成了小狗。
到了2011年,《南方都市报》的吕卓编辑又来约稿。说是要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一个专栏,叫“公司社会”栏目,以历史为依托来讲管理,把公司组织中的一些概念,比如“职业经理人”“CEO”等融入到历史事件中去,从而给现代公司人、公司高管以启示。《南方都市报》是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都市报,影响力很大,给出的稿酬也很有诱惑,特稿千字400元。当时省里的报纸也就到千字80元。我这人格局一向不大,这种名利双收的事当然不能错过。最为关键的是,不像在天涯上写连载,天天被捆得跟阳澄湖的大闸蟹一样,毫无自由,这可以随时脱身,重返江湖。
我又重操旧业,写了《项羽之败:一己之力独扛天下,创业团队分崩离析》这样的一堆文章。后来跟其他作者的文章一起,结集成册,也是在磨铁出的,而且取了个很“磨铁”的名字——《公司就是朝廷》。这回比较幸运,既拿了报社的稿费,还能从出版商那里再拿点版税,算是一鱼两吃。
跟南都的专栏分别后,我就愈加懒得动笔了。白日里诸事繁杂,到家已是筋疲力尽。精力好时,还能翻下书;状态不好时,夜里的时间就被今日头条和短视频完全占据。写作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这时的我,年近不惑,髀肉复生,已安心当一个编辑,离创作的梦想越来越远了。过了几年,我到了集团的行政部门工作,跟出版一线也隔膜了起来。
2022年,“浙江宣传”公众号横空出世。头条是那种时政类的大文章,二条类似于副刊风格,主要写点人文历史和地方风物。我已弃笔多年,这时又手痒了起来,开始为其供稿。我擅长的还是文史人物,写一个人物或者某个事件,然后带出点对当下的启示。断断续续、零零散散,一两年下来大约写了40篇。一次全省文宣系统的大会,一位领导夸我的文章写得好,这让我在行业里赢了点浮名。
回首我这十来年的创作史,是屡败屡战,一直行走在素人作者的边沿,离真正的作家梦很是遥远。我有个大学同学叫善水,也用业余时间搞网文创作,就熬成网文大神了,还拿了“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每个人禀赋不同,赛道不一,所以结果也不同。
我一直认为,如果从文字的天赋语感来讲,一等人搞创作,二等人搞研究,三等人搞出版。比如曹雪芹、鲁迅、张爱玲,他们的文字天赋是老天爷赏饭吃,真的是妙笔生花。而做研究的人,写起学术文章来字斟句酌、法度森严,但要写起轻巧灵动的文学作品来,就会变得四肢僵硬、动作变形。我上大学时,有个文艺理论专业的教授,学问做得极好,我一向敬重。有一日,他兴奋地捧着一堆散文请我欣赏。我快速读完后,连忙恭维一番:老师,您儿子才读高中,但散文水平已露峥嵘,以后必成大家。从此,这老师就再也没理过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佳作不是他儿子的,是他自己呕心沥血的创作。所以文字语感的天堑就横在那里,靠后天的努力是难以跨越的,即便你能写好玄之又玄的文艺理论,却写不好家长里短的小散文。
比起学者来,出版人的文字能力更弱。在文字的天地里,出版人是眼高手低的,改起别人的文字可以大刀阔斧、纵横捭阖,一旦自己写起文字来,那很多是佶屈聱牙、不忍卒读的。出版人对文字最大的贡献是让作品变得“规范”,几十年修炼的是啄木鸟一样捉虫的功夫,躲在幕后还行,真到台上摆起身段来,那也是呆若木鸡的。
因为生产方式的变化,现在的编辑是职业化的,擅长于流水线的生产;而过往的编辑,是专业化的,很多本身就是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如岳麓书社的唐浩明,就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变成创作《曾国藩》历史小说的大作家了。作为一个出版人,为啥我老是丢不下创作的情结?因为我觉得,唯有多写多练,自己对文字有感觉了,才能辨识好文字,约到好作家,出版好作品。这是一个编辑对文字的底线功夫。
当年出版《后三国风云》时,我曾给自己如此画像:“江南人,与书结缘。编书养家糊口,写书娱人悦己,读书磨时度日。”今日虽已从一个小编辑成长为总编辑了,但当初的定位依然不变。出版依然是我的主业,是安身立命所在,必须全力以赴;但闲暇之余,手中那支笔依然不能放下。编辑帮别人出好书,是责无旁贷,是最硬核的实力体现,也是职业的价值所在;而编辑自己能写好书,是锦上添花,能带来别样的成就和满足。
编辑的一生,是神圣又卑微的,是热闹又寂寞的。出版的大舞台流光溢彩,万众瞩目,所有的热闹和掌声都给了作者——确实也本该如此。希望我们的编辑们,在白天做好剧务杂活的同时,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也能笔耕不辍,快意书写,勇敢地从幕后转到台前,在低吟浅唱、眼波流转中绽放一回自己的光芒。
(作者系浙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