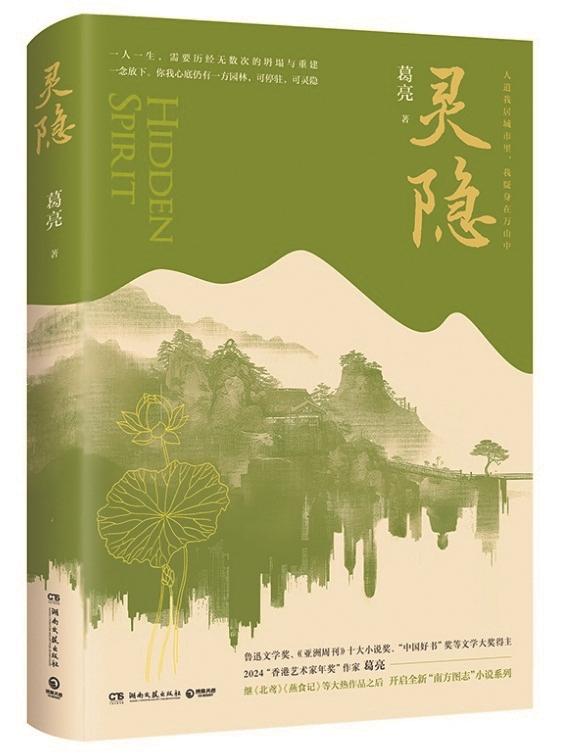□汤 俏
近年来,葛亮的每部作品都在创作旨归和叙事范式上更迭演进、力求突破。此前的“家国三部曲”《朱雀》《北鸢》《燕食记》,皆以呈现历史传奇人物身世及家族薪火存续为线索,以宏阔笔力见证时代风云兴变、聚散流徙,描摹出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世态人情的雄浑画卷。新作《灵隐》则宕开一笔,以独特的双线叙事结构、深入人物心理动因的追索和丰富的地域文化元素,既接续了《燕食记》以来的岭南文化脉络,又别有一番风貌。正如葛亮自己所说:“《灵隐》这部作品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南方图志’写作系列……它更回归和关注于人本身,在人物命运交叠中塑造了一种别样的历史演绎方式。”小说以“父篇:浮图”和“女篇:灵隐”相对应,又缀以“番外:侧拱时期的莲花”,在叙事上形成彼此呼应的美学空间,内容上则以南华大学教授连粤名及其女儿连思睿的命运轨迹为主线,细腻描绘了历史长河中的个人沉浮与社会变迁,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看似波澜不兴,实则暗流涌动、变动不居的社会画卷,更以对个人史、微观史的观照切入人间烟火,精致里见出宏大,轻盈中托出浑厚。
扉页题着元代禅师惟则的诗句“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颇有全书题眼之意。葛亮并不讳言,《灵隐》的创作灵感与现代人的心境相关。香港在更多人眼里,是一个充满现代性的国际化大都市,但葛亮似乎总是执着于将目光投向中环那鳞次栉比的高楼之外的浓郁烟火之气,从香港现代性的罅隙中去发掘一如古都南京深藏的历史感。比如《灵隐》中写到的太平清醮、猴王诞等古老节庆,还有女篇中一再提到的“香港也有座灵隐寺”。
立足岭南不断北望江南、呈现某种文化对位的写作姿态,其实是葛亮多年来在其香港写作中始终坚持表现的香港这座城市古老与现代兼容并存的特质。葛亮认为,这是香港人对历史抱持的独一份“天然的敏感和尊重”,只要你愿意,永远能在香港那些逼仄的空间里找到压缩得满满当当的历史。看葛亮笔下的故事,总能深深感喟,市井罅隙里的人情世故往往最具打动人心的力量。“当人们身处闹市中的一方园林时,恍然发现四周全是高楼,会油然生出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虚幻与孤独。”而如何守住你我心底的那一方园林和净土,在那里游历,在那里呼吸,可能需要历经无数次的坍塌与重建。一念拿起,一念放下,可停驻,亦可灵隐。
小说是以一宗当年震惊港岛的热点事件为切口,通过连粤名和连思睿父女二人互为镜像又彼此缠绕的命运,打开一方人性试炼场,勘察所有入局者多面立体的性格成因与命运走向。在每一次心灵的坍塌与重建中探讨执念与放下、创伤与治愈、和解与告别等话题,也为读者展开一幅从繁华都市到偏远村落横向绵延、纵向贯穿将近半个世纪的香港社会更迭图景,点染粤港澳乃至闽地百年沧桑变迁史。这正是葛亮一直秉持的微观史观,经由自己的写作指向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来打开时空,在这样博弈和抗衡的演进中呈现更多城市及历史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不确定性。正如蔡崇达所言,葛亮借《灵隐》携带的在大时代的破碎感传达出对人性的细腻深情和悲悯之心。这既是葛亮虽温润平和却自有撼人心魄的力量之所在,也是他自出道以来便一以贯之的创作根柢。《灵隐》虽不同于前作着意表现时代洪流中的家国兴衰,却以其小而美的微观视角观照个体命运浮沉、拓展香港都市书写,从俗世繁华中照见朴实坚定的温暖力量,以人间烟火知著命运如椽中的历史褶皱,纵有破碎荒芜却始终不失明月照大江之辽阔,市井巷陌之声与喃喃梵音在字里行间交错流淌,人性与佛性也在气韵流转中浑然交融,有容乃大,气象万千。
葛亮曾说,所谓“灵隐”,是五千年传统中华文化所沉淀下来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部分,那是“我们中国人缔造心灵的方式”。据此,《灵隐》既是地方史、族群史,亦是心灵史。连粤名由性情温厚、知书达理、处于社会上游的大学教授深陷家庭与伦理漩涡,最后沦落成杀妻犯,而连思睿则经历了爱人变性离世、独子失智、父亲杀害母亲、网络暴力等一系列人生磨折,每一次坍塌都成为她不得不努力重建自我的契机。在连思睿这一系列的磨难与重建当中,林昭与段河这两个角色对她的命运轨迹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不同侧面形成互文。每个人都不得不直面自我最深层的挣扎与痛苦,在命运猛烈的冲击下艰难跋涉,获得成长或者最终放下、自我成全。故事中,除连家父女之外,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袁美珍曾经是一个对爱充满希冀的女子,后来在家庭的经营和女儿的冲突中要强自救,但最终走向精神失常,始终带着原生家庭的伤痛遭逢人世。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条副线。而在段河的家族前史中,金秀与明香一妓一伶生死相托的故事则和《燕食记》中的月傅与荣慧生的故事遥相呼应。弱者罹逢乱世互相扶持并结下深厚情谊,这份韧性和深情正是世纪流转中普通民众之所以绵延不绝的族裔密码,始终是葛亮浓墨重彩书写的中华民族特质。
葛亮以温润如水又自有风骨的文字,对笔下每一位个体选择予以尊重,所谓“不假臧否”“对于世界乃至个体的一种微微仰角的态度”,更是叩问心灵之后难能可贵的理解与圆融。这些特质,自葛亮早期的都市异闻录系列,如《浣熊》,到前几年的《飞发》《燕食记》,已有所体现。《灵隐》接续这一悲悯与风骨兼具的情怀,为当代文学界逐渐丰富的“新南方写作”带来别样的质感。
葛亮以处于多种文化交汇点的国际大都市香港为锚点,辐射粤港澳及闽南地区,有意识地在城市发展的源流中寻找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交融碰撞的多元面貌。借南方所处空间及语言表达上天然的多样性、开放性和流动性,融入自己对于历史现场的思考和表达。在书写个人史、心灵史、器物史和技艺史的过程中,呈现更丰富多元的现代汉语写作,创作出既有古典质感又深具现代性冲突的“南方图志”系列。从《燕食记》到《灵隐》,从同庆楼到春秧街,从连胜街到木桥街,从上海、福建到岭南,葛亮在饮食文化和器物技艺的迁徙流变中敏感地捕捉着命运、时代变迁的图景,以日常人间烟火的磨砺和情感冷暖打通个人经验与时代历史。作家温柔地摩挲着那些在历史褶皱中依然温润有光的“物”,以人世流转的生命实感来构建抵抗文化同质化的文学飞地。
《灵隐》作为葛亮开启“南方图志”系列的一次重要实践,也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他以“物”的重量来沉淀“人”的质感,以尘世老腔通达寺院的梵音,以人间烟火知著百年粤港史,让时代变迁脉络和文化肌理在器物的裂痕与技艺的余温中显影历史神经元,将岭南文化、客家文化等多元文化因子熔铸于市井巷陌的呼吸之间。人类的历史正是在无数次的自我确认中完成螺旋式演进,葛亮以其“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写作,呈现出这种从固定空间到流动载体的转变,勾勒出一幅个体命运与集体记忆交织的图景,恰恰隐喻着岭南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的自我调适,既波澜壮阔又细腻入微,而这正是《灵隐》和葛亮在“新南方写作”中独特的位置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