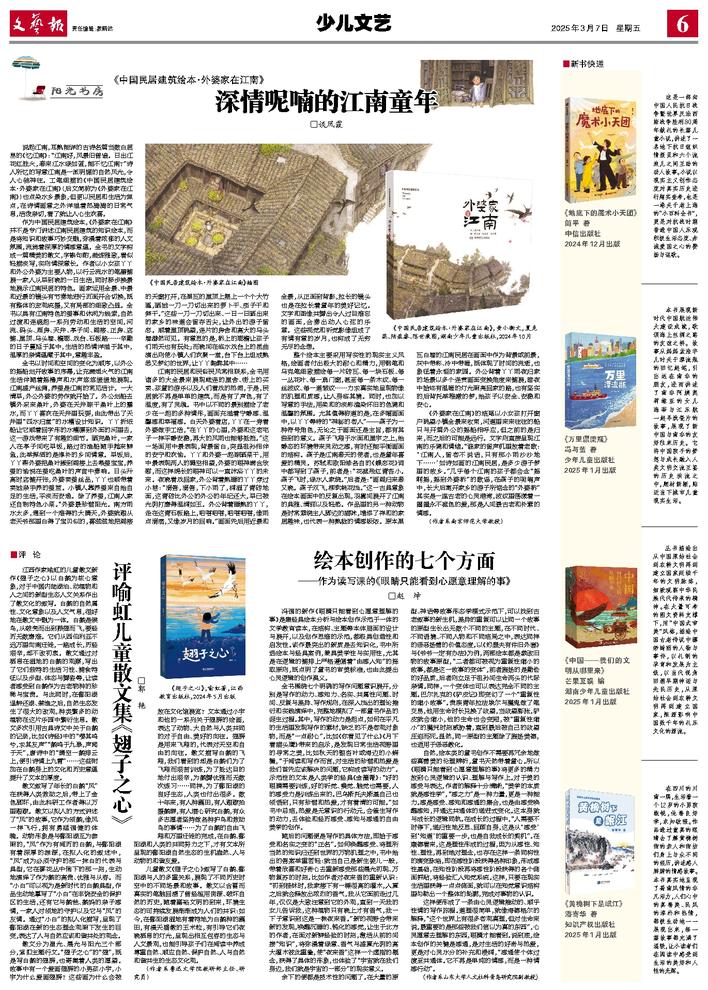冯强的新作《眼睛只能看到心愿意理解的事》是集经典绘本分析与绘本创作示范于一体的文学教育读本,在结构、主题等本体层面的设计与展开,以及创作思维的示范,都极具创造性和启发性。该作最突出的新质是去知识化,书中所选绘本与经典案例,兼具美学性与实用性,尤其是在逻辑的铺排上严格遵循着“由感入知”的择取原则,既点明了童书的审美标准,也由此提出心灵逻辑的创作奥义。
全书围绕七个明确的写作问题意识展开,分别是写作的动力、感知力、名实、共属性问题、时间、反复与差异、写作规则,在深入浅出的理论推衍和实践演绎中,完整地模拟了一部童书作品的诞生过程。其中,写作的动力是起点,如何在平凡的生活里发现写作的素材,缺乏的不是客观对象物,而是“一点耐心”。比如《你看见了什么》《月下看猫头鹰》带来的启示,是发现日常生活视野里的寻常之美,比如秋天的银杏叶或海边的小螃蟹,“于阅读和写作而言,对生活的珍惜和热爱是我们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它构成读写的动力”。示范性的文本是人类学的经典《金蔷薇》:“好的眼睛需要训练,好的听觉、嗅觉、触觉也需要,人的感受力是训练出来的。巴乌斯托夫斯基自己也领悟到,只有珍惜和热爱,才有看清的可能。”如书中总结,热爱是无意识的行动元,会催生写作的动力,去体验和经历感受、感知与感通的自由美学的创作。
随后的问题便是写作的具体方法,即始于感受和名实之变的“正名”。如何唤醒感受、将理所当然的知识归还到世界的万物肌理之中,书中给出的答案举重若轻:就当自己是新生婴儿一般,带着欣喜和好奇心去重新感受那些晨光初现、万物复苏的时刻。比如作者对夜来香的重新认识:“初到桂林时,我家楼下有一棵很高的灌木,入夏之后就会释放出浓烈的香气,我从它面前走过几年,仅仅是大致注意到它的外观,直到一天我的女儿告诉我,这种植物只有晚上才有香气,我一下子意识到这是一株夜来香。”新的视野会带来新的发现,唤醒沉睡的、钝化的感觉,让生于北方的作者,在面对新鲜经验的时刻,激活从前的间接“知识”,将弥漫着绿意、香气与盛夏光阴的高大灌木彼此重叠,使“夜来香”这样一个虚指的概念,获得了具体的形象,也体验了“宇宙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是宇宙的一部分”的现实意义。
余下的便都是技术性的问题了。在大量的原型、神话等故事形态学模式示范下,可以找到古老叙事的新生机,差异的重复可以让同一个故事的原型生长出无数个不同的主题,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不同人物和不同结局之中,表达同样的惩恶扬善的价值态度。以《约瑟夫有件旧外套》与《爷爷一定有办法》为例,两部绘本都是裁改旧物的故事原型,“二者都可被视为重复性缩小的故事,都是这一故事的变体”,前者旌扬的是勤俭的好品质,后者则立足于祖孙间生命两头的代际亲情。同样,一个变体也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主题。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即变幻了一个“重复性的缩小故事”。贵族青年拉法埃尔与魔鬼做了笔交易,他用生命时长兑换了欲望,当欲望膨胀,驴皮就会缩小,他的生命也会变短,被“重复性缩小”的魔咒时刻威胁着,直到最后被自己的欲望压迫而死。显然,同一原型的主题除了旌扬美德,也适用于惩恶教化。
自然,绘本类的童书创作不需要再冗余地做些真善美的伦理辨析,童书天然带着童心。所以《眼睛只能看到心愿意理解的事》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心灵逻辑的认识、理解与写作上。对于美的感受与表达,作者的解释十分清晰,“美学的本质就是感性学”,“感之力”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能力。感是感受、感知和感通的集合,也是由感受唤醒感知,并通达共通体的递进式变化。这本身就与成长的逻辑同轨。在成长的过程中,“人需要不时停下,递归性地反思、回顾自身,这是从‘感受’到‘知道’的重要一步,也是自我成长的契机”。在康德看来,这是理性形成的过程,因为从感性、知性、理性,再到绝对理念,也存在这样一条同构性的演变脉络,即在感性阶段获得各种印象,形成感性基础,在知性阶段再将感性阶段获得的各个侧面拼贴,将经验汇入知觉系统。这样,只要在现实生活里获得一点点侧面,就可以在知觉意识结构里勾勒出一个整体的轮廓,完成对事物的认识。
这样便形成了一条由心灵逻辑推动的、顺乎性情的写作旅程。道理很简单,就像海德格尔的解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客观真理,但对生命来说,最重要的是那些被我们信以为真的东西”,心灵愿意去理解的东西,眼睛才能看到。说到底,绘本创作的关键是感通,是对生活的好奇与热爱,更是对心灵水分的补充和浸润,“感通使个体过渡至共通体。它不再是单纯的情感,而是一种情感行动”。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