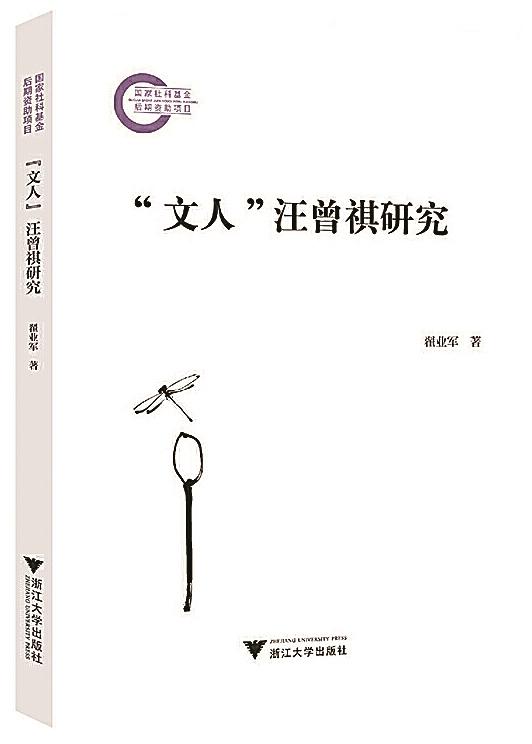提到汪曾祺,从文学界到普通读者几乎都对其倍加推崇。可在经过数十年的经典化过程后,哪怕是“好处说好”,也很难有大的推进空间。此种情形下,翟业军的新著《“文人”汪曾祺研究》读来却令人击节赞赏。书中所呈现的汪曾祺,或许不全是崭新的,却一定比我们习见的汪曾祺形象更加本真、立体,且丰饶多姿。
《“文人”汪曾祺研究》没有局限于汪曾祺的新文学创作,而将视域扩容至汪氏所热衷的戏曲、书法、绘画甚至美食等过去不大被关注的方面,考察这些艺事与其创作如何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展示汪曾祺作为杂家、通才的魅力,即一个“文人”形象。翟业军认为,“有情的人间”实乃“文人”汪曾祺之于世界最美的馈赠,“倘若只是着眼于他的文学创作,就只能看到有情的人间之一角而已”。而将这些零散的领域连缀起来的,是著者和所论对象共有的对人、对世界的一汪深情。
“情”是汪曾祺身上最显著的标签,人们最为熟悉的是他在新时期复出后以《受戒》《大淖记事》为代表的那些所谓表现人情人性之美的小说,这些小说奠定了几代读者对他“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印象。作者擅长细致的文本分析,痴迷于挖掘文本深层更多层次的意蕴。通过他的探究,我们体会到了《受戒》这杯“不凉不烫的清茶”对国人内心的慰藉,为巧云、十一子即便身处苦难仍能绽放生命力量而感动,也会为《异秉》《八千岁》中由一块块熏烧、一把把糙米所构筑的市民社会的细碎与庄严而赞叹。于是我们发现,优美冲淡不过是表象,这个“有情的人间”首先建立在生命的韧性和厚重之上。“情”同样体现在汪氏书画里洋溢着生之欢欣的凡俗草木,以及沸腾于他笔端和灶台的令人垂涎的家常美食中,它们与其文学创作相互呼应,寄寓着汪曾祺在这一阶段将日常世界艺术化的审美理想。
然而,“有情的人间”并非总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式的温暖。深入了解汪曾祺,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看待他年逾古稀后那些越写越简短、也越写越枯瘦的小说,这些小说似乎对此前的抒情世界构成了消解和颠覆。作者从文本的症候罅隙处入手,逐一探秘《鹿井丹泉》中的人兽相恋缘何“极美丽”,《薛大娘》中直白大胆的性事背后人性的舒展和解放。作者还注意到了汪曾祺暮年作画用墨的变化,由“萧萧”转为“鲜浓”,这一转变不单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没有“老透”,更是要以最淋漓的色彩抵抗即将来临的“彻底的虚”,“意欲于万千色相中展现生命的飞扬和恣肆”。
难得的是,全书的语言也随着论题的转换而有所变化。当分析那部分重现纯美的高邮旧梦的小说时,行文如舒缓的小夜曲般潺潺流淌;随着作家的目光投向现世烟火,作者的笔触则变得相对绵密、亲切且幽默,从中能嗅出洋溢在王二、八千岁们周身那种“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让人看到躲在后面观察这一切的汪曾祺那副天真、妩媚又带着点狡黠的模样。其余诸如探寻汪曾祺一心从《聊斋》翻出新义却不被理解的孤愤,以及对旧戏进行雅化背后的紧张焦灼,皆可谓知人之论。
作者在本书中有意避开理论的窠臼,多从汪曾祺更为浸润其中的中国古典文学源流展开论析。他在面对这一与他渊源最深的研究对象时,放下了锋锐的“匕首”,始终用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去感知、贴近,这也是研究者个人生命逐步成长的过程。如论及汪曾祺改写《黄英》“醉陶”一节时,感受到“最好的我”与“最好的他们”(汪曾祺和蒲松龄)的相遇;有忧伤,如从《侯银匠》这篇不太被人注意的小说中,体会到全天下父女间明明深重、却只能表现为淡而远的亲情;更有痛楚,如前面提到当看懂汪曾祺遗墨里对世界“说不出口的再见”时的悲痛难抑,又或者从改写后的《促织》结尾中,感受到对所爱者及自身命运的无力,以至于突然“嚎啕大哭”。此般将自我全情投入、熔铸了个人生命体验的研究,或许缺乏审视的距离和冷静,但却不失为走近汪曾祺这样一个至情之人的有效路径。
翟业军在“后记之一”中追索了本书写作近20年光阴里的个人心路:“当我看十多年前的文章时,仍然觉得新鲜,仍然能感动于当年写作时的感动,它们好像并不过时。我知道,我和我的书都是年轻的。”话语间流淌着温热的感情与平静的自信。在“后记之二”里,翟业军又坦言自己始终无法系统地讨论汪曾祺从而写出一本“专著”来,只好让这本书呈现为“非书之书”的形态。的确,像汪曾祺这般鲜活丰富,怎能用条理分明的逻辑来梳理和解释呢?因此,这本书必然是一本缠绕的、重复的,既相互说明又彼此驳斥的“非书之书”,但其内部却是交织回旋、谐和无间的。恰如汪曾祺对语言的比喻:“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翟业军的这十几篇文章亦是这般相互滋养,抽条开花,构建出了一个趋向完整的“文人”汪曾祺形象。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