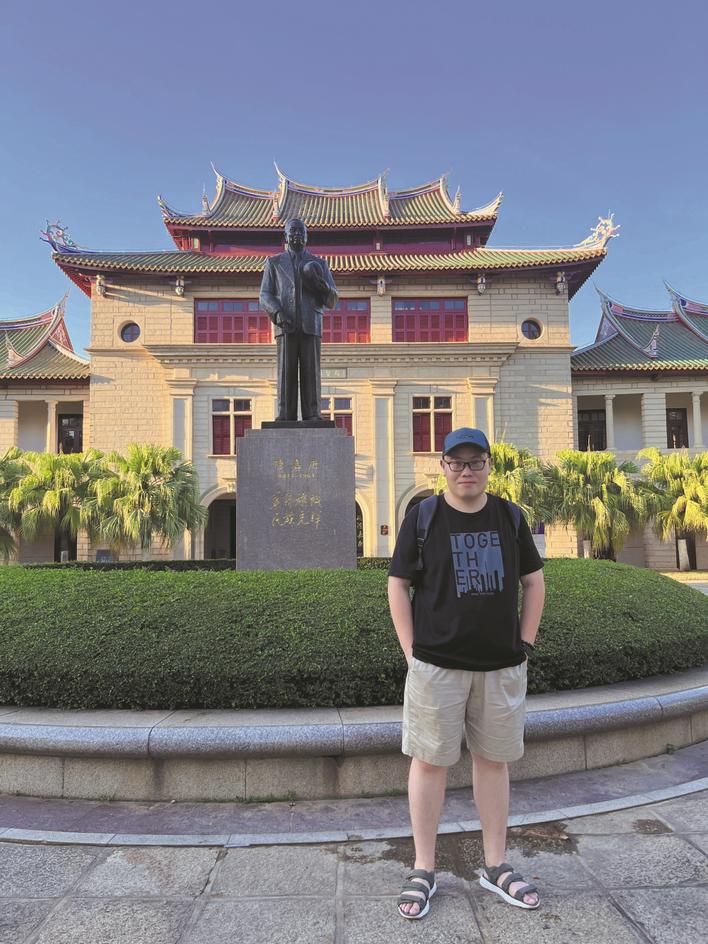顾奕俊是个天生的文学批评家。这倒不是说他眼下已技艺精湛、成绩斐然,而是想特别指出,批评家群体里很少有像顾奕俊这样的:当其人生不期然地与文学发生链接时,他几乎是不假思索、毅然决然地举意以文学批评为志业。他似乎没有那个试图通过涂鸦诗歌或小说来接近文学荣耀的“文青”阶段——他利索地掠过了这个阶段,像掠过青春期一样,眉眼和笔墨都早早地隐有苍色。他学生时代就勤勉、善思、健谈,一副随时随地准备发起提问和讨论的兴奋样态,聆听教诲时则面色凝重,尊师贵道的恭然、心领神会的释然和不屑苟同的默然,交叠浮现。对文学批评的热爱,使他对一个普通青年人的常规生活内容进行了大幅删削,阅读、写作和不定期的思想聚谈几乎占去了他日常结构的所有实地。但这枯澹的日常显然丝毫无损于他的热气腾腾和兴致勃勃,他常态性地敏思和健谈,提问和讨论的兴奋,浓郁如故。作家、作品、思潮、史迹,这诸多的“文类”,依着他的理解和意图一帧一帧地打开或折叠,这重建的话语楼宇,新定的意义疆域,使他流连其间,自喜不已。或许,阐释的妙趣,是他投身、沉迷于文学批评并矢志不渝的最大理由。
顾奕俊迄今为止最主要的批评工作集中在对当代作家作品的阐释。他的阅读胃口颇大,不到30岁的年龄,已发表了30多位作家作品的专论文章。他偏重于关注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年作家,关注他们的破壳与成长,关注他们的步态与走向,与此同时,他也密切关注仍有强劲的写作输出并饶有号召力的前辈作家。他强烈的“现场感”和“时代感”由此可见一斑。在对一些作家的单篇作品解读时,他善于捕捉作品的某个“线头”——有时来自作家言谈间的无意披露,有时则缘于他对文本织体高度细致的摩挲,经由这个“线头”的提拉来拆解文本,从而见出这个织体的别致针脚或针法。他缘此对三三、王苏辛、朱婧等人的小说解读,令我印象深刻。他的评论文章里也时有对原著核心情节的重述,但他的“重述”并非对原著故事的复刻或缩写,而是依据他的阐释逻辑对原有情节元素进行重组,这包括对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重新设定,对人物命运和故事脉络的全新推导。与那些通过复述故事而滥充篇幅的注水文章不同,顾奕俊的“重述”所制造的刻意偏离,总是能撑开一个新的意义空间,使人对原著的理解陡然多出一个异质的叙事参照,一个鞭辟入里的认知切口。这样的批评技艺,其实很考验评论者的阅读积累和审美悟性。顾奕俊借此展示了他开阔的知识视野、多元的理论资源、致密的诗性感悟,以及细读细绎的诚恳和扎实。若要成就一个出色的批评家,上述种种皆为可贵的品质。
顾奕俊勤奋、多产,却不给人逞才汲宠、轻薄为文的佻达感,相反,他的文章多有苦吟之色。他虽也追求纵横捭阖的文章气象,但衍为文字,则处处审慎,出言谨重。这尤其典型地表现在对一些已然大器的作家,如王安忆、毕飞宇等人的评述上。比如《吃饭、算账与“一条向上的斜行线”——论王安忆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一文,虽是对一部长篇新作的应时快评,他硬是将王安忆40多年的创作序列进行了谱系式的呈现,据此说明王安忆的这部新作何以令人感佩地处在“一条向上的斜行线上”,以及它当下所处的历史高点对于王安忆本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所深具的突破性意义。这是一次复杂的、步步为营的谨严论证。它同时也是一次艰巨的体力考验。王安忆的写作之勤,天下无双,沿着那条向上的斜行线谱系式地通读王安忆的浩繁卷帙,对于一篇应时快评来说,“苦吟”二字恐已难呈其辛。
读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我读到了后英雄时代的凡俗和庸常,读到了“英雄”与后两者总是并举又彼此消解的荒谬,读到了平静之下的悚栗,悲怆之上的虚无,行动之中的无力,清醒之后的苍茫。顾奕俊则捻出“吃饭”“算账”的线头,于无常的世道雾幛下牵出对生命中恒常之具的浩叹。虽然都触及某个常数,但我们持论的动机已在殊途。某些不易分享的历史记忆不由分说地、确凿地在批评家之间划出了代际线。然而,也正是这篇文章,它抱朴的方法,守拙的逻辑,使我难捺对其结论之外诸方的激赏。单是他对王安忆通过对自己的文学经验和创作积累的“算账”而不断垫升高度的喻说,就是颇可称道的才识。只不过,即便是在文章里,他的才情也常被诚恳和谦逊所蕴藉。但是,这样的文章——再举一例,《“先锋文学”:何以成为自己的敌人》——让我对顾奕俊的前途有放心感。
顾奕俊并非“野生”的批评家,身上不免学院气。他有时喜欢用音乐转调式的长句,有时就滥用若干个这样的长句来讲述一个用四字成语就可以讲明的道理。对于写作来说,俭省笔墨是一种美德——这个道理可能还需要向他强调。文学批评已是夕阳产业,他们这代批评家说不定是这块窄迫的疆土上最后的骑士,我希望他有刚毅、利索的文字形象,哪怕终究要战败于末日。这才不负自己对文学批评一生的挚爱,也不负这一志业馈赠我们的莫大恩惠。不过,与那些用肃穆的术语和变形的理论块垒砌成“学院感”的文章不同,顾奕俊的文章总体晓畅,鲜有晦涩,且抑扬有节,张弛有度,流溢着热忱的恳切,以及被细加节制的聪慧和激越。他擅在文章中使用比喻,也喜用排比,这些有频度和密度的修辞使他的文章蕴有某种引而不发的、却赏心悦目的文学性。如果说顾奕俊曾像掠过青春期一样掠过了自己的“文青”阶段,那么,顾奕俊的文学批评可以说是他为自己的青春暗留的文学笔记。
(作者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杭州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