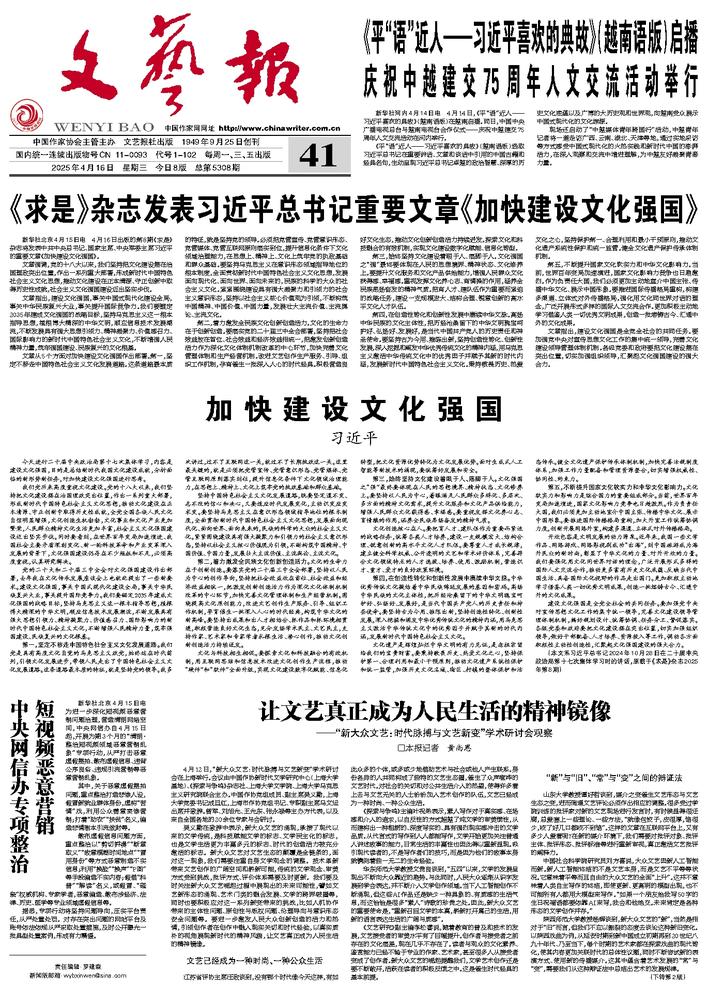□本报记者 黄尚恩
4月12日,“新大众文艺:时代脉搏与文艺新变”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基地)、《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成旦红,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马文运出席并致辞。曾军、刘旭光、王光东、张永禄等主办方代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专家与会研讨。
吴义勤在致辞中表示,新大众文艺的涌现,承接了现代以来的文学传统,是科技赋能文学的标志、文学民主化的标志,也是文学生活更为丰富多元的标志、时代的创造活力被充分激活的标志。新大众文艺对文艺生态的颠覆是全链条的,面对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注重自身文学观念的调整。技术革新带来文艺创作的广阔空间和崭新可能,传统的文学观念、审美方式受到挑战,批评方式、评价体系需要及时更新。我们要及时关注新大众文艺崛起过程中展现出的未来可能性,譬如文艺新形态的涌现、艺术门类的融合发展、文学的跨界破圈等,同时也要积极应对这一系列新变带来的挑战,比如人机协作带来的主体性问题、原创性与版权问题、伦理导向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等。要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创新创造的活力和热情,引领创作者在创作中融入现实关切和时代经验,以真实质朴的视角展现新时代的精神风貌,让文艺真正成为人民生活的精神镜像。
文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公众生活
江苏省评协主席汪政谈到,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有如此众多的个体,或多或少地借助艺术与社会或他人产生联系。身份各异的人共同构成了独特的文艺生态圈,催生了众声喧哗的文艺时代。对社会的关切和对公共生活介入的热望,使得许多看上去与文艺无关的人士纷纷加入艺术创作的队伍,文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公众生活。
《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表示,素人写作对于真实感、在场感和介入的追求,以自反性的方式超越了纯文学的审美惯性,从而建构出一种粗粝的、深度写实的、具有强烈现实感冲击的文学品质。从代言式的写作到人人都能写作,文学开始更加关注普通人讲述故事的能力,日常生活的丰富性也因此得以重新显现。吸引现代读者的,不是写作者们的技巧,而是因为他们的故事本身就镌刻着独一无二的生命经验。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贵良谈到,“五四”以来,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不断向大众靠近的趋势。与此同时,人民大众逐渐从识字发展到学会表达,并不断介入文学创作领域。当下人工智能创作不断涌现,但这些AI作品还是缺少一种具象的、有质感的生活气息,而这恰恰是很多“素人”诗歌的珍贵之处。因此,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使命是,“重新召回文学的本真,崭新打开属己的生活,用新的语言表达生活的广阔与质感”。
《文艺研究》副主编李松睿说,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技术的发展,文艺接受者的审美水平有了巨幅提升。创作者与接受者之前存在的文化落差,现在几乎不存在了。读者与观众的文化素养、鉴赏能力已经不输于专业的作家、艺术家,甚至很多人从接受者变成了创作者。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提醒我们,文学艺术创作还是要不断敞开,活跃在读者的积极反馈之中。这是催生时代经典的基本前提。
“新”与“旧”、“常”与“变”之间的辩证法
山东大学教授谭好哲谈到,媒介之变催生文艺形态与文艺生态之变,进而倒逼文艺评论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很多受过学院训练的批评家对新的文艺现场进行发言时,有时候显得很迂腐,总爱套上一些理论、一些方法,“就像包饺子,皮很厚,馅很少,咬了好几口都咬不到馅”。这样的文章在互联网平台上,又有多少人爱看呢?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我们需要对批评对象、批评主体、批评形态、批评标准等进行重新审视,真正激活文艺批评的阐释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方喜说,大众文艺因新人工智能而新。新人工智能终结的不是文艺本身,而是文艺不平等等状况。它意味着平等而且自由的大众文艺的全面“上升”。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自主写作的终结,即使更新、更高明的模型出现,也不可能所有人都用大模型来写作。“如果一个朋友给我写50字的生日祝福语都要依靠AI来写,我会和他绝交。未来肯定是各种形态的文学创作并存。”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辉谈到,新大众文艺的“新”,当然是相对于“旧”而言,但我们不应以割裂的态度去谈论这种新旧变化。以陕西戏曲为例,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当下,每个时期的艺术家都在探索戏曲的现代转化,使其内容更加关联时代的总体性议题,同时不断尝试新的表演方式、使用新的传播媒介。这其中蕴含着艺术发展的“常”与“变”,需要我们从这种辩证法中总结出艺术的发展规律。
上海大学教授谭旭东认为,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文学性从纸质作品中溢出,成为跨媒介存在的景观。由此,文学作品不仅是个体阅读的对象,而且还通过多媒介转化实现跨界破圈,成为具有公共性的文化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也实现了文化的增值、审美的增值。
强化对新大众文艺的理论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玮认为,大众文艺因技术驱动而产生诸多新变,从网络文学到网络视听,来自各行各业的“草根”创作者加入其中,带来创作风貌的多样化。庞大的用户群体在阅读和观看的过程中,既关注作品的内容,也享受彼此参与、陪伴带来的情感交互。这些作品转向类型化叙事,人物塑造注重“人设”,呈现出互文化、数据化写作的趋向。此外,互联网打破文学、影视、动漫、游戏间的壁垒,各媒介开始共享叙事元素和叙事结构。
上海大学副教授朱羽谈到,当我们谈论一个概念的时候,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坐标系,谈论新大众文艺亦是如此。新大众文艺的建构和命名,隐含着命名者对现实之变、技术之变和时代远景的关注。在这之中,我们尤其需要关注文艺如何发挥其“受感致动”的作用,即文艺如何影响受众的身心力量,进而引发相应的实践活动。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助理教授吉云飞说,新大众文艺是一个很有生产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现实对象蕴藏着巨大能量。它牵扯到很多的话题、命题,能够让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坐在一起,并产生交流的欲望,进而建立起某种关联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把钥匙,一把打通20世纪和21世纪中国文艺的钥匙。
上海大学讲师王玮旭谈到,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很多人都提到了诗歌。新媒介的确让诗歌获得了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不仅体现为诗歌传播范围的扩大,还体现在诗歌文本内部的新变上。比如在互联网上,大家通过“回复/仿写”“融梗”“歌谣化”等手段,推动了诗歌形式的网络化,而这种形式本身内蕴着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