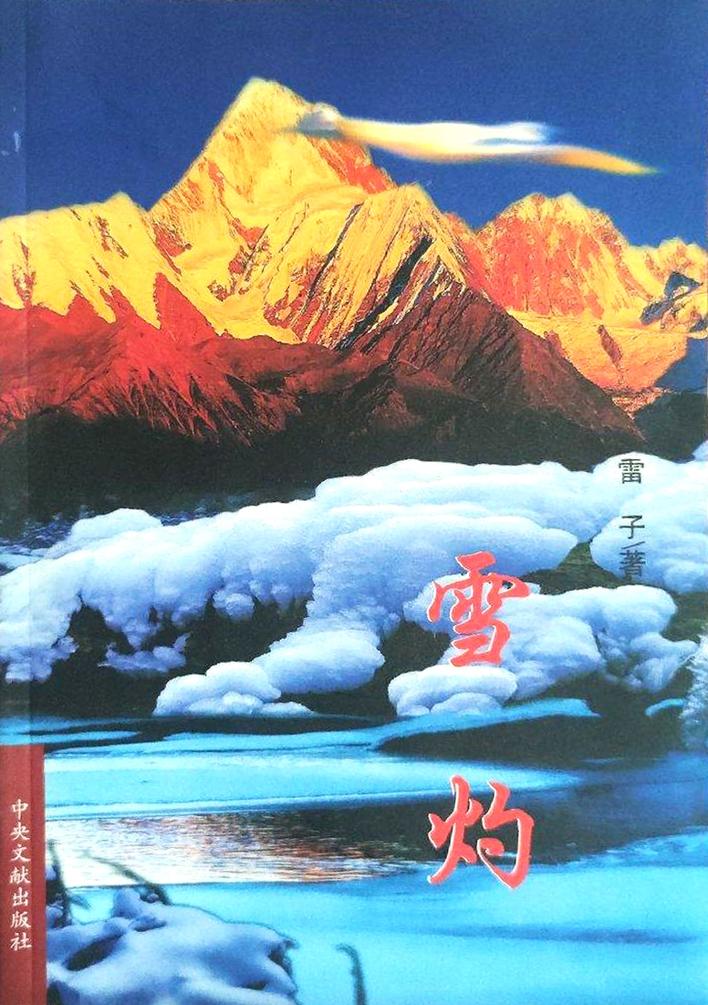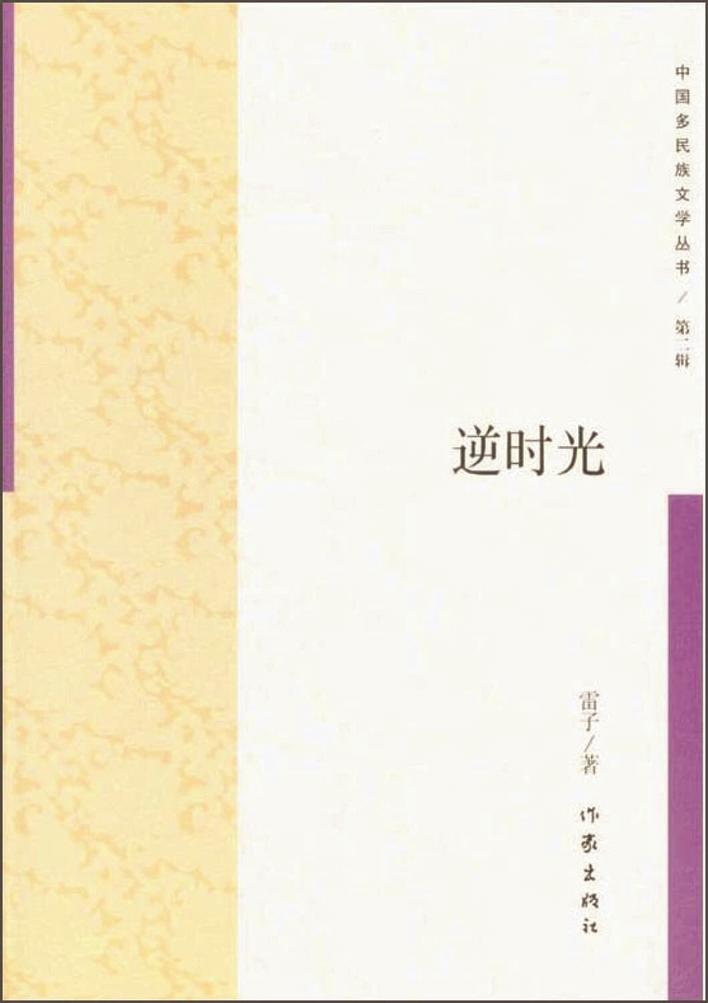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环境中,当代民族文学发展呈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西藏新小说”创作者、“康巴作家群”和“大凉山诗人群”等作家群体在文坛的亮相,以及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的涌现,都是当代民族文学繁荣的见证。在此背景下,羌族这一古老的民族也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先后有雷子、羊子、羌人六三位作家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代羌族文学的重要特点,本文旨在以羌族诗人雷子的创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羌族诗歌中的具体表现。
雷子,原名雷耀琼,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1985年开始写诗,曾在《民族文学》《草地》《羌族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诗集《雪灼》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雷子的诗歌具有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民族观念,华夏几千年历史都被她囊括进诗歌世界,在历史沉思和现实关怀之中表达一种既立足于族群又超越族群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其诗具有鲜明的文化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表现为族群与国家的高度统一性。
雷子的诗歌具有鲜明的羌族文化记忆,羊皮鼓、羌绣、口弦、白石、羌红、释比等承载羌族历史记忆的意象是其诗歌中的高频率意象,如《祖灵声纹——记羌族口弦》《羌绣》和《阿坝的石头》。雷子诗歌中的历史文化记忆并不限于羌族,而是具有华夏民族的开阔视野,《写意三生》中的宣纸、狼毫、古砚、紫檀、沉香、紫砂、青玉板、行草、“福”,以及盘古、女娲、伏羲、翼龙、炎帝、蚩尤、大禹,古今文化符号汇聚为不同生命时光的相遇,显示出诗人文化观、族群观的开放性视野。“汉朝马蹄声声入耳/踏进宣纸铺展的雪域/……/你有洞箫,我有横笛/……/永恒是砚,永恒是墨”,呈现出宽广的时空和密集的文化意象,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作者的滋养。
雷子的文化认同于悄然之间展现,显示出文化的日常性:“让我哑然失笑的总是汉字精灵/常常去时光的河畔偷渡/它们藏在东方人的基因里/用方方正正描红的步伐走来/用楷书的 隶书的 仿宋的 草书的/以及所有传神的感觉在宣纸上跳舞”。她的诗作呈现了华夏历史几千年来各族群相遇融合的过程,具有历史整体性。《越过天空的火把》以神话原型以及燃比娃、火种、咒语和火神灯等意象,建构起羌族的“生命起源”图景。《马鞍戒》书写族群之间的生命融合史,“一条基因链在阡陌纵横的联姻里不断结果”。她用诗作追踪家谱,找寻生命基因的源流,发现在长远的历史河流中,族群融合早已难辨彼此,成为生命混合的存在。诗歌《鳛鱼》表达对鳛鱼忍受千年孤独成龙的钦佩向往,“龙的传人”成为生命谱系的最终归属。
雷子诗歌中的族群文化意识及身份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身份认同高度同构,具体表现有二。
一是以红色精神谱系表现族群和国家的同构。“一盏遵义会议的马灯成为不朽的明喻/他被瞻仰了上万次,依然微笑如烛 波澜不惊。”诗歌《革命的马灯》追忆80年前的遵义会议,赞颂革命先贤们扛起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旗,捞起跌落于黑暗中的阳光,驱走暴虐和欺凌。以一盏马灯寓意革命,再忆革命长征,重构革命红色精神。《我是汶川的女儿》中的“神鹰”“神兵”形象,与藏、羌、彝等各民族作家作品中的红军形象共同组成红军百年精神谱系,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建党初心。当年,红军在西南将广大农奴从社会生存链的最底端解救出来,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主人,被百姓奉为“神鹰”“金珠玛米”;21世纪的今天,当边地遭遇灾难之际,也是大批部队官兵不顾自身生命安危,救助灾区人民于水火,再现当年“神鹰”“神兵”风采。雷子在《口述历史》中重现当年红军为阿坝人民“捧出金色黎明”的历史时光,其诗歌中的红色精神谱系是族群之爱和国家之爱的具体展现,是当代中国民族团结的显著标志。
二是在日常性的现实关切中体现家国之爱。诗歌《地税·共和国的血管》追忆周恩来,“我看见山一样的伟人走了/我看见人民永远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豪情提笔写下了四个殷切的大字:中国税务”“四个方块字言尽老一辈革命家/对共和国的祝福和希冀”。从伟人、革命者到平凡人物,凡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都可成为雷子讴歌的对象。她赞扬劳动人民,“像蜜蜂一样辛勤的身影/他们披星戴月/点点滴滴汇成共和国血管里奔腾的血液”。
爱与反思是雷子诗作中有关族群历史记忆的情感双重奏。她将生命苦难升华为一种精神品格,经历了太多苦难的羌人,依然保留对生命美与幸福的渴求,形成了今天爱好和平的羌族面貌,“朴素的银饰将幸福的暗喻在世间渲染”。
在诗集《逆时光》中,雷子对民族国家之爱的表达更为炽热。诗歌《金川有梨花,千朵醉》,以地理版图的大小格局,呈现国家与民族的紧密关联,从梨花的自然之美联想到汉字之美,再延伸至历史深处。“在中国的一隅,在四川的眉梢/在阿坝州的腮帮有个金川的地方”“据说中国的汉字有十万之众/……/神性的汉字可穿越时空/今年我想当它们的导游。”文字是历史文化的直接呈现,具有时光的深广度。语言文字之爱,沉淀着文化之爱。诗歌《中药》以中药串联起中华民族的辉煌与坎坷,表达民族自豪情感,“站起来了/站起来一个新中国”“每一个药名都诉说着/五千年的盛衰与痛楚”,体现出面对中西文化交汇时的危机意识以及对民族与国家的深沉爱恋。
雷子诗歌中的文学主体“我”,既是个体也是群体。作为个体的文学主体总有些虚无缥缈,呈现出一种矛盾性,如《在风中》中的“我”是被遗忘的废墟,是野茫茫的月光,《一头年兽的忧伤》中的“我”从唐朝逃亡到今天,《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我”只有一颗彻夜叫嚣的灵魂。而当文学主体从个体转变为群体时,“我”在民族国家之爱中有了归属感。
“我是汶川的女儿/我的命运与岷山汶水一脉相连/……/汶川的儿女不哭泣/怀一颗感恩的心铭记/重建家园的路上我们没有独行/牵着四面八方援助的手啊,满怀信心/一个云朵上的民族唱响希望的壮歌前行/无畏地前行!”
“汶川的女儿”显示了雷子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即族群和国家的同构。作为人生中遭遇的重大事件,汶川大地震甚至影响了诗人的诗学观和价值观。在2008年的汶川,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部队官兵和众多志愿者们带来了爱与力量。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经历地震灾害后写成的诗集《逆时光》,其中的民族国家书写较《雪灼》更具宽广性和人性光辉。
雷子的创作体现了羌人的典型性格,乐观开朗,敏感多思,勤奋执着,以感恩之心对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正如她在骏马奖获奖感言中所说的:“这个奖不是给我的,而是颁给整个羌族人民的。我庆幸自己还活着,祖国人民在这种时候给了我们更多的关爱,给了我们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我被全国人民的大爱之举深深感动,我要好好地活着,继续写作。”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2025年中央高校项目“共同体视野下的当代巴蜀文学研究”(2025SZL12)中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