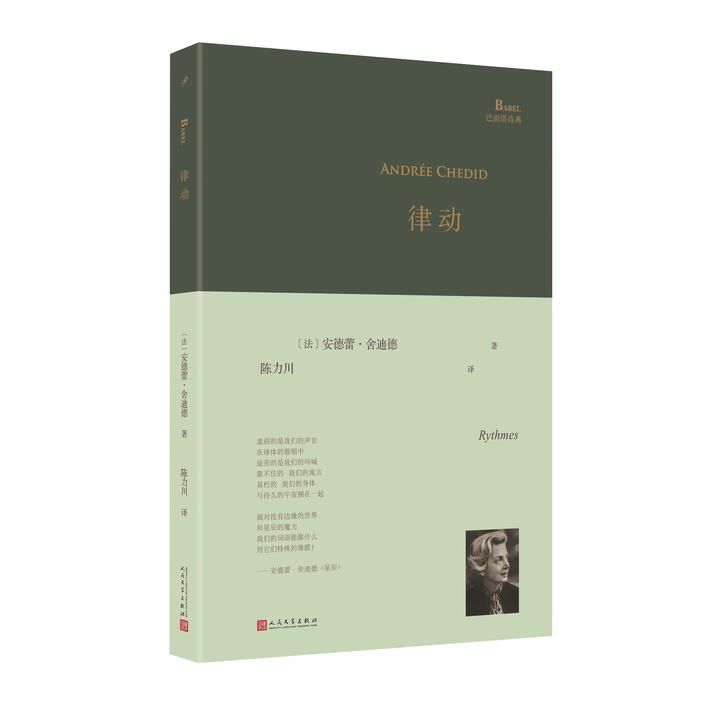和八十多岁出版《白鹭》的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不同,同样也是在耄耋之年出版了诗集《律动》的安德蕾·舍迪德,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自我与外部对象的关系上,自身具体的生活经验也甚少出现在笔下,她全神贯注于内心的精神内容,因而她的诗写得更为抽象也更为直接,无论探讨时间还是谈论死亡,她都毫不掩饰充满“律动”的内心活力,有着生气勃勃的激情去呼应着宇宙运动的节奏。
安德蕾·舍迪德,1920年出生于开罗,其父母分别是黎巴嫩和叙利亚人。她自幼学习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二十多岁时结婚后移居巴黎。1943年,她的第一本英文诗集出版。据译者陈力川先生提供的生平介绍,她的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戏剧、评论和儿童文学,并曾获得马拉美奖、龚古尔诗歌奖。这位被法国前文化部长称赞为“一位光彩熠熠、有心肠、有思想、有信誉”的女诗人,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成绩卓然,她的子女和孙辈中还出了六位艺术家,他们是画家、歌手和导演。国内对舍迪德诗作的翻译介绍非常少,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律动》,可使汉语读者得以了解这位黎巴嫩裔法国诗人晚年诗歌创作的面貌。
伽利玛出版社诗刊主编让-皮埃尔·西梅翁在本书序言中盛赞舍迪德这部诗集是“关于世界和人类生存思想的闪光的总结,舍迪德的全部都蕴含在她对生命始终不渝的激情之中,她毫不犹豫地赞美大写的生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非常好奇那些重要作家、诗人在衰老之年对于生命和死亡的看法。按照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对于作家和艺术家“晚期风格”的描述,在相当多作品中可以发现“超凡脱俗的宁静”。这令我想起诗人米沃什那首著名的《礼物》,这是他年近九十时的作品。在抛却了一切恩怨得失、搁下痛苦往事之后,“尘世中没有什么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人值得我去妒忌。/无论我遭受了怎样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我的身体里没有疼痛。/直起腰,我看见蓝色的海和白帆”。这首诗符合萨义德所说的“毕生的美学努力臻于圆满”的情形。事实上,米沃什晚年的诗集《第二空间》中也充满了对生死的探寻,那是宗教意义上的思考和怀疑,也如其所言“写作是一种持久不变的抗争”,但舍迪德显然跳出了宗教,而是从整个宇宙生生不息的背景中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她在本书第一章“律动”中以“不信神不信教”的态度写到:
凡生命/皆开启/神秘
凡神秘/皆蒙着/黑暗
凡黑暗/皆承载/希望
凡希望/皆服从/生命
这几行诗概括了舍迪德对于生命和未知世界的看法以及对两者关系的思考,并由此在本章的结尾处写出“短暂的栖居/为了种植/未来的麦子”。这是一大段以宇宙大爆炸开始的无题诗,她以生命的名义赞颂对所有暴力奴役“不效忠”的自由,包括对死亡否定生命价值的抵抗。在她看来,一切无序的现实,溃败和散落的喧嚣,在天地自然之中如洪水翻涌,从中“突然冒出/生命的漩涡”——这个脆弱的、渺小的生灵,却能够从无序的杂乱中挣脱,“借助生命和词语/动作和画面”,延续着对于虚无的抗争。她将这样的力量归于词语和思想活动,因为符号、声音和诗的言说“使地平线增多”,因为诗也在言说那不可言说之物,“比饥渴更顽固/比风更自由”。
我惊讶于高龄的舍迪德思维的缜密与精神世界的辽阔。当她在诗中通过写出自我而演奏生命的乐章、寻找生命的意义时,她发现语言和诗不仅否定了时间、激活了思想,同时也向她昭示“另一种现实”,那是与我们所能感知的物理时空不同的存在——既神秘又平常,既有可能磨灭人类的向往,也有可能使人类的认知得以解放。毋庸讳言,进入老年的人不会不想到肉体的易朽。米沃什也曾在访谈中说过他“为生命即将结束而感到悲伤”,但在舍迪德的诗中,有的只是对自我冷静的观察和对生命毫无保留的赞美,即使是面临死亡的生命。在她看来,一个人的身体,就是造就一个生命的各种因素的连结点,当它们开始回收那些诞育生命的时刻,生命便化作“太阳或夜”,即另一重的时间,也因此战胜了昙花一现的命运。在延续了第二章“词语的源头”后的第三章“这个身体”中,舍迪德有条不紊地展开她对于有限生命朝向“非现时生命”的思索,并笃定地抛却“人造的和虚幻的时间”,因为“生命在变形中”早已跨越界限和人类有限的理性。
正如节日的存在是人类所创造的、打断时间连续性的时间一样,人的一生中也会有许多跳出时间之流的某些时刻或瞬间。在那些罕见的时刻,人是忘我的,也是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她或者他,会深深感受到自己寓居于万物内在之中,单个的生命本就是宇宙永恒运动的一部分——
我赞美你 啊 生命
在洞穴和梦之间
渴求的间歇
介于空和无
舍迪德将诗集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命名为“季节的偷闲”和“生命,渴求的间隙”,仿若生命的存在就像宇宙的一次节日庆典,是被允许可以“自由拼读自己”、摆脱时间重力的一次灵魂的飞翔。而生命只要体验过这样自由的时刻,便将会如她所写“太阳在心中”那样,“因造访过太阳/你是种子/播种和火炭/在你永恒的碎片上”。即使有肉体的衰老与消亡,即使人间有杀戮和仇恨,但是在事情的另一面,“在时间的另一个坡度”,却有着诗人永远信任的爱与弥合的力量。
让-皮埃尔·西梅翁在《律动》序言中有句话说得极为精彩:“这就是为什么这部诗集的全篇都以对立的‘但是’为轴,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诗作都建立在对位法,或反向的对称上面……那是因为我们天生被一种无解的双重性所控制:难道我们不是无可挽回地被‘损害我们的黑暗/给我们生命的火’紧束吗?”他敏锐地指出,舍迪德的诗不仅仅在广袤的太空和无限的时间中穿梭,她起飞的跑道和着陆点依然在人间。这是因为,把生命视为虚无则意味着一切都毫无价值和意义,暴行与善行、人道主义与丛林法则都可被理解和允许。舍迪德恰恰在承认生命必会带来阴影这一基础上毫不犹豫地赞美生命,因为这“意味着良知与最坏的情况对抗和较量”。作为一个诗人,她并非仅仅直面个人消亡的荒诞并与其抗争,她思考的也是整个人类曾经经历过、也将会继续经历的苦难。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她的诗中没有丝毫自恋,没有自艾自怨,只有“你在的地方/我在”,以及“我是多个人/我不是任何人”的对他者的深情和良知担当。
在第六章“追逐”之后,诗人以“惊叹”作为最后一章的题目。她以四季轮回、四时有信诉说在“瘫痪的土地”上对种子的信任和对下一个春天的期待。从我们的目光可见的山川大地到万千星辰——那脆弱渺小的生命与持久的宇宙;从树木不断再生的枝干到孱弱微小的花朵昆虫,她拒绝用有限的尺度来丈量生命,因为无限“在绝对的领地”嘲笑着某些人的短视;因为作为“蜉蝣”的生命,如水流一般永无停歇地流动,并因此而获得长生;也因为人的精神创造与“不可磨灭的星球”相连,正如米拉波桥在阿波利奈尔笔下得以永存。
舍迪德最终以“爱情”作为这本诗集最后的歌咏,端庄、深情而又从容,甚至流露出她特有的睿智幽默——“爱情是我们自己人/永远!”而这正是她对于生命最坦诚真挚的赞颂。
这是一本令人赞叹的诗集,一本让人难以平伏心绪的书。尤其当我想到它足够延续诗人的生命——并不是线性时间的计年,而是在诗中,在她对生命的祝福和热爱里,在所有读到这些诗的读者心中,在宇宙的某处,诗人安德蕾·舍迪德,依然会“因一个节奏激动/从一句话再生”。
(作者系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