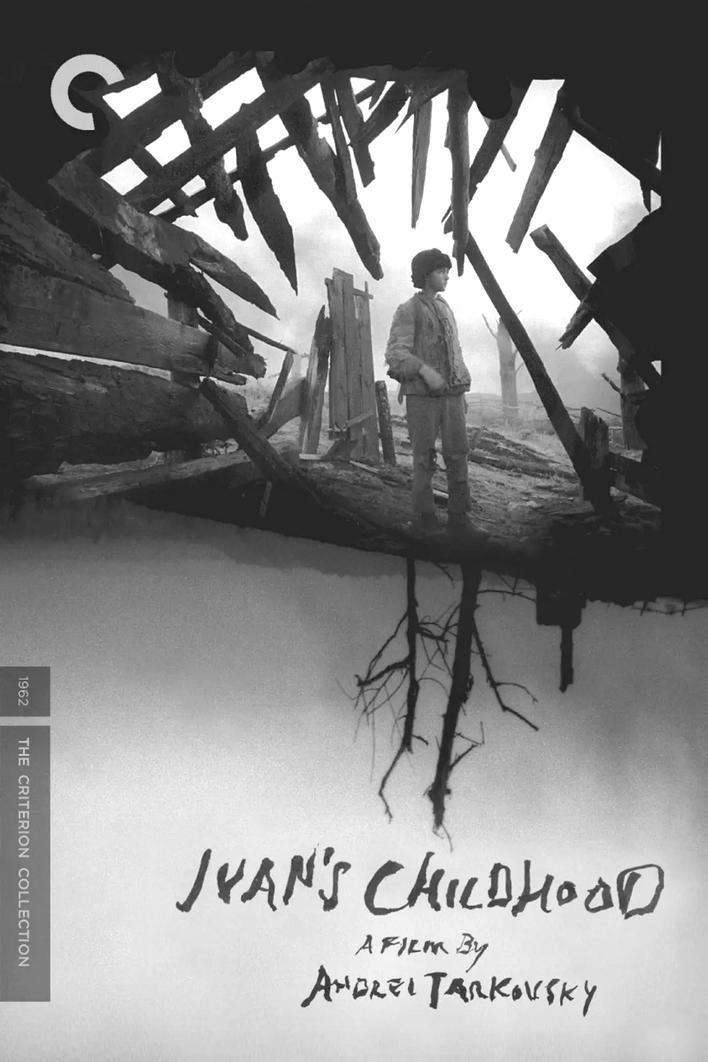当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得到改编拍摄《伊万》的机会时,他是个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的新人导演,唯一的作品是毕业短片《压路机与小提琴》,而小说《伊万》已是在苏联广为流传的名篇,作者弗·博戈莫洛夫也已跻身著名作家之列。1962年8月,电影《伊万的童年》从威尼斯捧回了金狮奖。
小说《伊万》以21岁的加尔采夫上尉的视角展开,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父母双亡的伊万从敌军阵地跨过第聂伯河,出现在“我”(加尔采夫上尉)的防区,12岁的他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侦察兵。情报战线的霍林上尉和卡塔索诺夫士官都非常关心伊万,希望送他到后方去,但伊万坚持以侦察兵身份战斗在一线。“我”继续战斗,又和伊万有过几次接触。在一次任务中,“我”代替阵亡的卡塔索诺夫,与霍林和伊万一起去河对岸搜集情报,伊万因为身材矮小不易被察觉,决定独自深入敌占区侦察。战争结束时,霍林已经牺牲,“我”在被盖世太保杀害的遇害者档案中找到了伊万的档案。
塔可夫斯基在电影《伊万的童年》中还原了小说的全部主要剧情,也没有改变人物的结局,他只是添加了几段非现实的画面——伊万的梦境,而这些梦使故事产生了某种本质性的变化。宛如幻觉的梦并不推进战场局势的发展,但借由“梦”这种最私密的介质,塔可夫斯基改变了故事的叙事主体,从青年人加尔采夫视角变为了儿童伊万的视角。
在原本的小说中,全部故事都出自于上尉的所见所闻,博戈莫洛夫事无巨细地还原前线阵地的每一个细节,加尔采夫上尉就是作家的眼睛。上尉总领一个营的各项事务,只在繁忙的作战任务间隙偶尔回想起伊万这个小孩。但塔可夫斯基却确立了伊万的主体性,当上尉给伊万盖好被子离开防空洞,镜头没有随着他一起去巡视河岸哨所,而是顺着水流潜入伊万的梦中,让这个孩子与故去的妈妈一同在水井中寻找星星,随后在梦中再次经历母亲被杀害的情景。
在关于《伊万的童年》的讨论中,它有时会被作为儿童视角的经典与崔嵬导演的《小兵张嘎》进行比较——两部电影也确有关联,《小兵张嘎》正是中国电影界对《伊万的童年》的批判性回应。但是这样一种对“儿童视角”的关注可能与塔可夫斯基本人的意图有所偏差。影评家们只注意到《伊万的童年》讲述了一个“小英雄”的故事,却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伊万牺牲在1943年底,年龄在13岁左右——他与1932年出生的塔可夫斯基是同龄人。塔可夫斯基不只是在以成年人视角塑造一个儿童,还是在描写自己这一代中早逝的人。年龄,这是塔可夫斯基与作家博戈洛莫夫和崔嵬导演之间的差别:出生在1924年的博戈洛莫夫在战争期间正值青年,与加尔采夫上尉年龄相仿;崔嵬导演生于1912年,抗日战争期间也正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他们表现战争中的小英雄依靠观察,而塔可夫斯基却凭借感受。
用电影的形式写一首诗
强烈的感受力,这种天赋可能遗传自塔可夫斯基的诗人父亲。这位导演自己曾说过,相比于戏剧,他更亲近诗歌。电影的俄语片名“Иваново детство”中,用“Иваново”表示“伊万的”这一用法基本只出现在古典诗歌中,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修辞表达。塔可夫斯基从最开始就是要用电影的形式写一首诗——这也许是苏联“诗电影”的传承,也许是“诗是吾家事”的自信。
因为是诗,许多意象就多了一层引申义,首当其冲的是电影标题。无论在小说还是电影,伊万都曾在任务中伪造姓氏,但他始终未改换自己的名字。“伊万”是俄罗斯人最常见的名字,几乎是俄国人的代称。在诗歌的语言中,在俄罗斯文化语境下,“伊万的童年”这一名称拥有这样一层隐含义:“我们的童年”或“我们这代人的童年”。
在塔可夫斯基之前,拍摄《伊万》的项目属于另一位导演阿巴洛夫,此公花去了一定的预算但效果并不理想,正因如此,年轻的塔可夫斯基才得到这个项目。塔可夫斯基接手项目时就提出要在影片中加入伊万的梦境。在塔可夫斯基撰写的《雕刻时光》一书中,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伊万》原著作为文学作品的鄙夷:“纯就文艺学层面而言,这篇小说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内心冲击”,但他在“伊万”这个角色身上看到了一种可以被电影表现出来的巨大张力——正如他写的:“人生的某些层面仅有诗才能忠实表达。”而塔可夫斯基表现这种诗意逻辑的方式就是梦境。
在最后一个梦之前,伊万的每一个梦都预言着悲剧的结局。在许多解读中,伊万的梦都被笼罩了神秘主义的宗教色彩:一个女孩的脸出现三次,男孩递给女孩一个苹果,这些画面蕴含显而易见的神秘学元素。但也许,把这些图像看作诗歌意象而非神学思辨才更符合导演本意。在此前的一千年中,俄罗斯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都浸润于东正教文化里,从诗歌中完全剥离这些意象会使诗意受到严重损害,使用其他的意象更可能令影片堕入晦涩之中。即使在原著,博戈洛莫夫也在伊万最后的档案上写着,伊万被一个叫叶菲姆·季特科夫(俄国名字)的辅警捉住,伊万咬伤了季特科夫的手,而出卖伊万使得季特科夫获得了一百马克——这正是耶稣被出卖故事的改写。
当伊万在防空洞中睡着,加尔采夫抱起伊万,伊万一只胳膊下垂,加尔采夫低垂着头,这一幕的构图神似米开朗基罗的《哀悼基督》。这尊雕塑摆放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中,如果是为了宣扬东正教的思想,俄罗斯人怎么会选择与“罗马异端”的雕塑类似的构图呢?这些宗教或神秘元素的加入,其艺术意义和诗学意义远大于神秘学意义。当善良单纯的加尔采夫像玛利亚怀抱圣子那样承托着伊万的躯体,画面就蕴含着两重含义,它首先预示着伊万肉体生命遭遇不幸的必然,其次又传达出这样的信息:纯洁的伊万已经死去。那么,这躯壳中残留的是什么?下一个白日梦给出答案:一个被仇恨扭曲的灵魂。
“战争是为了战胜邪恶”
《伊万的童年》中,所有角色都和伊万产生了关联,只有一个人除外——女军医玛莎,这是塔可夫斯基安排的另一条故事线。在原著《伊万》中,女军医是一个美丽但无能的医疗官,上尉严厉批评了她——像传统小说中的战斗英雄常做的那样——并且下定决心一有机会就把她调走,换一位更称职的男军医。塔可夫斯基完全抛弃了这样的设计,作为电影现实部分出现的唯一女性,他给了这个女孩名字“玛莎”——被命名使得她真正成为一个人。不同于常常处在昏暗与泥泞中的伊万,玛莎总是出现在光明和白桦中间,她与霍林在白桦林中约会,医疗站是桦树枝搭建的掩体。她是女学生,有家人来信说一切都好,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未经淬炼的纯真,完全不同于伊万时刻警惕的神情。玛莎的存在与伊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她穿着整洁的军大衣在阳光明媚的桦树林中行走,而伊万则要伪装成小乞丐悄无声息地在泥泞里穿行,他们互为对方的影子,玛莎是仍有家庭庇护的伊万,伊万是一无所有的玛莎。
塔可夫斯基让俄罗斯民歌《不要让玛莎渡过那条河》贯穿整部影片,这可能也是他为角色取名为“玛莎”的原因。这首歌本来讲述了一个姑娘被负心汉辜负的爱情悲剧,但在影片“不要让玛莎渡过那条河”的吟唱中,它奇妙地与汉乐府的“公无渡河”产生了共鸣。河流在此时与生命紧紧连接,它直接指向侦查小队要在凌晨渡过的第聂伯河,同时又暗示着传说中由卡戎摆渡的冥河,以及冥河所指代的悲惨的命运。在一声声“不要渡河”的吟唱中,所有渡河而去的侦察兵全部壮烈牺牲,只有加尔采夫上尉一个人活了下来。玛莎的结局是被加尔采夫调去后方,但原因不是原作中对她工作的不满,而是出自影片从始至终的信念:战争是男子汉的事,不应该有姑娘和孩子的位置。
由于“战争中不应该有孩子的位置”这一思想贯穿始终,很多人把《伊万的童年》看作“反战”电影,这其实是一种比较肤浅的理解。在电影中,塔可夫斯基特意安排了伊万看版画的情节。伊万观看的版画是德国画家丢勒绘制的,给出特写的两幅分别是《天启四骑士》和《骑士、死神与魔鬼》。《骑士、死神与魔鬼》被认为是丢勒向捍卫真理者致敬的作品,在画中,披坚执锐的骑士没有受到死神和魔鬼的恫吓,坚定地在一条满是人骨的道路上朝着自己的目标行进。在影片中,骑士无疑指向了英勇无畏的战斗英雄们,甚至直接指向小伊万。从这一点上,塔可夫斯基用自己的方式在向卫国战争英雄们致意。另一幅画《天启四骑士》取材自《启示录》,四位骑士分别象征瘟疫、战争、饥荒与死亡。伊万对这幅画发表了评论:“看这个骑着马的,瘦成了这样……看吧,也在践踏这些人民。”但伊万所批判的,并不是手持长剑象征“战争”的骑士,而是第四名骑着苍白瘦马的骑士,其名为“死亡”。在玛莎来与加尔采夫和霍林道别时,霍林关掉了留声机,寂静忽然降临,他说道:“多么安静啊,战争……”这一刻的无声是对战争与命运的反思。塔可夫斯基无疑厌恶战争,但他在《伊万的童年》表达的不是“反”战。如果一定要说他“反”什么的话,那他反对的是“恶”。在接近尾声的混剪中,出现了戈培尔等纳粹高官杀害全家后自尽的纪录片片段,这就是纯粹的邪恶——战争是为了战胜邪恶。
在影片的最后,伊万的死亡牵引出最后一场梦。他与十个孩子一起在海滩上捉迷藏,与妹妹在海滩上赤裸着奔跑。这是这一代人本应拥有的纯真童年,但邪恶侵蚀了他们本来的生活。伊万拒绝平静的后方生活,他始终怀揣着一种自我毁灭的冲动;最后,死去的伊万褪去了仇恨,全片第一次奔跑在阳光下面——但活着的人所要担负的却是记忆难以承受之重。塔可夫斯基坚称自己的童年是快乐的,但几年后在《镜子》里,他对童年的描绘却刻印着深沉的忧郁和忏悔。他把自己的童年经历代入到伊万身上,这经历也成为伊万对真实世界的最后的记忆:他从水桶中抬起头看着母亲,微笑着说:
“妈妈,那是布谷鸟在叫。”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