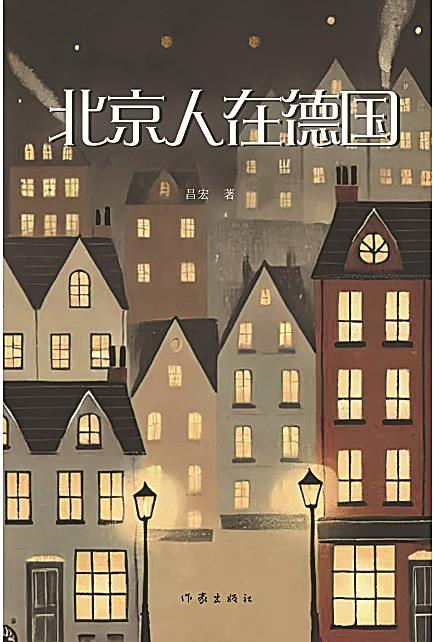□昌 宏
小镇的清晨洒满阳光,阳光里有股麦子的味道。老汉泊好车,拎一袋土豆戳在外面,望望天。
麦子熟了。收过夏麦,地里会冒出一种看似豆角又不是豆角的作物。我把去年拍的照片打开,问是什么?
老汉奇怪地看我,说,您问这个干嘛?
因为我活在这里。
阳光把罗马广场上的地砖烤得很热,我看见有人光着脚在上面走。侍者摆好刀叉,说烤牛排才是他家的特色。我问他,您知道OK地砖吗?侍者一怔,蓝色的眸子掠过惊诧狐疑与茫然。他朝广场的深处望去。圣尼古拉教堂门前刚好有个旅行团,导游在那边讲解。
导游举着小旗,一张嘴把罗马广场的前世今生说个明白。我问她,您知道这广场上的OK地砖在哪儿吗?她干脆说不知道,又说您问这个干嘛?
因为我活在这里。
她一指北边的博物馆,说那里面有专家。
博物馆里坐着两个年轻姑娘,一个在玩手机,另一个听音乐。我听出是一首德国名曲中的歌词:Wir leben und Wir sterben hier(我们活在这里,我们还将在这里死去)。
你们知道OK地砖吗?一个姑娘说不知道,另一个说管事儿的马上回来。
管事儿的是一位老妇人,她说这里是博物馆,不是问讯处。她每说一句,都用力甩一下灰白的头发,像是要从里面甩出一个个叹号。
我说,我们都活在这里!
她冷眼看我。那又能怎样?
那个下午,我一遍遍走在罗马广场的地砖上,我的目光也一遍遍抚摸它们。我想起有位老华侨说过,来德国那年,船漂在海上,像一块砖。我发现许多地砖腾空而起,漂在明亮的晚霞里,像一条条船。我蹒跚着张开手,想抓住它们,却总抓不到。
一个红脸汉子扶住我,说您去广场南边,市政厅旁边那门脸儿里碰碰运气。
一个操南欧口音的女人接待了我。她说OK地砖原本有四块,后来只剩下了两块。一块在圣尼古拉教堂门前。她打开手机找出照片,我认出那地砖就在女导游刚才站的位置。
没有人问OK地砖了。女人叹道。
因为我在这里活了28年。我想知道这地上长过的庄稼,有过的历史。
女人说,是漂泊!
我28岁那年出国,在德国漂泊了30多年。漂到第28个年头,我忽然有种莫名的惶恐,感觉此后的每一年都走在远离故乡的路上。我开始写小说,虚构的故事里有真人物、真细节顶着。比如害羞的老乞丐,他说:“零下二十度冻不死我,我一定要活到六十岁!”现在不行了,要活到67岁了,男女都一样。比如西米太太,她临终时伸出三根蜡烛般透明的手指,说:“不要在后园里挖土……盟军的哑弹。”
有两件事,在德国没有停止过。一是不停地反思战争;再就是不停地从地下挖出哑弹,大的小的。它们沉在下面,让上面的一切成了铺垫。哪天挖出个超级大的,就有人琢磨,万一没拆好炸了,从这儿到那儿都没有了。
这两件事之间是有联系的。两次战败和一次战败真不一样。
注:OK地砖与普通地砖无异,上面刻着OK两个字母。OK是Ochsenküche(公牛厨房)的缩写。16至18世纪,每逢德国皇帝在法兰克福加冕,都在罗马广场举行庆典。公牛在公牛厨房里被烤成肉串,分给法兰克福市民。四块OK地砖围起的,就是当年公牛厨房的所在。
(作者系欧华笔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