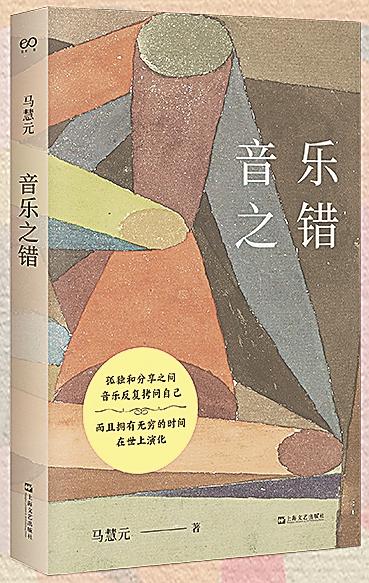音乐浸透了记忆,或者说它就是记忆的形状,不是吗?
多年以前,我写过一些随笔,关于音乐的细节和历史,更多的是音乐与生活的联系。写本身充满“危险”,人在写的过程中变化、演化,从一堆可能性中突围,也可能喂养出新的自己。不过,从六七年前开始,我不再写这类文章。然而,谁知道沉默的身体之中,有什么渴望在默默生长?渐渐地,我从心里清晰地读出一个新奇的愿望:去观察音乐的原理,看看它与数学、物理之间,到底有多少传说中的关联?几年孤独的寻找之后,历史的真相似乎一点点清晰起来:音乐和科学,并不总是一贯地“互利互惠”或“此消彼长”,它们偶尔彼此激励,更多的时候各说各话。然而,历史上那些努力“撮合”它们的人中,有多少科学史与音乐史上的英雄。他们失败了吗?音乐与科学的边界在一代又一代前辈的探寻中渐渐凸显。
很感动有读者把我这样的探索与梳理称为“思想地图”。于是便有了《一点五维的巴赫:音乐、科学和历史》这本书,我通过分析巴赫、海顿等音乐家的科学实践与牛顿、傅立叶等科学家的音乐研究,揭示人类对声音本质的共同追问。内容涵盖音乐结构的数学对称性、声波的物理原理,以及浪漫主义时期艺术与技术的互动关系,借助历史案例展现不同领域对真与美的探索路径。即便有了这本书,我觉得仍然有太多“未回答的问题”。今年出版的《音乐之错》算是进一步的开始。作为一个长期听音乐、经历各种感动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业余管风琴手,我对“感动”本身也有太多疑问。大概是程序员的职业习惯,我遇事总要问个为什么。于是打开音乐细看,打开自己的谱子细看,我开始猜想:种种音乐语汇并不仅仅是文化产物,背后或许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就是人脑的生理共性,它操纵着从创造到倾听的历史进程。这时我迷上了神经科学,上了一门门网课,收集了大量书籍。原来科学家们早有观察,各种实验也把音乐与人脑的作用考量到极致,但还远远不够。就这样,音乐中的一切都成为我学习神经科学的窗口。从音乐中独特的“重复”手段到漫长的节拍器传统,从曲式结构到旋律的时长,从全身运动的管风琴演奏到几秒之内的动作规划……许许多多重要的关联,我才刚刚开始知晓。音乐与语言、音乐与时空、演奏过程的手眼配合、身体和手指位置的记忆、乐器的设计与视觉习惯、节拍器和音叉在历史上对神经科学巧合般的启发……处处都值得言说,而语言的背后是庞杂的大脑进化史与文化史,音乐也是。
我日常练琴、演出,把自己当作试验品来观察:从动作记忆到并行的音乐处理,过去习以为常的“音乐体育”处处都充满奇迹。读一行谱,大脑辨认出音高,手和脚找出几个音并且弹出来——这个瞬间,会调动人脑860亿个神经元中的几百亿吗?其复杂度可能超过我们日常可见的“万丈高楼平地起”。仅就倾听和接收音乐的过程来看,人脑不断预测声音、不断制造模型、不断出错并纠正,几毫秒内就已不知有多少故事发生,若是科学家用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来追踪的话,定会捕捉到一片星海般的活动。
音乐,或者说所有的艺术都是神秘之物,因为接受者的思绪天马行空,谁也控制不得。音乐又充满物质之间的交互,它是空气振动与听者协作的产物,人脑的听觉、记忆、文化、共情、模仿、身体运动等交织在一起,才化合出“音乐”这样一种古老而无处不在的人类活动。自“音乐”一词凝聚成形,它也开始不断积累秘密。几年来,我作为观察者、思考者的好奇心燃烧不休,并且幸运地得到了编辑的支持,才没有那么孤独,才能持续记录自己在音乐与科学交汇之处小心翼翼的探寻。各种问题并不一定都有答案,我只希望能用个人的实践与学习经验,点亮那个变动不居、时时被科学认知所激荡的边界。然而,音乐终究是人生的一部分。我自己的一部分也常常回到往昔,想把自己交给音乐中的亲切与温甜,交给那种无需言说、不必多想的纯真。当我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用文字表达,却发现自己谈论音乐已经离不开科学与历史的语境。因为我相信这些语境的重要,相信物质关乎音乐的本质,科学不应成为音乐的禁区。这就是当下自己的思想状态,无法伪装。
音乐是“天真与经验之歌”,也是一条不可踏入两次的河流。曾经,我的文字更感性、更能传递情绪与生活,与他人的青春共鸣。而现在的我告别了那条道路,尽管我依然相信音乐的感人,敬畏它的神秘。一个关乎声音的关键词、一句温和的乐句,仍会射穿理性的堡垒,让无端的记忆喷薄而出。青春记忆仍可追索,当下的选择却已无处可逃。
(作者系作家、管风琴演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