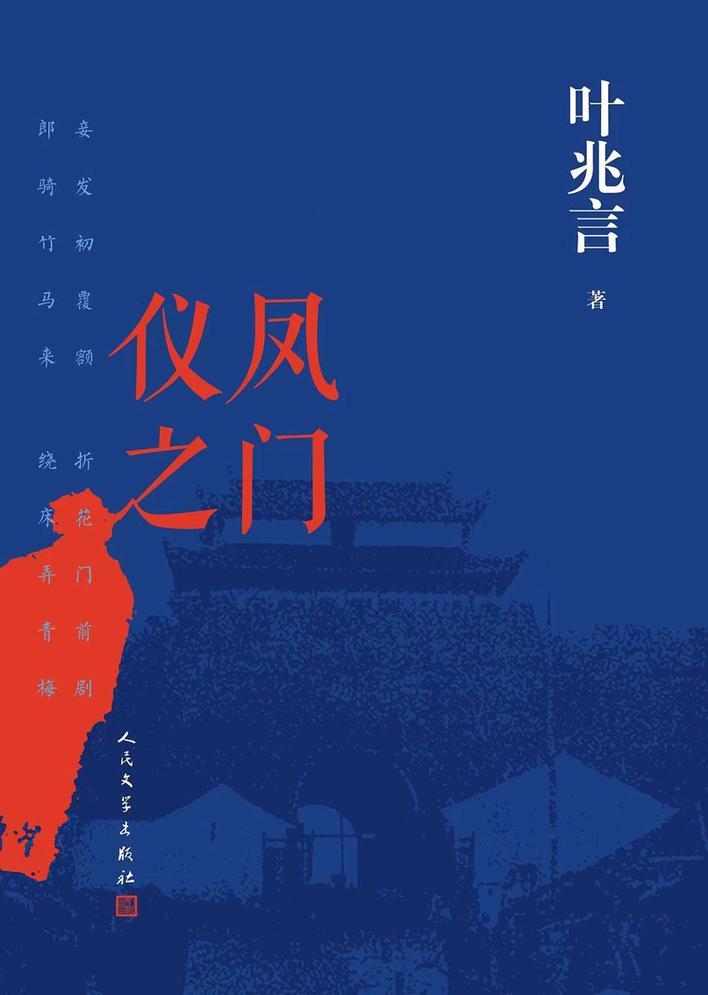《仪凤之门》是叶兆言用长篇历史小说的形式讲述南京故事的又一可贵探索。全书故事情节的发展起于清末,迄于1927年北伐军占领南京以及随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隐括了六朝古都在近现代初期将近30年历史的风云变幻。
小说《仪凤之门》似乎是叶兆言此前创作的纪实作品《南京传》的姊妹篇,二者互为副文本。《仪凤之门》在历史叙事层面可视为以“下关”地区为中心的另一部“南京传”,但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被作者转换为小说故事的背景,同时凸显了虚构人物的重要性。《仪凤之门》本质上是小说创作而非历史纪实,但历史纪实的框架与材料仍然被小说大量汲取。准确地说,《仪凤之门》是叶兆言探索的带有强烈历史纪实色彩的一部虚构性历史小说。
《仪凤之门》写人物,层次感很强。那些历史上真实而知名的军、政、商、学等各界人物都被设置为背景,居于小说实感世界前台的乃是虚构的,或经过虚构性改造与转换的一系列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他们才是以下关和仪凤门为中心的上述30年南京历史的主角。
表面上,小人物好似只是被看不见或看得见的历史巨手随意揉捏的蝼蚁之辈,但蝼蚁的爱恨情仇、是非好恶、沉浮生灭,恰恰正以其一再被忽视、被玩弄的弱者形象而显示其历史性的存在,甚至显示为南京历史的主体内容与文化特性。抽空小人物和他们的小故事,近现代初期30年南京历史的大故事会顿时失去依托。大历史与小人物的这种悖论,可能正是叶兆言创作《仪凤之门》时力求把握和开掘的真正主题。
《仪凤之门》注重人物群像的描写,其中有军界政界的高层斗法(满清政府、革命党、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有中外商界各色名流的尔虞我诈,有学界和新闻界人士的一腔热血,有警察和帮会的鱼龙混杂,有振槐芷歆父女、振槐仪菊兄妹、仪菊芷歆姑侄这样官宦人家的兴衰沉浮与伦理纠葛,更有聚集在下关地区以阿二和铁梅夫妇、杨逵姑妈、棺材铺老板为代表的下层人物的发迹。主要人物杨逵就是在这种人物群像的整体构思中被凸显出来。
在杨逵身上,几乎积聚了上述南京历史内容与文化特性的所有要素。他幼年失怙,读书不成,寄人篱下,跌入底层,又因缘际会起于草莽,一时叱咤风云,炙手可热,成为整个下关地区社会贤达的主要代表,但又始终与草莽世界血肉相连。杨逵似乎肩负了天降之大任,欲以一己之力振兴民族资本,却并无读者所熟悉的茅盾笔下吴荪甫那样虚骄的英雄气概。杨逵可说是善恶并赋的人物,虽作恶多端,却始终天良未泯。正是那一点天良使他在许多关键时刻不敢恣意妄为,也不可能掀起更大的风浪。杨逵最后在事业巅峰突然失去挚爱,几乎一无所有。在一个所谓的新时代大幕徐徐揭开之际,被上上下下寄予厚望的“下关之王”居然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杨逵的性格、杨逵的故事,好像就是古都南京难以摆脱的一种宿命般的隐喻。1928年以后,杨逵及其周围一干所谓“老南京人”将何以为生?他们将如何面对那更加反复无常的历史风云?小说的全部叙事其实已暗含了这个结束之问的答案。换言之,小说的结局乃是另一段历史循环的开始。在新的历史循环中,扮演主角的恐怕还是那群叫作“南京人”的蝼蚁之辈,只不过他们也许不再叫杨逵、水根、冯亦雄,而换成了别的名和姓。
读《仪凤之门》,不由得让人想起现代文学史上同样以南京为主要历史舞台或重要活动场所的两部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跟《仪凤之门》都有交集的长篇小说:阿垅(陈守梅)的《南京》(1939年)、路翎《财主底儿女们》(1943-1944年陆续完成)。
《南京》跟《仪凤之门》一样写实性都很强,但也都经过了一番艺术加工与虚构。《南京》主要描写1937年底南京陷落前后,中国守备部队英勇血战的始末,但作者以大胆铺排的手法,穿插了一系列如草芥般旋生旋灭的普通南京市民与郊区农民的命运,包括战线上、战壕里的许多普通士兵的生与死的挣扎。其中“挹江门惨剧”就发生在《仪凤之门》重点描写的下关以及在仪凤门之后新修建的挹江门一带。如果说阿垅的纪实性主要表现在他作为专业军事人才所熟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军事部署的专业知识上,叶兆言的纪实性则较为开阔,不仅涉及南京城和下关地区民生发展与城市建设的历史,更包括当时各种势力渗透其中的所谓民族资本的畸形发展,以及从清末到1928年各种军政势力,包括外国列强在南京走马灯式的更迭。
《财主底儿女们》在上半部写到,苏州巨族蒋氏一家的南京分支,一度吸引了家族全体齐聚南京。路翎笔下大家族衰落之前各色人等的表演跟《仪凤之门》中仪菊一家的兴衰很有可比性,而秦淮河畔的底层社会也很像是叶兆言描写的下关穷苦人家,至于《财主底儿女们》所展示的从淞沪会战到南京陷落的一段历史,则与阿垅的《南京》重叠,也可说是《仪凤之门》故事的历史延续。
熔纪实和虚构于一炉,尽量展示社会各阶层生活的全景图,是《南京》《财主底儿女们》和《仪凤之门》这三部相隔80年,都是讲述南京故事的长篇历史小说(或曰具有清醒历史意识的小说)最值得注意的相通之处。但这三部小说也有很明显的区别。《南京》《财主底儿女们》尽管也写到小人物的群像,却毕竟没有像《仪凤之门》那样把这群小人物设定为小说世界的中心,更没有像《仪凤之门》那样将小人物群像的其中一个(杨逵)塑造为整部小说的主人公。叶兆言不仅追蹑杨逵与南京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复杂关联,比如他与阿二、姑妈家的血肉相连,他和革命党领导人物张海涛、彭锦棠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会娶官宦人家小姐芷歆为妻,还有他跟东洋留学生朱东生合作做生意,他甚至被推举为下关乃至整个南京的市民代表跟炮轰北伐军的列强谈判,等等,作家还更深入地探索了处于上述复杂社会关联漩涡的杨逵的内心隐秘,由此折射出叶兆言笔下所呈现的“南京人”群体的性格与命运。
“历史小说”从其概念被提出至今,作者们各擅其长,从未定于一尊。甚至历史小说的定义也在文学史的有序展开中被不断刷新。历史小说的多样性源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深邃,更源于创作主体对历史的个性解读与个性的艺术表现。叶兆言的《仪凤之门》完成了他在历史小说写作上特色鲜明、定位精准而又内涵丰富的独特探索,值得认真研究和反复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