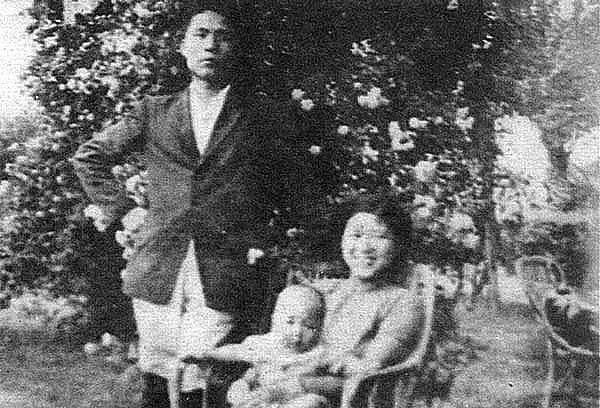将爸爸妈妈的一些文稿、书籍等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早已商定好的事情,那里有罗烽、白朗文库。我知道把这些东西捐赠专门机构比存放家里更稳妥,更能发挥它的作用。但是真要拿走,还会有些不舍,心中有种空落落的感觉。
爸爸妈妈离开后,偶尔翻翻他们书写的文稿、日记或信件,摸摸、看看他们曾经用过的物件,几乎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东西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在亲人眼里却非同寻常。它不单单是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它留有爸爸妈妈的余温,见证了他们生活、奋斗的波波折折。它是鲜活的,其中蕴涵太多的感情元素。
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件物品都有一段故事。不管这故事是愉快还是悲伤,都和爸爸妈妈息息相关。我从1978年爸爸和妈妈写给中央组织部“申诉材料”的附件中,挑出一份署名罗烽的“东北文艺思想指导上的两种偏向”的草稿给现代文学馆。这是爸爸1953年4月在“东北党的文工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从书面上可以辨认是妈妈的字迹。文稿末尾有爸爸的标注:这个发言提纲是总结东北三年(1949-1953)文艺工作经验教训的个人看法,本文原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大连‘造反派’红联军抄走,屡所索不还。
回头看,也许就是这薄薄的几页文稿,竟改变了爸爸的后半生乃至妈妈的一切。
爸爸于1952年底,经本人再三申请由东北调全国作协归队搞创作。此前,曾担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东北文化部副部长,兼东北文联第一副主席、联合党总支(文联、广播电台、文化部)书记等。刘芝明是东北宣传部副部长兼东北文化部部长、东北文联主席。作为刘芝明的副手,爸爸分工抓行政工作,刘芝明负责思想领导。从1949年末到1952年底的三年间,爸爸和刘芝明在文艺思想上发生过一系列分歧,也有不少次争执。有的是在干部会议上,有的是在其他场合(如共同在李富春、李卓然面前)。分歧和争论的中心问题,有的似乎解决了,有的不了了之,有的则根本没有解决。
1953年初爸爸办完调京手续,拟到鞍山市弓长岭矿体验生活。途经沈阳时,应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要求并征得全国作家协会同意,临时留下帮助做大区撤销后东北文化界的善后工作,同时协助刚成立的东北作协主席团(由白朗、马加、草明组成)工作一段时期。
在此之前,东北文联曾经接到全国文联即将召开全国文联扩大会的通知。东北文联要准备一个报告,题目是《三年来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与群众文艺活动问题》,报告于2月完成。经刘芝明审阅后即印发文联委员,拟召开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报告首先肯定了1949年“东北文代会”刘芝明提出“创造新英雄人物”号召的正确,肯定了几年来的成绩。爸爸看了这份铅印稿的报告,提出不同意见。东北作协的同志在讨论报告草稿时,也提出许多三年来对东北文艺工作领导的意见。后来李卓然召集会议,否定了这份报告。会上布置文艺业务部门,首先进行各单位的总结。并要求对领导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提意见。之后,以东北局宣传部的名义,于3月28日至4月10日召开“东北局党的文艺工作干部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东北一级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方面的负责干部及东北各省、市文艺方面的领导干部共49人,因为会期在4月,故称“四月会议”。这期间,爸爸和刘芝明的思想分歧不但没解决,反而矛盾加剧。爸爸在会议发言中说:“我认为,三年来东北文艺是贯彻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的,但有较严重的缺点。就是:对文艺干部思想领导不够,普及工作缺乏系统、缺乏研究,这缺点有改变,但需要在今后工作中巩固。”
“文革”中,李卓然谈到“四月会议”时说:
“东北三年(文艺)工作有错误……当时有人说文艺创作是赶形势、赶任务,限三天四天就赶出一个节目配合任务就不能提高创作。我认为赶形势、赶任务能结合实际没有错。好像刘芝明不大同意赶形势、赶任务。他是主张创作提高,赶形势、赶任务会限制提高。1953年的会,罗烽对刘芝明有意见。草明对刘芝明也不满意。
“做结论时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路线方向错误还是一般贯彻的错误。刘芝明当时好像偏向三年工作是正确的。我的意见是有严重错误,但方向错误要考虑。有人提出是方向路线错误,是谁提的记不得了。
“现在看看,当时‘东北文代会’上对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一些口号是提出来了,但没有贯彻。”
1994年春,爸爸妈妈已先后作古。原辽宁作协主席方冰叔叔提到他们时说:“……罗烽同志讲群众路线,重视普及,开展群众文艺活动。抓戏改,重视文工团,主张办汇演。1948年罗烽同志和我调查旅顺盐滩村的村剧团,支持寺儿沟街道剧团演的三幕话剧《穷汉岭》,罗烽同志赞扬群众演得好。我认为大戏要搞,但把群众抛开就不好。罗烽和刘芝明的分歧就在此。”
在不同历史阶段提倡“普及”还是“提高”,本是文艺思想上的问题。但是,爸爸妈妈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竟以“反刘芝明、反领导”为罪名,被打成“舒(群)、罗(烽)、白(朗)反党小集团”。舒、罗、白三人不同意强加给他们的罪名,一直在申诉。1957年“整风”之前,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党总支受党组委托召开有关同志的座谈会,处理1955年的“舒、罗、白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会上,前党组书记周扬等五位当时领导运动的同志,都说他们应该负有自己的责任,承认“那次会有简单粗暴的错误和缺点”,“不够实事求是,甚至刺激、损伤人的情况是存在的”。在另一次会议上决定:“摘掉一切带有原则性的帽子,在原来那种形式的会议上当众宣布,并向沈阳作协(即东北作协)传达”。
正当爸爸妈妈翘首以待正式书面结论下达时,全国的“整风”形势风云突变。由最初的帮助党整顿作风,变为反击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斗争。随之,爸爸妈妈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他们成了“向党翻案”,为丁玲“献策”、“通天”的反党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降职降薪,贬谪塞外矿区劳动改造。
我曾与一位长者慨叹说:如果当年爸爸不去参加1953年的“四月会议”,就没有这个发言了。那么,就不会被打成反党集团,更不会在以后的“反右”运动中沦为阶下囚。老人笑我不懂政治,说我是善良人的善良幻想。他说“现实生活不像想象的那样美好,特别身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年代。即使没有‘四月会议’发言,还会有其他的什么发言”。
捐赠物品中,有一块长(62厘米)宽(27厘米)不大的三合木板,一边已破损。从1960年到现在刚好半个世纪,它伴随妈妈数十年,是妈妈的遗物。
妈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患慢性增殖性脊柱(胸椎、腰椎)炎。1958年下放阜新地毯厂织地毯,致使病情恶化,不能伏案写字。1960年后,虽然穿着特制的钢背心,也只能借助这块小木板放在沙发扶手上写作。
文化大革命,妈妈精神失常。继之,肺气肿、肺心病、胃切除五分之三。医院几次下达病危报告。在妈妈卧床不起的最后十年,这块木板又成为她每日三餐的餐桌。一看到这块木板就能想起妈妈躺在床上的样子。十年,十年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妈妈去世前,下肢变形、萎缩,因骨质疏松引发两根肋骨断裂,稍一动就锥心般地痛……
记忆,在无始无终的苍茫岁月中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