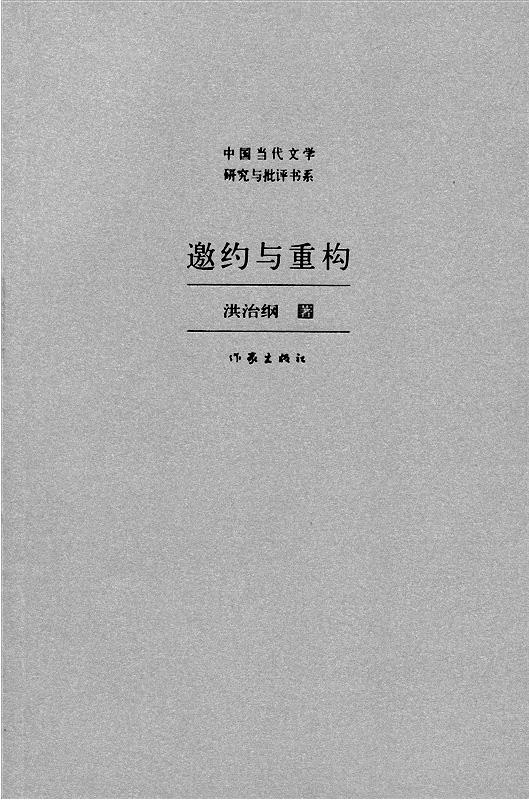在《西方正典》里,耶鲁大学的资深学者布鲁姆曾将西方的文学史划分为四个时代: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其中,所谓的“混乱时代”,就是指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实践,一切既成的艺术规范不断被打破,万物破碎,中心消解,感官放纵,仅有低劣的文学和大众的趣味到处蔓延。对于一个崇尚文学的精英意识、经典律则和“审美自主性”原则的人来说,布鲁姆的焦虑和郁闷是可想而知的,他甚至放出这样狠毒的话来:“作为文学批评界的一员,我认为自己遭遇了最糟的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虽然没有像布鲁姆所描述的那样,经历了几个不同时代的清晰特质,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混乱时代”的各种文学征兆在我们的文学实践中也是显而易见的。记得曹文轩先生就曾经在《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一文里,对此进行过一番痛诟,让我深受震动。
就我个人的阅读视野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虽然出现了不少重要的作家,涌现了一批不可忽视的作品,作家的主体意识也有了空前的扩张,但是,不尽如人意之处依然不容回避,“混乱时代”的各种文学情形有增无减。尤其是面对物质主义的生存现实,面对利益阶层重新分配的社会秩序,面对伦理体系不断被颠覆的人性场景,一些作家不断地陷入某种迷惘与失衡的精神空间。缺少思考,缺少发现,缺少伤痛,很多的作品,要么是对庸常经验的不断复制,要么是对公众聚焦的简单临摹,要么是对低俗欲望的尽情宣泄,要么是借助“剑走偏锋”的逻辑来哗众取宠。文学的功利性、实用性、媚俗性,依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只能说明,我们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找回文人的精神品质,也没有对自身作为现代知识的角色与使命进行有效的思考和定位。为此,我一直强调,重返真正的文人空间,以自我坚定的艺术信念和顽强的精神膂力,来回应历史长久的期待,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否则,我们将很难开拓出一条崭新的艺术之路,也不可能建构起属于自己本民族的“伟大的传统”。
在我看来,重返真正的文人空间,可以重新确立作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时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艺术使命——他应该拥有坚定的人生信念、独立自治的精神操守和专业上的原创能力。同时,他还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时刻保持着对各种不合理的现实秩序以及生活现象进行有效的揭露与批判,从而尽己所能地推动社会向更加合理、更加公正的理想状态前行。萨义德曾说:“知识分子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那种盲动的、好大喜功的精神领袖,也不是那种简单的、迎合各种权力机制的工具。他应该在内心深处始终拥有一种对祖国的深沉之爱,对大众的深情体恤,对个体精神空间的顽强恪守,对现实秩序勇于表达自己最尖锐的声音。他们像狮子那样独来独往,而不是像狐狸那样成群结队。一个从事精神劳作的作家,首先必须完成自己作为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定位,才有可能进一步在专业领域中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
重返真正的文人空间,就是要以高度清醒的内心意志来质疑一切生存的现实表象,并与一切价值观念及其社会体系保持着时刻的警惕。没有警惕就没有怀疑,没有怀疑也就不可能有发现,而没有发现就不可能进入本质,不可能揭示真正的生存真相和存在本质,更不可能显示出一个文人作为精神劳作者的独特品格。高尔基曾说:“道出真理与实情,是一切艺术中最最困难的艺术。”这是因为,它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和眼光,更需要一种时刻警惕的立场和姿态。因此,面对这种巨大的挑战,我觉得,作家和诗人们一方面要拥有“傲骨”,犹如鲁迅先生那样,以直面一切的勇气和力量,来道出民族内在的缺陷,展示历史潜在的本质,披露大众的苦难根由,而不是像当前的一些作家那样,看似在关注现实,其实却在四处彰显虚弱的道德立场;另一方面,还要有“禅心”,要有一种对大众苦难的体恤情怀,对人性劫难的悲悯胸襟。这是一个文人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基质,也是一个文人得以存在的道德底线。傲骨禅心,既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种艺术境界。真正的文人,只有进入了这种境界,才有可能穿透所有世俗的迷障,写出真正内涵宽广的作品。
文学批评也不例外。越来越多的人都感到,现在的批评家们不是忠实于文本的细读和基本的学理,不是忠实于艺术的审美律则,而是依赖于公众舆论和个人私情。人们看不到批评家相对恒定的价值立场,看不到率真的批评勇气,也看不到真正的批评智慧,字里行间之中,却透射出某些市侩的气息。批评的功利化和创作的功利化一样,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顽疾。但是,人们更有理由认为,批评的功利化,其危害远远大于创作的功利化,因为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批评具有对文本进行审美鉴别和阅读指导的意义,就像英国诗人奥登所言,批评家的功能就是“使我相信,由于我没有很好地阅读,我低估了某个作者或某部作品”,或者“对一部作品进行‘阅读’,以增加我对它的理解”。这也意味着,批评的阐释功能远比简单的判断更重要,对文本的尊重远比个人的趣味更重要。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批评就是利用批评家的专业知识和在长期的阅读实践中逐渐完善的审美标准去解读批评对象,阐释自己的理解和想法,“说明艺术品‘成长’过程”,或诠释“艺术与生命、科学、经济、伦理、宗教等等的关系”(奥登语)。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对批评对象的细读之上,通过认真的研读和专业化的分析,并自始至终围绕自己的批评对象来发言,而不是动辄就套用自己先在的观念,以“精骛八极”的方式标榜自己的所谓“学识”或糊弄一般的读者,更不是抓住一两个所谓的“细节”问题便粗暴地对文本加以否定。
批评当然需要判断,但这种判断,是建立在对文本进行丰沛阐释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审美判断。批评也是一种创造,但这种创造是“及物性”的创造,是针对具体文本所蕴含的审美信息而延伸出来的创造,并不是借用评论某个文本的机会,大肆灌输自己的某些所谓的体系化思考,更不是凭空的、甚至是莫名其妙地训诫作家应该如何如何地写,而不应该如何如何地写,仿佛自己是一个文学法官。
将自己视为文学评判的法官,这是批评家的角色错位。它造成了批评的武断、草率和粗莽,远离了文学批评应有的科学、理性和公正。尤其是当批评家受到自己个人趣味和私情的蒙蔽时,不认真地去研读文本,便四处表明自己的这种“法官”身份,无疑更伤害了批评应有的尊严。法国著名的批评家蒂博代就曾一针见血地否定了这种恶劣的、市侩化的“法官”式批评做派。他认为,如果作者是律师角色,那么,法官就应该是公众,而批评家只是一个检察长,“好的批评家,应该像代理检察长一样,应该进入诉讼双方及他们的律师的内心世界,在辩论中分清哪些是职业需要,哪些是夸大其词,提醒法官注意对律师来说须臾不可缺少的欺骗,懂得如何在必要的时候使决定倾向一方,同时也懂得不要让别人对结论有任何预感。”显然,在蒂博代看来,批评家的职责,就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桥梁,使读者能够更科学更全面地了解作品,但批评家也并非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和事佬,所以他又使用了“使决定倾向一方”来委婉地表达批评家应有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批评家建立在文本细研之上的价值立场。
抛弃“法官”的潜在意识,回到具体的批评对象之中,以自己的专业学识来阐释它们的内在品质,以此展示自己所恪守的艺术立场和价值标准,远比四处兜售所谓的“学识”更重要。如果在文学批评中强制性地兜售所谓的“学识”,那只是一种丑陋的“炫技”。用奥登的话说,在这类批评家的文字中,我们从他的“引文”中所获得的教益,要远远高于他的批评文字。遗憾的是,这种“炫技式”的批评并不少见——动不动就扯出一个大概念,做理论谱系状;或者无论针对什么批评对象,都要与某些经典性的文学作品作“跨越式”的比较;甚至因为某些评价风向的转变,批评家自己便悄悄地改弦更张、先抑后扬或前倨后恭,而且不乏以所谓的“学识”来印证自己的“观点”。通过卖弄“学识”来遮掩自己飘忽不定的价值立场,为自身批评的出尔反尔和见风使舵提供便利,从根本上说,表明了一些批评家正在以批评作为手段,来获取专业之外的世俗功利。如果加上他们对自身“法官”意识的不断强化,其恶俗化的效果可想而知。
当然,我并不想否认,一个批评家必须拥有敏锐而准确的艺术感觉,必须具备丰富而深邃的思想积淀,这两种素质将决定他能否有效地阐释作品,并对作品进行令人信服的审美评判。但是,要使文学批评真正地沿着学理性和科学性进入良性循环,我觉得仅靠这两点专业素养的强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将职业操守和艺术立场提高到应有的位置上来,认真地处理并协调好批评家作为“世俗的人”和“专业的人”之间的角色区别。作为世俗的人,我们或许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需要,在日常伦理规范下进行自由的生存选择;但是,作为专业的人,我们必须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和严谨的评判眼光,对待自己的批评对象,维护批评职业的基本准则和伦理操守,即它的公正性和科学性。我承认,我的能力有限,学识有限,但是,我一直在为维护批评的这一基本伦理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