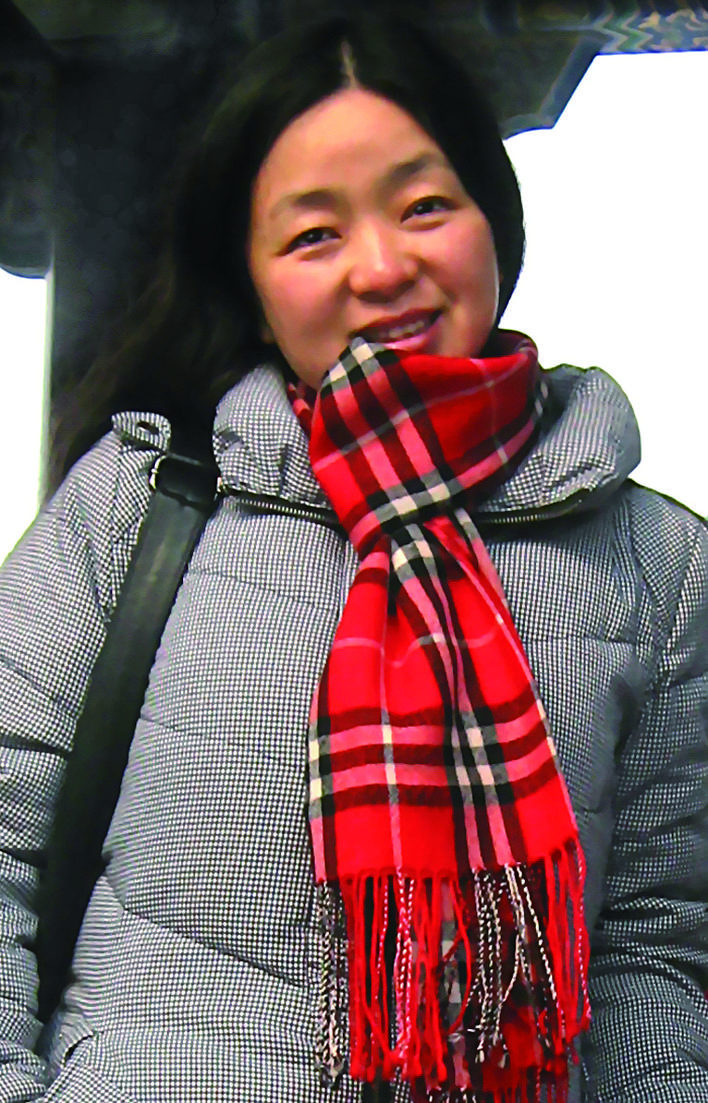诗情它突然又回来了。那只奇妙的鸽子,在《伊犁河》杂志社三面落地的玻璃窗外轻轻啄着窗
我的第一首诗是写我的父母带着幼小的我们姐妹仨去大森林里淘金的故事。我说那淘金的簸箕就是我们的诺亚方舟,我还说同样是金黄色的云母片,我们高高握在手心向着父母飞跑,他们爽朗的笑声回荡在深深的大森林和浩荡的大河边。诗歌的最后我说那小小的诺亚方舟后来被弃置在房顶,被阿勒泰的阳光晒得如泛白的唇。我用一个信封把这首名叫《屋顶的诺亚方舟》的诗平邮给了上海文学杂志社。他们那时候正在举办第三届上海文学征文比赛。之所以用平邮,是因为第一次来北京的我一定是囊中羞涩的。信寄出的时候,我对着信封沉默了5秒钟。这沉默的姿态我竟然记住了。过了3个月,我接到上海文学杂志社的电话,编辑告诉我,你获得了三等奖,奖金800元。那是2006年,我在朝内大街正骑车去望京上班。料峭清寒的春天顿时注入了无比明亮的阳光。我第一个给女儿打电话,她不过5岁。我说,笑笑,妈妈的奖金都给你。现在想来,那种新鲜的喜悦还是那样的清透美好。那个小小的平邮的信封,竟然是一只神奇的鸽子。
但我的诗歌创作并没有继续下去。那时候大家都拼命写小说。我也写。大家都说,只有小说能够成就一个作家,写诗歌或者散文在这个时代是不会扬名的。2006年到2008年,我写下了一篇篇能够发表却没有多大意义的也许是小说的东西。如果老的时候回望,我的一生里最痛苦的一定是这3年,绝望中看不见一点点新生的可能,生活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而文学,它并没有能够拯救我。生活的窘困、心灵角落的枯竭,直逼而来。
2008年11月,鲁院高研班课程结束,我返回故乡,坐上长途车去到一个西北以西的地方——伊犁。我决定把自己流放,放到一个最最冷寂的地方,这里没有小说创作的野心的逼迫,没有生存的压力,没有寒冷人心的浸入。那时候我没有想到,我的诗歌创作会在这片土地上最热烈地绽放。也许正是因为伊犁给予我荒凉之后的安慰,给予我寂寞之中的从容,给予我寥廓天地的舒展,诗情它突然又回来了。那只奇妙的鸽子,在《伊犁河》杂志社三面落地的玻璃窗外轻轻啄着窗。窗外是伊犁最大的清真寺,寺顶是直指苍穹的弯月亮,我日日看着蓝天和它们。到了夜晚,整幢大楼只剩我一人,我拉上窗帘,披上披肩,坐在电脑前,写下一首一首的诗。北疆大地,它们在我的胸中潺动酝酿多时,终于蓬勃而出。我被大自然浓浓爱意守护着的童年少年的阿勒泰岁月,我的青年时代的断点盲点,在纯净美好和黑暗困顿中交织挣扎的人生况味……正是因为这种挣扎,于是纯净的更纯净。相信美好就在不远的前方,我可以以趔趄的姿态去拥抱它们,而命运宽容地允可了。我的诗集《五月的布尔津》在2009年冬天诞生。这一年,我的诗歌在许多刊物上发表,被《诗选刊》转载,并获得了芳草杂志社评选的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第二年,我获得了新疆青年文学奖。颁奖词说,张好好在散文、小说、诗歌三种文体间跨越式的写作,展示了她强大的对于文学形式的掌控能力。
我不想说,文学是用来改变命运的。虽然现在的我果真过上了岁月静好的日子。我想说,感谢生我养我的土地,最后依然是它们拯救了我。北疆的大地、大风、大雪和苜蓿花,它们以最美妙的组合形式进入我的诗歌,各自占据一个位置,合唱出美妙的乐声。诗歌给我洁净,给我勇气,给我美丽的心灵和眼睛,也给予我永恒的爱情。今天,我写下这篇小文章,感谢2008年鲁迅文学院给予我的一切,在11月这个月份牌上,生命开始彻底转折,我带着一颗干净的心灵,去往我的福地——伊犁。我便在那里完成了我的新生。
我想把《白》这首诗献给亲爱的鲁院:
白
你看,今夜没有雪,没有风
没有西伯利亚的白胡须。雪花呢
那种古老的衣料。它饱含着爱和
眼泪啊。那么小的生命的刻度
宇宙的尺子,光束,花朵绽开,无限地
那只手翻转过来,向着极致,冲破所有,向着虚茫
那里什么也没有——那么我们站在哪里
昨天,是眼泪,是爱,是眷念
今日,四顾,我们爱的白,雪花儿的白
梨花面庞的白,滴落在枕畔的眼泪的白
挥手说再见的目光的白……
明日,舒缓柔美的,手——漫漶地打开
我们是否与光永在?同在?
我想起童年燕子的呢喃,她的声音亦是白的
那剪剪的身影,我局促地仰望,屋后的河水
今夜我们一同深呼吸,白色的浪花,果真逝者如斯夫
辨识世间一切的白,你的白,我的白
窄窄的门廊,月光温顺的白照进来
照着我们的白衣衫。用大雪渍染白衣,用月光渍染白衣,所以
我们爱着雪国,爱着驹子清越嘹亮,穿透雪野的洁白的声音
她的眸子乌黑
那些一生的希望,一秒的无望,湿嗒嗒的幼弱的依恋和爱
洁白的齿紧咬着下唇的倔强和坦然
多年以后,我们重新取出那方小小的白手绢
听见西伯利亚的风,它们呼喊了许多个世纪。世世代代
也只不过是宇宙生命小小的刻度
一切的一切洁白似雪花
一切的一切……从来没有过不欢而散,垂下头
两棵相爱的向日葵。它们的籽粒白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