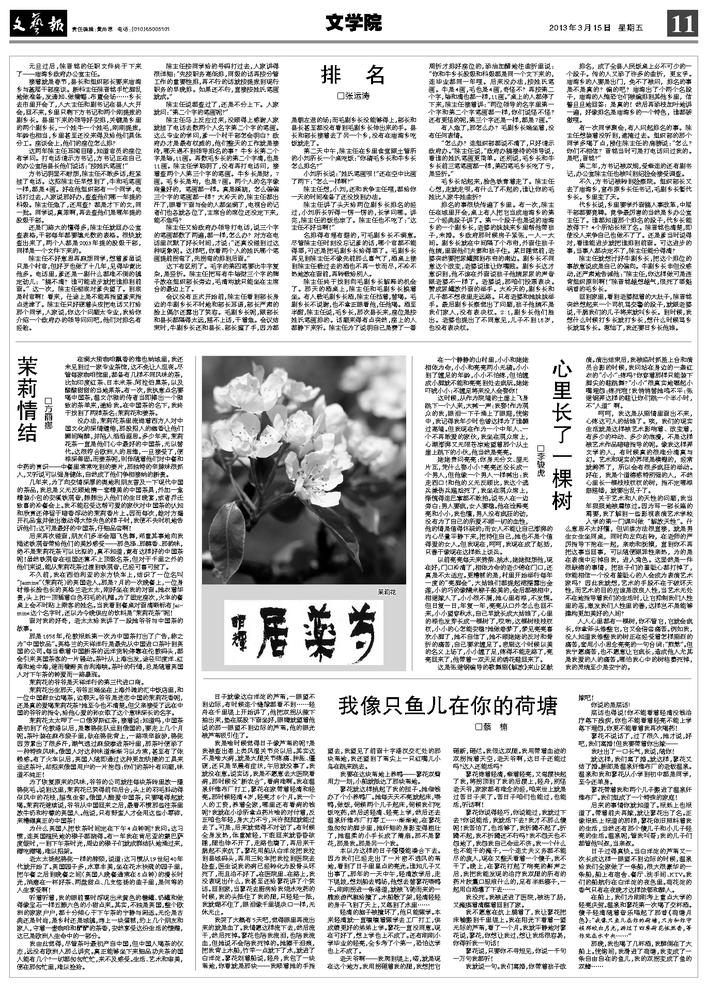在满大街咖啡飘香的维也纳城里,我还未见到过一家专业茶馆,这不免让人沮丧。尽管每家咖啡馆里,都备有几样不同风味的茶,比如印度红茶、日本米茶、阿拉伯黑茶,以及酸酸甜甜的当地果茶。有一次,我执意点名要喝中国茶,温文尔雅的侍者当即捧出一个雅致的茶单来,递给我。在中国茶的名下,我终于找到了两样茶名:茉莉花和姜茶。
没办法,茉莉花茶里流淌着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深情缱倦,那股招人的幽香让他们瞬间陶醉,并陷入滔滔遐思。多少年来,茉莉花茶一直是他们心中最好的中国茶,无以替代。这很符合欧洲人的思维,一旦接受了,便根深蒂固。而姜茶呢,则伴随着他们对中餐和中药的赏识——中餐里常常吃到的姜片,那独特的辛辣味很抓人,又听说可以强身健体,自然成了他们争相接纳的新贵。
几年来,为了向交情深厚的奥地利朋友普及一下现代中国的茶品,我总是义无反顾地携一套精美的中国茶具,外加一盒精装小包的安溪铁观音,频频出入他们的生日晚宴,或者乔迁致喜的冷餐会上。我不能忍受这帮可爱的家伙对中国茶的认知和欣赏还停留于暗香浮动的茉莉香片上。因而每次,趁对方揭开礼品盒并做出激动得大惊失色的样子时,我便不失时机地告诉他们:这可是最好的中国茶,仔细品尝啊!
后来再次碰面,朋友们多半会眉飞色舞,郑重其事地向我描述铁观音带给他们的美妙感受——那色泽、那醇香、那韵味,绝不是茉莉花茶可以比拟的,真不知道,竟有这样好的中国茶呢!虽然铁观音在祖国还算不上顶级名茶,但对于千里之外的他们来说,能从茉莉花茶过渡到铁观音,已经可喜可贺了。
不久前,我在西伯利亚的东方快车上,结识了一位名叫“Jasmine”(茉莉花)的英国老人。那是7月的一次晚餐上,一位身材修长脸也长的英格兰老太太,刚好坐在我的对面。她衣着华贵,头上扣一顶插着白色羽毛的礼帽。为了固定座次,火车的餐桌上会不时贴上乘客的姓名。当我看到餐桌对面清晰标有Jasmine这个名字时,还以为今晚供应的饮料是“茉莉花茶”呢!
面对我的好奇,老太太给我讲了一段她爷爷与中国茶的故事。
那是1658年,伦敦报纸第一次为中国茶打出了广告,称之为“中国饮品”。英格兰的天祥洋行是最先从中国进口茶叶到英国的公司。每当载着中国新茶的远洋货轮停靠在伦敦码头,都会引来英国茶客的一片骚动。茶叶从上海出发,途径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继而横跨英吉利海峡。茶叶的行情,总是随着英国人对下午茶的钟爱而一路暴涨。
茉莉花的爷爷是天祥洋行的第三代进口商。
茉莉花出生那天,爷爷正端坐在上海外滩的汇中饭店里,和一位中国淑女边喝茶,边聊天。爷爷是迷恋中国的茉莉花香呢,还是真的爱喝茉莉花茶?她至今也不清楚。但父亲接受了远在中国的爷爷的指令,给他心爱的孙女取了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
茉莉花太太呷了一口俄罗斯红茶,接着说:知道吗,中国茶最初到了伦敦港以后,是靠骆驼队运到俄国的,要走上几个月呢。茶叶装在麻布袋子里,驮在骆驼背上,一路艰辛跋涉,骆驼因劳累出了很多汗,潮气透过麻袋渗进茶叶里,那茶叶便添了一种特殊风味。俄国人对这种味道渐渐习以为常,甚至有了依赖感。有了火车以后,英国人随即通过这种更加快捷的工具来运送茶叶,却招来俄国用户的一片抱怨:你们的茶叶有问题,味道不纯正!
为了恢复原来的风味,爷爷的公司就往每块茶砖里放一撮骆驼毛。说到这里,茉莉花已笑得前仰后合,头上的羽毛抖动得似风中的花枝,摇曳生姿。俄国人酷爱中国茶,只要喝得起就喝。茉莉花继续说,爷爷从中国回来之后,最看不惯那些往茶里放牛奶和柠檬的英国人。他说,只有野蛮人才会用这些小零碎,来糟蹋真正的中国茶!
为什么英国人把饮茶时间定在下午4点钟呢?我问。这习惯,连英国殖民地的猴子都晓得。有一年我在肯尼亚的蒙巴萨度假时,一到下午茶时光,周边的猴子们就成群结队地涌过来,蹭吃蹭喝,难以招架。
老太太扬起骆驼一样的脖颈,说道:这习惯从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英国园子多,水草丰美,坐在花木扶疏的园子里,把午餐之后到晚餐之间(英国人晚餐通常在8点钟)的漫长时光,消磨在一杯好茶、两盘甜点、几支悠扬的曲子里,是何等的人生享受啊!
听着听着,我的眼前霎时浮现出米黄色的糖罐、奶罐和做得像宝石一样五颜六色的小甜点来。其实,不独是英国,整个欧洲的家家户户,都十分倾心于下午茶的宁静与闲适。无论是古典还是时尚,是乡村还是城镇,烤上一块蛋糕,约上几个朋友和家人,守着一壶咖啡和酽酽的茶香,安然享受这份生活的馈赠,这已是欧洲人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由此觉得,尽管茶叶最初产自中国,但中国人喝茶的仪态,远没有欧洲人那么讲究。真正能够坐下来细品功夫茶的国人能有几个?一切都匆匆忙忙,来不及感受。生活、艺术和审美,便在那匆忙里,难以捡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