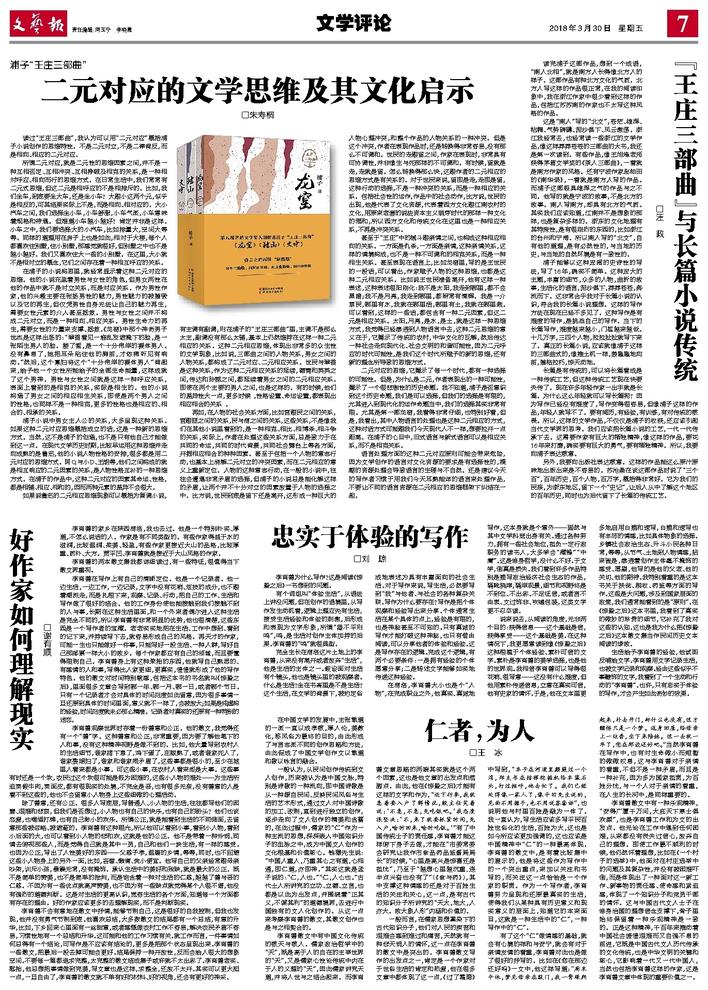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主张载道的一派一直以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为最终的目的,由此形成了与言志派不同的创作思路和方法,由此促成了中国文学创作文以载道和歌以咏言的融合。
一般认为,从民间创作传统到文人创作,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文脉,特别是诗歌的一种流向,即中国诗歌是从一种源自民间、反映民间风俗与生活的艺术形式,通过文人对中国诗歌的加工、改制,直到进行独立的创作,逐步走向了文人创作的精美和含蓄的,在此过程中,儒家的“仁”作为一种主流的思想,深深嵌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文人创作的文化根基和价值核心。钱穆先生说:“中国人重人,乃重其心之有道,心相通,即仁道,亦即神。”其实这就是孟子说的:“仁,人也。”“仁,人心也。”古代士人所讲究的立功、立德、立言,也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并围绕着“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去进行中国独有的文人化创作的。从这一点来考察李育善的散文,其散文创作也是与之相契合的。
李育善散文中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敬天与敬人。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天”,既是高于人的自在的主宰世界的“天”,又是儒家心性论传统中内在于人的义理的“天”,因此儒家讲究天道,并将人世与之结合起来。而李育善文章思路的两端其实就是这个两个因素,这也是他文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他在《惊蛰之后》才能有这样的文字和作为,“放下行李,我就急着要入户了解情况,殷主任笑着说:‘不急,不急,先吃饭吧。’我态度很坚决:‘不,来了就要抓紧时间,先入户,啥时回来,啥时吃饭。’”有了中国传统士子的责任感,李育善才能这样俯下身子去做,才能在“市委常委会研究让我作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的时候,“心里是高兴是惊喜还是担忧”,乃至于“越想心里越沉重,连半点兴奋也没有了”(《食与药》),其中支撑这种情感的还是对于百姓生活的关注和关心,这一点,是有古代的知识分子所讲究的“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内涵和价值的。
一般而言,在儒家思想熏染下的古代知识分子,他们对人民的疾苦和艰难会感到难过和痛苦,天然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一点在李育善的散文中是突出的。李育善散文写作的出发点之一,肯定是一个作家对于世俗生活的肯定和热爱,他在很多文章中都体现了这一点,《过了霜降》中写到,“车子在河道里颠簸过一个湾,郑支书在指挥挖掘机给车装石头,打过招呼,他去忙了。我们已经处得像一家人了,像平凹先生说的,见面不用握手,也不用说客套话”,也说明他与村里百姓是融为一体了。我一直认为,写生活应该多写平民百姓世俗化的生活,百姓为大,这也是如今所应该更加强调的,这也应该是中国精神中“仁”的一种最高体现。李育善的散文中,是有着比较集中的展示的,他是将这些作为写作中的一个突出重点,来加以关注和书写的,而关注这一点恰恰是一个作家的职责。作为一个写作者,李育善努力呈现和还原最真实的生活,使得我们从某种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层面上,知道它的本来面目,这就是一种生活中的“仁”,一种写作中的“仁”。
有了这个“仁”做情感的基础,就会有心境的祥和与安宁,就会有对于亲情友情的看重,李育善对此也是做了很好的抒写的。比如在《您在那边还好吗》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周末午休,梦见母亲在敲门,我一骨碌爬起来,扑去开门,却什么也没有,这才醒悟只是一个梦。返身回屋,给母亲上一炷香,坐下来陪她。这一去就一年了,您在那边还好吧。”当然李育善在写作中,也有对生命微小而短暂的微微叹息,这与李育善对于亲情的看重,不但不是一种矛盾,而且是一种补充,因为多为国家担责,为百姓分忧,与一个人对于亲情的看重,在人生的长河中,是同样重要的。
李育善散文中有一种乐观精神,“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是李育善工作和为文的出发点。他无论在工作中遇到任何困难,从来都没有丧失过信心,放弃自己的理想。即使工作最不顺利的时候,他仍然怀着理想,比如在《一个村子的选举》中,他面对在村庄选举中的问题及其复杂性,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体现出了一种面对这一新工作、新事物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的情怀。这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在修身治国的理想信念支撑下,骨子里始终保留着一种乐观精神是一致的。正是这种精神,千百年来推动着中国社会缓慢艰难而又自强不息的前进,它既是中国古代文人历代传承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华文明的关键和核心,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当然也包括李育善这样的作家,这是李育善文章中体现的重要价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