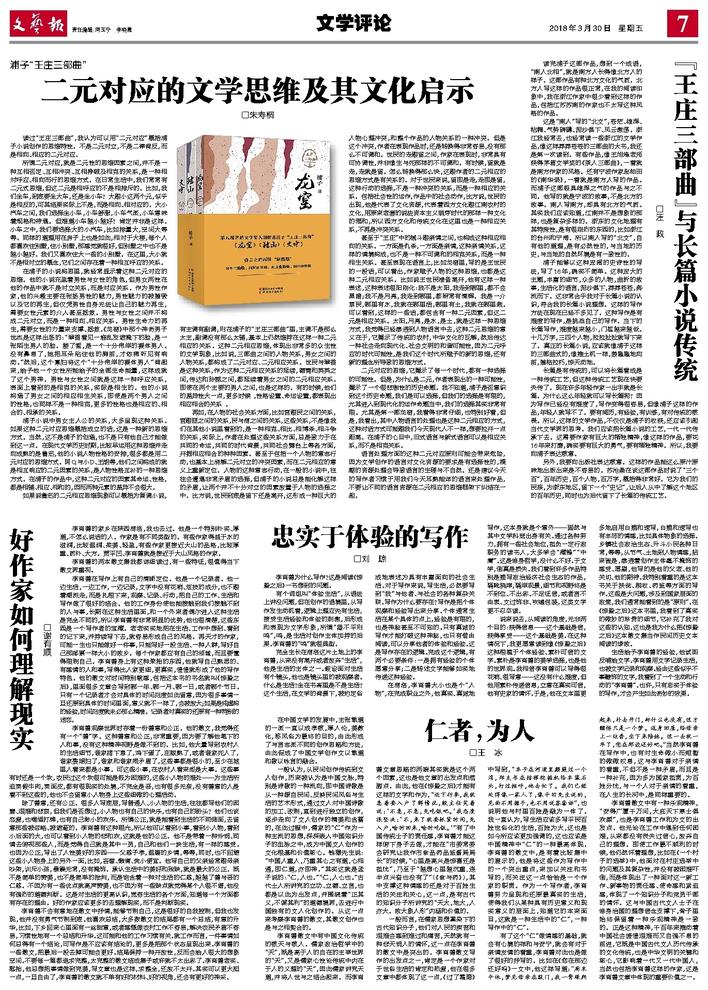李育善为什么写作?这是阅读《惊蛰之后》一书想到的问题。
有个词组叫“体验生活”,从语法上讲没问题,但在创作的语境里,从写作发生动机看,逻辑上理应先有生活,接受生活经验和体验的刺激,后形成和表现为文字形象,所谓“器不平则鸣”,鸣,是生活对创作主体加持的后果。李育善的“鸣”就很典型。
完全生长在商洛这片土地上的李育善,从来没有离开或者放弃“生活”,他是生活的主体之一。假设面对生活有个镜头,他也是镜头里的被观察者。什么是生活?坐在书斋里是不是生活?这个生活,在文学的背景下,被约定俗成地表述为具有丰富面向的社会生活。对于写作来说,写生活,必然要写到“我”与他者、与社会的各种复杂关联。写作为什么要存在?写作是把个体观察和经验写出来分享。个体通常生活在某个具体的点上,经验是有限的,也是神秘甚至不可知的。只有真诚的写作才能打破这种神秘,也只有借由阅读,可以分享他者的体验和经验。这是写作存在的逻辑。完成这个逻辑,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拥有经验的个体愿意分享;二是转述文字能够如实地传递这种经验。
在商洛,李育善大小也是个“人物”,在完成职业之外,他真实、真诚地写作,这本身就是个意外——固然与其中文学科班出身有关。通过各种努力,拥有一些社会地位,担负一定行政职务的读书人,大多学会“藏锋”“中庸”。这是修身哲学,没什么不好。于文学,倒真是损失。我们看到许多作品特别是描写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的作品,隔靴挠痒,隔岸观景,细节和视野终是不到位、不出彩、不足征信,或者言不由衷、文过饰非、吹嘘包装,这类文字更不忍卒读。
说来说去,从阅读的角度,无非两个目的:获得信息——这个基础是信,获得享受——这个基础是美。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愿意读到像《惊蛰之后》这种根植于个体经验、素朴可信的文字。素朴是李育善的美学选择,也是他的世界观。我相信李育善可以写得很花哨、很写意——这没有什么难度,但他用素朴传递信息,立意在真实可信,他有史家的情怀。于是,他在文本里更多地启用白描和速写,白描和速写也有丰沛的情感,比如具体物象的选择。乡镇社会政治生态、升斗小民各种日常,等等,从节气、土地到人物情感,拈来皆是,渗透着创作主体毫不掩饰的感受、愿望,他写的是他的父老、他的关切、他的期待。我特别看重的是这本书关于扶贫、税收、药监等方面的写作。这些是大问题,涉及到国家层面的政策,我们通常能看到的是“原则”。在《惊蛰之后》这本书里,我看到了真实的微妙的珍贵的细节,它补充了我对这些的认知。这也是我为什么把《惊蛰之后》这本散文集当作民间历史文本阅读的缘故。
生活给予李育善的经验,他试图反哺给文字。李育善用文字记录生活,也被文字记录和观察。经由这些似乎不事雕饰的文字,我看到了一个生动和行动的“李育善”。也许,只有忠实于体验的写作,才会产生如此奇妙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