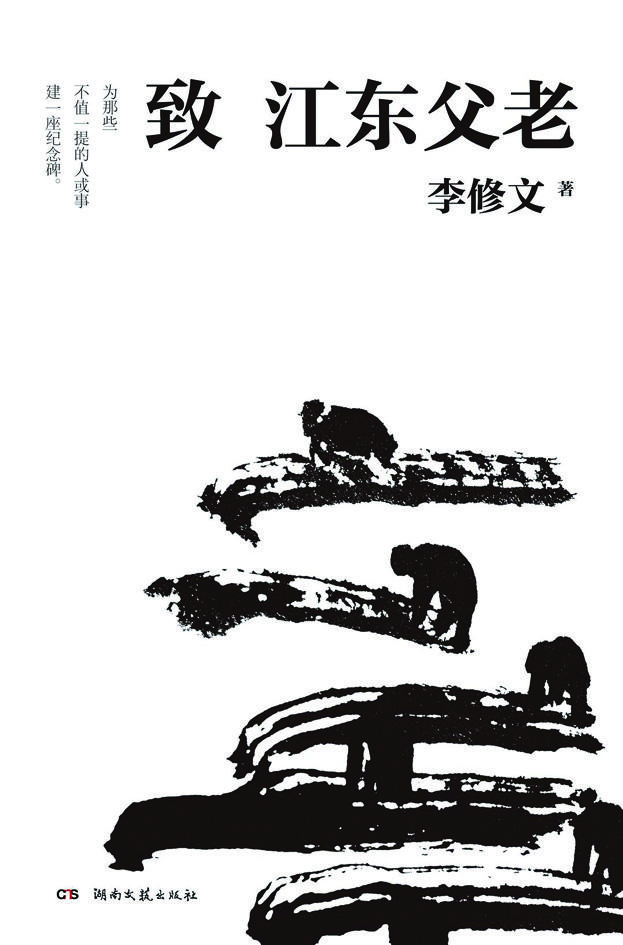一部带有异质性的散文集
——写作者并不是在反抗某种文体形式,而是在无限追随我们的内心。
化 城:文学是一个开放世界,我们自然不应该被任何一种概念所局限,或者拿出某种道德律令姿态,告诉写作者你不应该这么写。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判定某个文本是散文还是小说?我想用“情感调性”来说明。如果把“情感调性”比作一个直角坐标系,原点是“我”,横轴是文本,纵轴是手法,离“我”越近,它就是散文,超过某个数值,即为小说,目前暂时无法判定这个数值在哪,应该将众多文本放置在这个坐标轴中来才能确定。《致江东父老》跳脱出我们固有认知的地方在于“小说笔法”,但我相信大家在读这些文章时,都能感受到一种普遍的情感。这证明了一个结论,无论怎样,《致江东父老》都是一部“我”特别强大的文本,这份情感如此稳固、恒定,无论作者使用的手法多么丰富,依旧无法甩开它。书的标题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致江东父老”虽然缺了主语“我”,但却是隐性的“我”“面对江东父老”的书写。可以这样说,写作者并不是在反抗某种文体形式,而是在无限追随我们的内心。
山景琦:我不喜欢标签化。我认为,当一个事物有了确定的标签时,它就已经死了。这些标签像一个不可打破的框架,将它所有的可能性锁在其中,扼杀了向外拓展与创造的空间。而对于散文而言,形散而神不散,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朦胧的概念。这种朦胧,反而给了散文更多的可能性与伸展空间。李修文的作品,就像在散文与小说之间朦胧的边界上游走,吸收着两方的营养,既增强了可读性,又使炙热的情感能够自然地抒发。
张佳音:我想以《猿与鹤》来具体说明。首先,这不一定是真实的事,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很难看到一只想自杀的猿和一只混入鸡群的鹤。这更多的是人精神世界的象征,现实中可能有这样的原型,但是在散文写作中将真实的事情进行了较多艺术化处理,猿是深沉抗争的,鹤是直冲云霄的,它们都不甘于浑浑噩噩混日子。作者用猿与鹤的形象表达自己心中的丘壑。第二,这篇散文很有画面感,比如猿在电闪雷鸣中从悬崖上一跃而下,颇具电影镜头的效果,而且作者将猿的笼子设计为高大的关押长颈鹿的笼子,呈现出猿正襟危坐的富于尊严感的画面。第三,这篇散文也很戏剧化,写主人公与作家之间的冲突,写作家如何羞辱他嘲笑他,人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态度鲜明,没有日常生活中的委婉和遮掩,与一般散文表现的日常性有所不同。最后鹤为了飞上高空而撞死自己的结局也很出人意料,这是戏剧性的体现。那么这篇文章为什么算作散文而不是小说呢?虽然有虚构的主人公、情节、场景和戏剧化的夸张手法,而且还表明这是虚构,但它的核心不是创作故事,而是展现自己现实中的经历,以及自己的思考和感情,所以我觉得这构成了它是一篇散文而不是小说的原因。
汪 琪:《女演员》是《致江东父老》里我最喜欢的文章之一。我在开始时是以读故事的心态去读的。中年落魄的女演员,傲慢、势利眼、前倨后恭,按理说是很不讨人喜欢的。但是当她带着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剧本修改中去的时候,当她收起一个演员的尊严在葬礼上唱歌的时候,当她知道自己所有的付出终成泡影后静静地站在海边的时候,她太打动我了。虽然作者在写作时用的都是小说手法,势必也有很多虚构的情节,但文中“我”的存在感太强了,字里行间有太多作者的个人情感了。之前大家讨论散文到底应不应该用小说的写法,我认为如果借用小说的手法可以让一个故事、一篇文章达到最好的表达效果,那又为何不可呢?
邱雨薇:我想谈一下这本书在真实与虚构的把握上对我的启发。虽说总的原则应该是以真实为基础把握一个“度”,但还是可以看到作者的探索。尤其是《何似在人间》这篇文章,作者似乎在使用一种刻意营造的含混和不确定性。首先是时间、空间的含混。文中有时代的暗示,以及 “那一年,几年前,两天后,三个月后,猪狗不如的六年”诸如此类的提示词,但是却没有明确的时间点和准确信息的出现。其次,是言说者身份的含混。作者使用近乎“转录”的语言进行叙述,是作家写出的“才子”的语言;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口语的修饰成为正常的事情,但是也因此可以将作者完美地隐蔽在讲述者的语言里。作者用讲述者的视角进行叙述,而自己全程仅仅以称呼的形式出现,叙述者的提问和回答同时都是作者存在的证明,作者似乎没有出现,但是作者无处不在。再次,是言说内容的含混。叙述者的人设是间歇性躁郁症。叙述者口中的内容随时有可能成为“不清醒”时候的叙述,没有判断的标准。最后,是言说对象的含混。叙述者对于作者的称呼是“仁兄”“你”“兄弟”,但是这样的称谓指代是很模糊的,可以是在现场与他交谈的作者,也可以是在不同的时空中与文本相遇的读者。因而这种含混为文本提供了更多的时空弹性,也就增加了不同时空的读者对其产生更强共情的可能。这样的含混本身模糊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于客观真实过分追究的意义,这让我很受触动。
王 喆:文集里的大部分文章都存在虚实结合的写法。真实的写法有两点,一是事件的真实性,二是内在精神外在化,即现实化真实感。例如,《观世音》一文中,“我”在修补佛像的时候,却看到了早已走了的老秦又回到原来的房间,笑着跟“我”聊天,这是作者内心想象的一个场景,但他确切地告诉读者这个场景真实存在,他真的看到了。内在精神外在化,个人内心体验与现实结合成一个新的世界。《女演员》里,“我”经过熟悉的地方,熟识的女演员迎面而来,而此刻的女演员已经去世了,但“我”告诉读者她就在那里,不可质疑。他虚构的地方在于所有事件巧妙的组合。这是一种创作手法,虚构自然流畅。
袁 媖:李修文的文本呈现出来的事实是,他似乎一直在触碰散文的边界。因为我们感觉他的散文像小说。“像小说”,那就是我们认同他的散文还是在散文的边界内。这种认同其实提供了一种暗示,散文的边界还可以再触碰,同时,也可以说李修文的散文文本表现的是散文内部的变化。比如长度变化,肯定会带来结构的变化,而结构的改变就会引起承载力的变化,那么散文是否可以容纳更多的人物和叙事,以及使用相关的技巧?
唐楚涵: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李修文老师的作品主观色彩较为浓厚。具体的表现就是不论本书中的文章是以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我”的存在都很明显。叙述者就连笔下人物的内心状态、复杂的情绪活动都似乎洞若观火。不过,这就是散文文体的特点。一般来讲,剧本往往是纯粹的客观叙事,只能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来构建一切。散文中作者就要显得全知全能一些,“我”的认知与情绪都可直接外露。小说在主客观问题上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存在。纯客观叙事往往是由作者通过拼接客观来让读者自行感知到作者埋藏的主观表达,这样做使主观表达具有了足够的可信度。偏主观的叙事虽然降低了可信度,但也有好处:文章的指向更精准。我认为在《致江东父老》中,李修文在追求一种散文表达可能性上的变革,将小说或剧本的客观叙事大量融入散文写作,从而使主观、客观、可信度、精准度达到一种平衡。不得不说,对于散文文体来讲,这是一次大胆且较为成功的突破。
散文写作的可能性
——正如习武之人,只有勇于打破门户之见,才有可能取长补短,成为集大成者。
阎 旭:我们讨论的话题主要围绕散文文体的可能性。如果追溯散文概念的形成,它其实是受西方文学理论影响的一个后起的文体概念,现代文学诞生以来,我们以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的体裁划分,进行文学研究。但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本身是两个不同时段、不同性质和思维的行为,所以如果今天以“写得像散文”的文体标准来评判一篇散文的优劣是不恰当的。那么今天评价一篇好散文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从散文写作的出发点上给出一个标准,那么,我认为一篇好的散文应该建立个人的美学。在《致江东父老》中能看到很多这种建立个人美学、冒犯散文陈规的尝试。首先,李修文看世界的眼光始终是自下而上的,与人民和生活站在一起,赋予每个渺小的人以存在的意义。读这些人和事,让人在文字中接受来自世界的启示,反复擦拭见出普通人的人性光泽。如果将《山河袈裟》与《致江东父老》比较而言,后一本书更倾向于一种作家声音的隐退。在散文集《山河袈裟》中,如《羞于说话之时》诸篇,仍以作家的个人抒情为主体,但新作中作家进行了一种隐身,多篇均以人物之口叙事,这也是使其近似于小说特质的原因之一。第二点,我想谈李修文的语言。我觉得他受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很大,这既是一种文化滋养,也是作家回归传统的自觉追求。这种借鉴体现在散文的叙事中,不是冗赘的长句,反而三四错落,长短相杂,交替迭出,颇似韵文旋律化的表达。在文字的使用上,多白描场景,少修辞,却字字精准锋利,似传统文人小说如《聊斋志异》《水浒传》中的场面描写。与作者的目光看向的人和世界相联系,叙事中常常有一种“江湖气”。李修文正是寻找到了戏曲、古诗、史事中的精华作为情感表达的出口,承载人民社会的江湖义气。以中国式的语言表达,表达中国人的情感。
常旻雨:我想说的是散文塑造人物的可能性。之前我的阅读经验让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当代经典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对我们来说,其实已经随着时间的更新而渐渐变得遥远了。说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却已经逐渐变成了远方和远方的人们,而新的“我”在哪里?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下的青年,我的生活里已经有很多新的矛盾和冲突,我希望能在当下的文学里找到它们。所以我在看这本散文集的时候,注意到里面有很多和我的生活很贴近的人物形象,比如为了儿子的一句话而拼命要拍戏的女明星,弟弟们在外打工、自己留在小镇的姑娘,她拖着病体在雪夜走山路去“偷青”,为了没有娶上媳妇的弟弟,“她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她又想,她去偷过了,总好过没有偷”……这让我感觉到另外一种打动我的方式。不是像那些从1940到1980的人们打动我的方式,而是从1990到2019人们的新经验。所以散文的可能性是否在于它对于表现人物存在着更加自由、更加敏感的地方?它可以比其他文学形式有更加细长的触角去探进我们时代的生活。
康佳欣:对我而言,一篇好文章,它会告诉你一些你不曾注意到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或者与你有着某种关联的关照性。我大致猜想了一下李修文的写作过程,或许他最开始就是想要表达自己——情感是推动他写作的动力,然后他选取了一些东西来表达自己,可以是自己经历过的,脑海里想象过的,当然也可以是完全虚构的,因此我们探讨虚构与真实。我认为没有发生过的,不一定就不能称为一种真实。比如《猿与鹤》这篇,我不知道文中的猿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作者到底见没见过鹤,但是我看到的是作者自我的不断反思和突破,猿与鹤是作者的两个影子。背后存在一个苦闷的、纠结的主体,他表达出了人性的苦闷与挣扎。这种主体性的体现、情感的贯穿,也是散文的一种可能。所以,我觉得在创作之初不能守着一种文体规范,应该注意文章本身的价值是什么,它能够带来什么,因为文体毕竟是为文章背后蕴含的价值和表达的内涵服务的。如果达到了这一点,对于文体来说也是一种突破。
杨 毅:其实我们没有必要特别在意这个作品究竟是哪种文体,我们应该关心的是文体背后的内容,也就是它有没有接近世界的“真实”。为什么今天会突然出现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甚至带有一种先锋性的写作?其实在今天,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即总体性已经瓦解了,甚至连启蒙话语都变得可疑。如果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真实和虚构的界限也被消解掉了。我反倒觉得在这种真实性不断地被怀疑的年代,才会出现这样的文本,就像现实其实也是人为建构出来的一种认知装置一样。
向 迅:相对于传统的叙事散文,李修文把叙事往前推进了一步,把散文这种文体所能抵达的深度,也往前推进了一步。白话散文经历100年发展,确实遇到诸多瓶颈问题。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问题,当代散文与小说一样,同样大有可为。李敬泽、李修文、周晓枫等人的散文写作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首先要勇于打破固有的文体边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小说、散文、诗歌等文体界限分明,不能轻易越矩,否则会影响文体的合法性。但李敬泽的《夜奔》、李修文的《观世音》、周晓枫的《有如候鸟》等,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该如何界定其文体?固然它们的面目有些跨文体,但其精神依然是散文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他们创立了一种新文体?虽然下定义为时过早,但他们确实以自己的写作实践,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如何打破写作和文体的边界,我认为既要在散文内部做文章,也要在散文外部花工夫。外部,多在形式上进行一些探索;内部,在文章的结构上进行探索。正如习武之人,只有勇于打破门户之见,才有可能取长补短,成为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