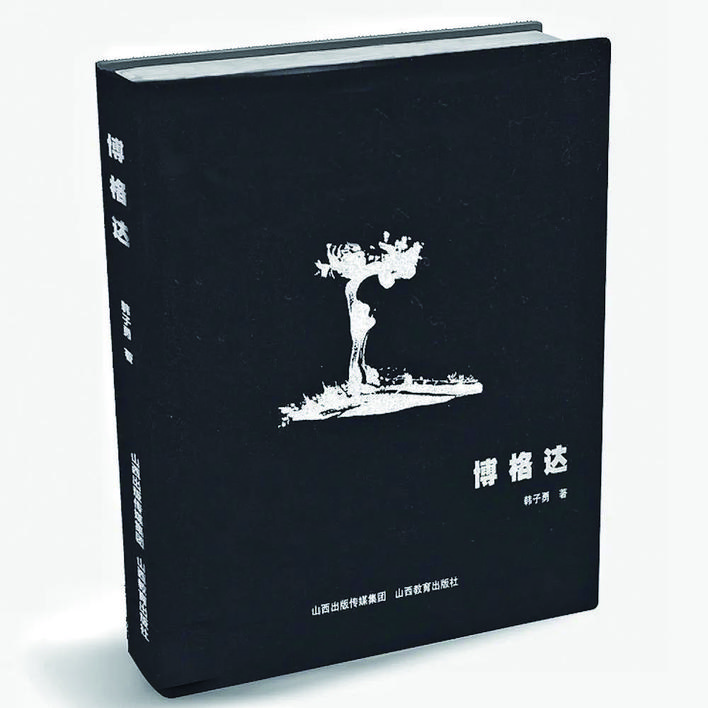近日新读了恩师韩子勇的新作《博格达》。作为一部评论人的诗画集,它那么富有指向性地概括出作为西部以西的新疆,可以被初来乍到者迅速吸引的要素:辽阔的地景、简单的人际交往、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缓慢的时间节奏以及由古至今渴望建功立业者的精神乐园,这几乎也是富强大国边疆之梦的一些主要内容,就仿佛2012年之后,韩子勇由西向东的人生逆旅仍然是在完成一个大国图景之中边疆之梦的叙述。特别是这部书中所收录的2017年以来他的诗画作品,更是记录一名文化学者、作家、评论人如何结合自己的人生位移,将其在新环境中对家乡生活的反复回忆、符码重塑为一份富边强国的家国情怀。的确,这部书是诗集、国画集、文字笔墨互文之中的乡情乡忆、人生反刍,更是行旅之人诗歌吟咏中的家乡之情、游子记忆之景中的边疆之梦。这也恰恰印证了作者反复强调的那句声明:“我的新疆之爱——纵到底、横到边”。
海拔近6000米的博格达峰是新疆东部天山第一高峰,在韩子勇的笔下更是边疆之梦、记忆之景的“精神之地”与“象征之地”。这座山峰在诗歌表述中寄托着他对新疆的亲密感、归属感与认同感,也高度概括出他所牵挂的边疆生活内容。在新疆长期定居生活的人不仅要驯服酷烈的景观,还要适应绿洲、草原与高原等西部地理特点所决定的时空认知的丰富性以及多种生活方式间的平衡或者不平衡性。在这些受新疆地理环境所影响的空间认知、生活经验和场景中,绿洲、农场、毡房、葡萄园、高原、博格达峰等自然也就成为该诗画集中较为频繁出现的空间记忆或景象,一起构成作者记忆之中的“西域地景”,并与其人生际遇的起伏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生感喟自然交织。
新疆地广人稀、丰富多样,无论是长居还是暂居新疆的人,对新疆时空的认知似乎也会产生一种隐秘的魅力,这种魅力由距离、探险、两小时时差的缓慢错觉综合作用而成。因此,在韩子勇笔下,对它的描述也多与僻静、隐秘、空荡、自在、冷清、荒凉、缄默、辽阔、平静、神秘等表述相联,这些基于新疆地理时空认知的表述,充满情感和记忆的投射,是快节奏生活之下几近遗忘的自在之道,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对伴有深切持久满足之感的由衷渴望。
韩子勇的诗画哲学简素、调白、内省,有一种深刻的大地伦理,扎根向长居新疆生活的记忆之景。按他的讲法便是,他并非画家,只是喜好涂鸦,他也总自谦并非纯粹的诗人,只是偶尔写写短小的文字。他大半生都致力于文学批评与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和保护实践之中,这两件事就像是新疆文学与文化艺术界中的博格达峰。他也总叮咛我们这些学生,人一生能做好、做极致的事十分有限,年轻人做学问尤其要珍惜年华,不要三心二意,不可追逐时髦。
韩子勇的诗画文章如同他的文学批评、他的为人一样,在看似锋芒外露、尖锐直白、直截了当的批评话语背后,却蕴含着那么深刻真挚的情感。这份情感如同他对新疆的热爱一般,浓缩了比隐喻更隐喻的真实,充满着比理性更理性的感性,是带有距离的亲近,是仰视与俯视的并存,是冷热交替的相处,是苦涩与甜蜜交织的回忆。一个地方的风景习俗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长期生活于其中的人赋予了它意义并用笔墨记述加以流传,却又不止步于牧歌怀旧,而是用诗画笔墨中的家乡之情压垮真实世界中对它的种种想念,用真正的新疆土著回忆抵抗风光游记中的诸多浅薄。就此来看,《博格达》也是具有这样意义的一本书,其记忆盛景、内心景观、视觉语法远超过了它所指称的地名价值。
掩卷思虑,不由得感慨万千。韩子勇来自祖国边疆博格达峰下辽阔的荒野戈壁,却突然有一天感到无法从中汲取到力量,于是他决定重新启程,向东逆行。这让我想起整个陆地丝绸之路历史中一度向西而行的旅人们,他们或是怀揣创业梦想的打工者,或是受到西部大开发召集一路西行而来的支边者,或是持有坚定人生使命与理想信念的播撒者……他们身上渴望实现边疆梦的精神动力让人感叹。的确,在当代中国,无论是从西向东还是由东向西,与其被理解为一种简单的位置位移或地理迁徙,倒不如被理解为一种精神奋斗或价值观抉择后的过程,其迁移的过程更易被视为一种文化记忆的丰碑,礼赞它的恰是如“西域偏向诗与歌/栽棵白杨住我家”般的豪情万缕或心有千结。
对普通人而言,在新疆生活不需要那么多深刻的道理,更需要的是持续蓬勃的壮志豪情,我想这也是自古至今承载无数人边疆梦的新疆大地所吸引人的地方。它不是你短程驱车经过的一处风景,而是一个需要长途跋涉方能游历全部的地方。它就像是所有中年人渴望再经历行旅启程的青春梦,是一个需要用持续的激情而非绝对的道理去鼓舞生活的地方。这种激情的感召力过于磅礴,有些人天生具备,根本无法逆流而行;这种激情的形式过于抽象,很难被简化为一个或者一系列具体的故事,需用一生奋斗加以概括。就像韩子勇在《博格达》后记中所说的:“那些个大大小小的道理,就是心、生活、生命、人的全部吗?它里面、对面或者就是它本身,是不是还有一股倔强的、压抑不住的、含混强烈的激情、意志、直觉、感性的力量,火热神秘地涌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