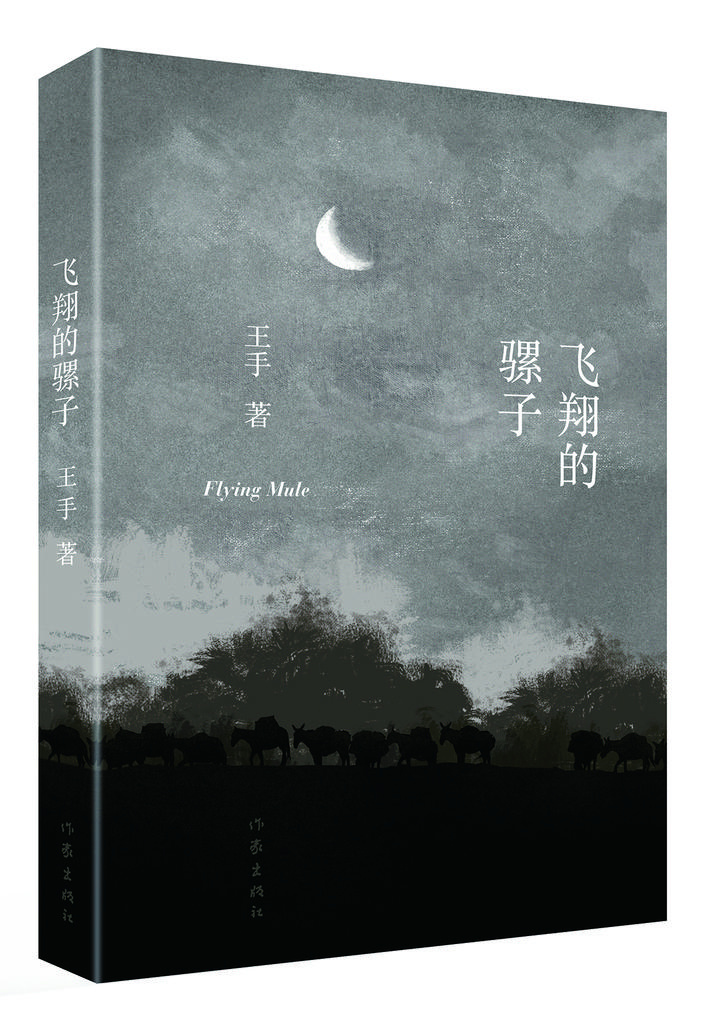每年的五月,宇文都要去上海一次。
五月是一年中最舒服的月份,黏糊的霉季已经结束,天渐渐高了,风也吹得远了,气温就像是刻意调节了一样,设置在半袖衬衣和一件汗衫之间。如果在晚上,那也是最有意境的“线毯”程度,隐约又不累赘。
五月是宇文在心里定下的。说是定,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一年的许多时间,他都是这样忙而不碌,他不会觉得月份之间有什么两样,或者说,他对月份本来就不怎么敏感,有时甚至是昏昏庸庸的。但临近五月了就不一样,他会对日子突然警觉起来,常常在暗地里提醒自己一句,噢,再过几天就是五月了。于是,心里记挂着,小心地、不动声色地在五月的日子里匀出两天……
宇文去上海是为了去看小雨。一直以来,他想着能和小雨睡上一觉。
有一段时间,宇文在自己的小城里是焦灼的。这个小城有许多民间私拟的竞赛内容,比如青年比才、中年比富、老年比子女,这些项目像鞭子一样抽打着那些仁人志士,激励着他们奋力拼搏。宇文自忖,自己的“而立”已经过去,他尽显才华了吗?自己的“不惑”即将开始,他有富裕的迹象了吗?子女那是后事,暂且按下不表。对于前面两项,宇文的回答是,马马虎虎,不尽如人意。尽管这样,宇文还是喜欢这类竞赛的,怎么说它也有积极向上的一面。
这个小城是富裕的。白天在单位,宇文感觉不出它的富裕,他觉得这些和自己无关。他沾沾自喜自己的安逸和优越。他的窗外,是一个叫吟潭的公园,他可以在自己的座位上,呆呆地看上半天树叶。他可以花很多心思,去选择和收集自己品抿的茶种。遇上有把握的求事者,他也可以不用担心地接纳一套小小的皮具。工资,现在都打到卡里了,透支了也不要紧。最不用操心的就是奖金,头儿们总会挖空心思地弄出些招儿,给大家凑个心境平和的数字。但是,到了晚上,宇文的感觉就不那么自在了。那些情调暧昧的茶座,那些灯火隐约的浴室,都弄得他鼻子痒痒的,喷嚏连天。还有,这个小城是禁鸣喇叭的,那些香车宝马总会像蛇一样悄没声息地在他身边匍匐过来,冷不丁地吓他一跳。这个时候,宇文才感觉到,自己心底的不满原来是那么明显。他突然不喜欢这个小城了,尤其不喜欢它完全分离的实质内容。就说那些竞赛吧,白天和晚上,职业和阶层,人和人,都有着大相径庭的标准和要求:第一,要想办法赚点钱,没有钱,在外没身份,在家没地位;第二,有了钱要先购置下一套好房,什么是好的房子?老城区商业街一带的房子;第三,有了好的房子还要安顿好一个家,家是安身立命之本,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不是一个好生活,同样,仅能遮风挡雨,却家徒四壁,肯定也不是一个好人家;第四,光有一个好家还不够,还要有一个好女人,这当然不是指自己的爱人,爱人是感情的一部分,但不是感情的全部,是全部,这个人生就“抑欲寡欢”了。人的感情是丰富的,丰富的感情和单一的生活是不和谐的,要让丰富的感情不至于倾斜,就要有一个外在的因素来平衡它。这四则完全做到,宇文觉得有点难,但努力努力,突破个一二,还是有些把握的。
他就是在这个时候碰到小雨的。有了小雨,宇文心里平静了许多,至少和别人比起来,是不那么落后了。他可以自我安慰地换一种说法:凡事是不能十全十美的,能力也是有所侧重的,堤外损失堤内补嘛,他用小雨来弥补其他。
宇文和小雨是默契的,这种默契不仅仅体现在关系上,还体现在一些细节上。为什么一定要搞得那么清楚呢?他们都这么想。于是,他们的交往就没有负担了。曾经有一次,宇文试探性地问小雨,我能去上海看看你吗?小雨说,行啊,虽说是两个地方,其实也挺近的,交通很方便。宇文进一步说,我若去上海,你是陪我玩呢,还是真的只是见上一面?站在某个标志性建筑下面,隔靴搔痒地拥抱一下?小雨浅浅地一笑,你真会制造意境。又说,白天如果抽不出身,晚上应该有空吧。宇文故作惊讶地说,那不是得留下来过上一夜?小雨说,你计划不在这儿过夜的,就那么蜻蜓点水一下?还是顺其自然吧。这是个接纳和很有余地的信号。本来,宇文还想问得再具体点,比如这一夜在哪里过,在宾馆,还是在家里?后来想想,真是不能太计划了,大方向解决了,细枝末节应该都会是一路绿灯的。
小雨说,你来的那个站叫梅陇。
开始的时候,宇文觉得小雨一定在耍什么花招。比如说自己正在梅陇办事,不方便,然后草草地在路边见上一面,在快餐店里坐一坐,充其量捉个手,尽管情调也有,但宇文觉得,那不是他所期待的。事实上,小雨是诚心的。梅陇是铁路沿线的一个分站,在上海的西南角,出口在虹梅路地铁,距认真的上海站,地图上看,还有一掌,路还不短,在梅陇下只是为了方便,没别的意思。上海是一个“省份”,而梅陇,就像是一个“县级市”。
小雨还说,你来的话,给我带个手机吧,我那个老的被人偷了。宇文爽朗地应了下来,问,你要好点的,还是一般的?小雨说,就那种千八九的红三星吧,我用它已经习惯了。宇文说,那你就自己买一个嘛,我把钱刷到你卡里就是。一个手机,宇文这一趟上海之行就更有理由了。
宇文是晚上七点到达梅陇的。他和小雨约好在地铁的楼上等。这个时候,下班的高峰已经过去,地铁也开得慢条斯理了,站在空荡的地铁楼上,灯光惨淡,等的意味就浓重了起来。宇文知道,也许哪趟地铁过后,小雨就会从电步梯上缓缓上来,然后,笑吟吟意味深长地朝他走来。
小雨还没有来,宇文一时无所事事,楼上还开着的就剩一间音像店了。他对音像有点兴趣,他本来可以进去看看,边看边等,时间就过得快。也许是他滞留在空荡的楼上很突兀吧,店里那个样子前卫的女孩瞄着他看,这样,他再进入音像店就有点别扭了,他只得做出另外一个选择,踱步到那张线路图前,作寻找方向状。在梅陇,他肯定是个过客,东南西北也搞不清楚,但站在线路图前,他还是和谐的,就像线路图里的一个箭头。
他记得小雨说过,她住的地方叫什么庄。他顺着线路找,就找到了一个莘庄,对,就是莘庄。莘庄是这条线路的一个站头,宇文数了数,从梅陇过去还有四站路,这个距离不算远,坐地铁二十分钟,走路也不过一个半小时,也就是说,就算接下来这段时间他有些仓促,拼命在酝酿,到了夜前,也应该有个火候了。
有人像纸一样飘到他身边,碰了他一下,他回头一看,小雨俏皮地向他噘了一下嘴,他顺势就撸过来她的腰,小雨也像模像样地贴上了他。这是宇文第一次来上海,他暗暗有些吃惊,自己怎么做得如此顺风顺水,一点也不生硬,连那个偷偷盯着他看的音像店女孩也觉得无趣了,她本来猜揣,这个鬼鬼祟祟的男人一定有什么精彩,这会儿,她像是突然遭到了枪击,脸上没劲地木然起来。在这之前,宇文和小雨只见过几面,都是在小城,在某个场合。宇文觉得,熟悉的地方总会有一些障碍的;就说程度,仔细分析起来,也只是心仪而已。在上海居然能放得很开,根本不用考虑和准备。宇文感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环境,就是好。
小雨说,现在,你想怎么玩?宇文也装作挺有玩兴的,客随主便吧。小雨说,那我们先去上海影城吧,你看过《花样年华》吗?宇文摇摇头。小雨说,那去看吧,你不会后悔的,就算你闭着眼睛去听听音乐,那个琴也拉得……宇文心想,不就是一个半小时吗?去就去吧。小雨接着说,然后,我们去一个陶吧;然后,我们再去吃个夜宵……小雨又说,你平时有熬夜的习惯吗?宇文勉强附和着,还行。心里却在嘀咕,别再弄出个什么项目,把时间安排到天明。
一辆地铁咣当咣当地响了过来。表面上,宇文也装得兴致勃勃,仔细一体会,自己的脚步有点情绪,不那么欢快。他在进地铁时又下意识地看了看那张线路图,隔远在心里把这条路默走了一下。往西走,就是那个莘庄,虽然只有四站路,但现在和他没什么关系。他们走的是往东的方向,意向是那个上海影城。
上海影城在淮海路附近。在上海,宇文像一只无头的苍蝇,所有的方向都是小雨给的。
《花样年华》确实不错,那条石板路非常有意境,那些旗袍也非常符合情调,那段反反复复起来的音乐,就像小雨渲染的,差点把人给拉死了。
两个小时后,他们又去了隔壁的一个陶吧。做了碗,做了盘,又做了罐,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宇文想起自己原先的打算,这些时间,本来都是他在酝酿的过程,现在看来,原先的想法不很实际。在上海,他得听凭小雨的调遣,小雨不主动,还不想归巢,他就是热血沸腾了也没有用。他暗暗嘱咐自己,慢慢走着瞧吧。
从陶吧出来已经快十二点了,这会儿,宇文怎么也不想再吃夜宵了。他没说自己困了,他不能有太明显的“睡”意,好像他来上海就是为了熬夜。宇文说,我没吃夜宵的习惯。他还说,其实,吃夜宵一点也不卫生。他指的是生活卫生。小雨说,我发现你们这个年纪的人特别讲究规律。宇文说,那是身不由己啊,我们要保持好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小雨笑了一下,那我们早点休息吧。宇文暗想,现在,她的行为指向才步入他的思想轨道。他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他们接下来会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呢?他对如何开始感兴趣。
地铁早没有了。如果就这样走回去,也是挺有情调的。小雨哇了一声,你以为这是你们小城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在上海工作生活了两年,从没有在逛街的时候碰到过同事,你说这地方大不大?宇文点点头,表示相信这个说法。
他们拦了辆的士,驰去。小雨用上海话轻巧地指点司机怎么走,宇文听得不是很懂,但他知道,不管怎么走,那都是往莘庄的方向,去小雨家,他的心开始踏实下来。
这是一间真正的斗室,一间单身女人宿舍。与宇文在小城的家相比,这里是缺了很多内容的,硬件上就差了很多,比如差像模像样的客厅,甚至差两张坐着说说话的椅子,或者说能让人端着形象、正襟危坐的椅子。他们只能够坐在床上,靠着一堆枕头垫子之类的东西。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坐着的,但坐在床上太认真,感觉更别扭,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他们过渡到半躺半靠,这样就让人舒服多了。同时,他们也给自己铺起了想入非非的土壤。宇文想起小雨那句“顺其自然”的话,一般意义上讲,这句话表现得很有风度,很有亲和力,实质上,这句话反而让人拘谨了。顺其自然其实是叫人不自然,因为它把目的点出来了。任何人的相处都一样,有了目的,就浅薄了。假如没有这句话,他们最终也会走到故事里去,但那个性质不一样,那是瞬间擦出的火花,火花属于意外和突发,不是人能够控制得了的。
曾经有一下,宇文的手碰到了小雨的手,他停了一下,他没有惊乍着把手抽回来,他那时候不知要做什么,尖起自己的手指,在小雨的手心上画了几画,他肯定这不是暗示,他也说不清这是什么内容,但这一下像把小雨贴了符咒,她的身体温暖起来。她先是把另一只手也递到他手里,她特地张开眼看了看他,好像是征得了他的同意,或者是得到了什么鼓励,她放开身体,像蛇一样匍匐过来,游到他身上。这时候,宇文要是再停留在她手上就坏事了,就要呆滞了。他把自己的手抽出来,在她的背上轻抚了一下。他相信,对某些人来说,抚背也能唤起她的“性趣”,于是,他听见她一声很轻的、不易察觉的呻吟。
(摘自《飞翔的骡子》,王手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