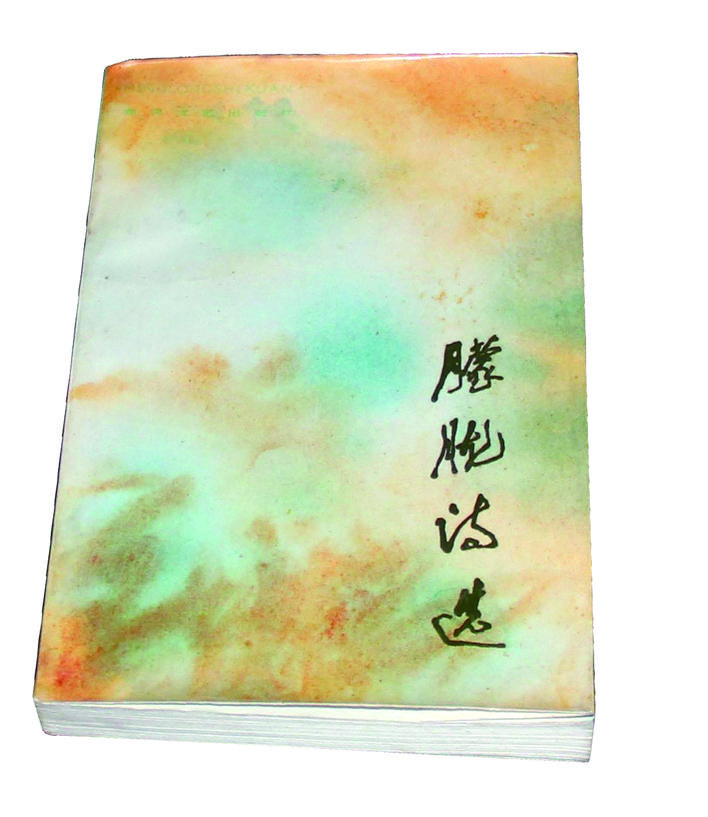如果以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8首白话诗作为中国新诗的起点,如今新诗已经度过了它的百年华诞;如果以1920年1月新诗社编辑部编的《新诗集》(第一编)的出版为标志,中国新诗选本也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百年来的新诗编选活动,不仅是新诗传播与经典化的重要环节,也与新诗创作相互呼应、紧密相连。
在新诗问世后不久,新诗选家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最早的一部诗选应该是《新诗集》(第一编),新诗社编辑部编辑,新诗社出版部于1920年1月出版。此外还有许德邻编的《分类白话诗选》(1920年8月)、新诗编辑社编的《新诗三百首》(1922年6月)、北社编的《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1922年8月)等。这时候,新诗创作与新诗编选都处于草创与初步发展期,因而此时的选本,更多具有传播新的诗歌理念、维护新诗合法性、保存新诗文献并实现初步的经典化的意义。作为中国新诗年度选本的开山之作,《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选目严谨、点评精当,备受新文化界赞誉。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8月何仲英编纂的《白话文范》第二册首次收入了3首新诗: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沈尹默的《生机》。这是新诗首次进入国文教科书,其意义也是十分重大。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新诗创作的推进,新诗选本领域出现了朱自清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这样的经典选本。该选本彰显了中国新诗第一个十年的实绩,以“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勾勒出新诗史,选入了周作人的《小河》、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戴望舒的《雨巷》等优秀作品,建构了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等诗人的经典地位。他还注意各家诗人风格的多样性,比如选录了闻一多的《闻一多先生的书桌》这样“纯粹的幽默”的作品。
在40年代,较多的是个性化选本,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闻一多编选但未能完成、出版的《现代诗钞》。闻一多坚持诗歌美质,格外欣赏同为“新月派”成员的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但除了“新月派”,他选收“现代派”与“抗战派”的诗人作品却又比较多。或许这也是他的矛盾的体现:他的选本,已不是纯粹的文学选本,而是力图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方案。这展现了闻一多为民族与文化寻找“一剂药方”的宏愿,而这剂药方的发展方向,正是人民的文艺。
1949至1979年,新诗创作与编选都展现了新的时代面貌,以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为准则,建构人民文艺的传统并作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规范。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版的各种文学丛书其实也是具有特殊意味的选本,如“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新文学选集”与“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这些大型丛书的出版,建构起一条完整的新诗史线索。在这些丛书中,郭沫若、朱自清、闻一多、殷夫、艾青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现代三十年的新诗成就;1942年以后,则以李季、阮章竞、田间等为代表。其中,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又是具有标志意味的“人民的文艺”的经典之作:它以民族的民间的形式歌唱解放区的新人新事,塑造新时代的新模范。
就专门的新诗选本而言,1957年开始出版的年度诗选,及时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与新诗创作的成就,而综合性新诗选本影响最大的是臧克家主编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成为当时青年人了解中国现代新诗的重要选本。臧克家以革命史来确立新诗史线索,强调现实主义原则,将郭沫若、艾青、闻一多、殷夫、田间确立为中国现代诗人的代表,肯定了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总体而言,臧克家对新诗史脉络的梳理、对代表性诗人诗作的选择和评述,是很有眼光的。
1979年至2000年是中国新诗创作与编选回归审美本位、开启多元化格局的新时代。诗坛的拨乱反正与新诗选本的破冰之旅结合在一起,这一破冰行动首先是通过回顾历史、重塑现代新诗史而进行,其标志性成果就是1979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共同主编的《新诗选》与1980年诗刊社编选的《诗选》出版。它们开始突破单一的政治标准,收入以往被视为资产阶级诗人的胡适、周作人等,也收入了“归来者”诗群的作品,一体化的格局开始打破。
20世纪80年代,新诗选本大规模地向诗歌流派倾斜,如《新月派诗选》《象征派诗选》《现代派诗选》《九叶派诗选》,正体现出对审美本位的认可,它们同时具有指导新诗创作的现实意义。阎月君等在1982年编印、1985年出版的《朦胧诗选》,更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象征,“就像久旱春天的一声春雷”,震撼了全国。朦胧诗潮的人道主义情怀、求新求变的艺术手法,对诗坛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也在读者中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反响。
90年代,随着经典热的出现,审美现代性的追求近乎极致,但仍然能够在“20世纪/百年中国文学”的思路下兼顾审美性与历史性。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有张同道、戴定南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和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他们都强调了文学回归审美本位、追求审美现代性的重要性,由此都对80年代诗歌特别是朦胧诗给予了极大的倾斜。此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收入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诗界革命”代表人物的作品。
21世纪以来是个未完成的阶段,新诗选本的多元化与新诗本身的多元化一致,选本的多元混杂、众声喧哗是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百年中国新诗”成为新诗研究与编选的范式,审美固然是衡量作品的最重要尺度,但选家的编选立场带有更丰富、多元的文化意味。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20年,年度诗选与综合性选本影响最大,这两类选本都与时间有关,前者可以在场地展现当下诗歌成果,后者则与新诗百年诞辰有关。就前者而言,主要有六大年选:长江诗歌年选、《中国新诗年鉴》、太阳鸟诗歌年选、漓江诗歌年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花城诗歌年选等。六大年选注意到新诗格局的多元化、网络的兴起对于诗歌写作与传播的冲击、新诗创作的叙事化倾向等,在时间线索的追踪中勾勒出中国当代新诗的发展印迹。
综合性选本中规模最大的是《中国新诗总系》《中国新诗百年大典》《中国新诗百年志》等。谢冕等人编选的《总系》从“现代性质”这一根本点出发,以“选”叙“史”,不仅数量上超过以前选本,在作品质量上也严加把关。以胡适为例,姜涛在编选时既收入胡适在白话实验与诗艺探索方面较好的作品如《一念》《鸽子》《湖上》《梦与诗》等,甚至收录了译诗《关不住了!》,以及《十一月二十四夜》这样之前不大受关注的作品。《总系》还发掘了大批边缘化、被忽视的诗人诗作,如刘延陵、王怡庵、关露、贾芝、刘廷芳、朱英诞、吴兴华、灰娃等。《大典》将编选下限延伸至21世纪,更多地表现出对当下诗歌的关注。中国作协于2015年组织编选的《中国新诗百年志》,分为作品卷(上下卷)和理论卷(上下卷)共4卷,收录了426位诗人和诗评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460多首诗歌和80多篇诗论。张新颖编选的《中国新诗:1916—2000》将以往选家较为忽视的40年代与90年代诗歌作为重点,突出了冯至、穆旦、海子等诗人的地位。它们是对中国新诗前所未有的总结与筛选,重新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新诗史图景。
中国新诗选本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与新诗创作一样既有辉煌,也历经坎坷,新诗选本促成了中国新诗的经典化,铸就了中国新诗的百年辉煌,同时也成就了自身:一大批经典选本确立了自身在新诗史上的地位,它们以深刻的诗歌观念、精准的评选眼光、公正的新诗史观,为新诗创作与接受提供了重要参考。新的百年之门已经开启,中国新诗创作与选本编选仍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