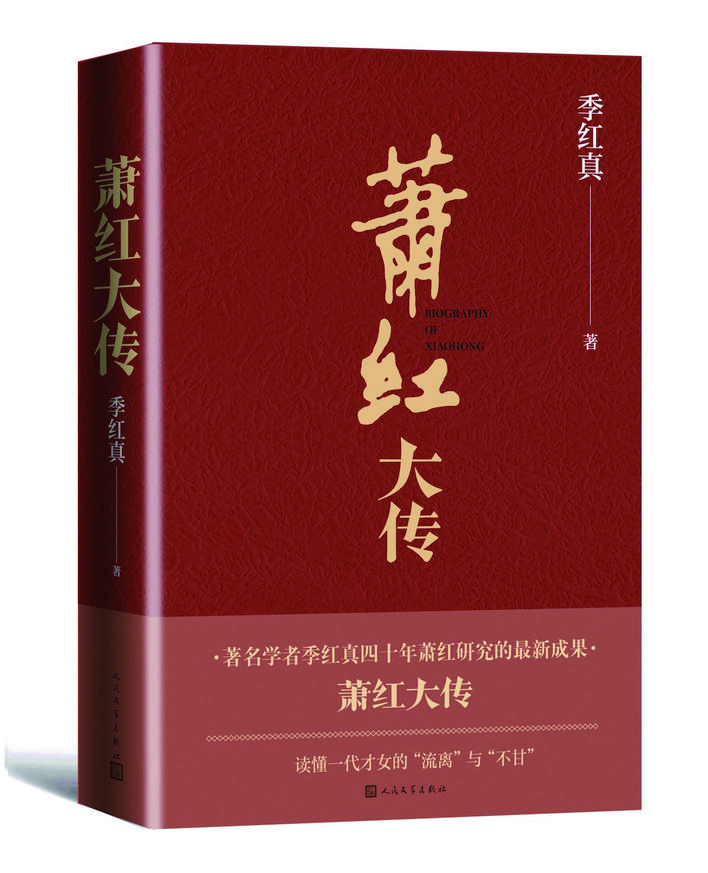季红真的萧红研究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她写作的《萧红传》就作为十月文艺出版社著名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之一出版,影响甚广。进入新世纪以来,她用更丰富翔实的历史细节与斑驳交响的时代回声不断完善研究成果,陆续修订了多个版本的《萧红全传》,并编选《萧萧落红》一书,漫忆萧红一生的传奇经历与精神风貌。今年,适逢萧红诞辰110周年,季红真50余万字新著《萧红大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装发行,“呼兰河女儿”一生的坚强与挣扎更加鲜活。不断地占据新史料,不断地采纳新观点,季红真对萧红的持续性关注可谓“深耕”。几十年间,反复阅读、查找资料、走访专家、编写传记、开课传授,萧红研究贯穿了季红真漫长的学术生涯。萧红对于季红真而言绝不仅限于学术上的研究对象,而更像是她的一位素未谋面却早已融入生命的挚友。
2008年,季红真第一次来到小城呼兰,这是陪伴萧红一整个童年的故乡,也是萧红日后在无数个暗夜里心系的灯塔:
清晨的凛冽寒气激励着身心,积雪铺缀成斑驳的街景。行人微弯着身体低头缓行,色彩鲜艳的服装在冷色的背景中晃动成一片印象派的画面。……雪野中的风景是单调的,村落好像埋在积雪中,树木也颤抖成灰黑色的暗影,零星的行人像散落的点。未久,车就开过了宽阔的呼兰河大桥。(季红真《萧红故里》)
季红真所感受到的这份“印象派”般的清冷,让人自然地想到《呼兰河传》的开头,小城昨日严冬的冷仿佛到今日也未曾改变: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萧红《呼兰河传》)
其实读这一类寻访旧迹的散文,不难于感知山河之“常”,难的是触摸世事之“变”。时过境迁后到访呼兰,季红真对“风景”的发现与探索可见她的心迹:“崭新的萧红故居坐落在呼兰城的东南隅”,“喧闹的市声覆盖了大泥坑,也覆盖了萧红古旧悲凉的记忆”;曾经香火旺盛的龙王庙,现在“只剩下一座结构谨严而破旧的大门”;在哈尔滨,萧红、萧军同住的商市街25号有着诸多故事,如今已变成“一座不矮的楼房”,“当年冰冷狭小的耳房地面上,安放着高压电箱”……似乎曾经的诗性正在渐渐流失,萧红驻留处在今天“更像是情节简单但细节丰富的现代派小说”。然而,季红真又另辟蹊径地从浮光骤变里再获世变缘常:虽然修缮后故居以整齐的花木代替了旧园中半野生的瓜果花菜,“后花园也许不再种植小黄瓜、大倭瓜,蝴蝶、蚂蚱和蜻蜓却会‘年年仍旧’,黎明的露珠会落在整齐的花树上,黄昏时的晚霞也会继续变化出各种形状的动物”……读罢这份在常与变之中的迷津往返,季红真对萧红精神世界的涉渡之深清晰可见。
如此心迹玲珑,可称“解人”。面对萧红一生的种种谜团,季红真多年也的确在做“解人”,她曾分别对萧红的家族背景、身世来历、文化信仰、知识谱系、修辞手法等诸方面详加论述,又从萧红与鲁迅关系、萧红与张爱玲对比、萧红作品的传播史及经典化等角度起笔,还原这个有“盖世之才华”(柳亚子语)女作家的点点滴滴。谈及为何选择萧红用力毕生,季红真认为学术研究的选择有时是非理性的。不过,非理性的心智认同总和理性的逻辑必然紧密相连。和同代人类似,季红真青年时代的“关键之书”也是《鲁迅全集》,在鲁迅对《生死场》作的序中,“力透纸背”四个字令季红真印象深刻。上大学后,季红真借阅《生死场》,想知道萧红如何得称“力透纸背”的评价。从此开始,她渐渐地明白了萧红为什么把人生苦难写得如此淋漓尽致。
这种“逻辑必然”还与地域性有关,季红真曾就读于吉林大学中文系,视吉林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据友人赵园回忆,同在北大读研时,季红真对朋友言必称吉大,可见认同深切。中年后获聘沈阳师大教授,又与东北结下不解之缘。季红真长期读萧红、写萧红,也跟长期在东北生活的体验不无关系。回溯动荡时期的东北社会状况显得艰难,当时的东北政治势力庞杂,传统族系与外来移民的复杂关系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声场。萧红写的是东北,娓娓道来的风物抒情之外,也有掷地有声。她的书写是贯通现实的,并非孤立地写某一事件,而是将重大历史事件放在现代性兴起之后的东北近代史脉络中,一方面以大量的器物细节作为历史的标记,另一方面调动历史意识,艺术地还原20世纪上半叶的东北往事。萧红的左翼思想萌根于混乱的地缘政治,但未被政党意识形态的外在观念所干扰,她以“天籁之音”呈现出对现实的超越。在《萧红大传》中,季红真便着力于萧红植根历史的超越性方式,在尽可能真实的历史还原中,重点讲述她如何用审美经验反抗现代困境,以及个体生命如何在与时代政治的错动中,回应制度与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
历史撕裂了文化的缝隙,但文化史永远比观念史或政治史对人的制约更强劲。与其说萧红一生的地点转移与文学变化是主动为之,不如说是一种求生的挣扎。若想理解她的奔逃、无奈与奋斗,必须用非道德主义的眼光注视真正的历史语境。基于此,《萧红大传》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书写了萧红的“史前史”,以破除她早期婚恋和家族历史的神秘性。通过对照曹革成等人的叙述,汪恩甲家族与萧红家族的关系得以明晰。乡绅家庭的成长环境与特殊婚约的约束,让萧红在家庭破裂中天然地易于接受新文化,尤其是左翼文化。季红真指出,萧红的《生死场》选择以崩坏的乡土作为生命故事的原点,表现了从失败变革到奋起抗争的完整过程,为断裂的历史留下了最初的遗照。“萧红因此而成为民族历史的书写者,她的创作和其他作家的创作一起,成为全民抗战的先声,带有民族集体记忆的特殊意义。”
传记文学在中国文学史的谱系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古典时代正史叙述的名篇佳作常被当成虚构文本解读,一些脍炙人口的名作往往并非毋庸置疑。季红真多年来的萧红传记创作,是在近代学术细分后的文学选择,虽非学术意义上的史论,但仍具备严肃的史识。在处理萧红人生中广受关注的婚恋关系时,季红真没有迎合大众趣味,不利用性别制造“看点”,以端正的态度解读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之间的情感关系,综合各方史料,不只采信一家之言。的确,那些充满噱头的传记叙事又怎能写出萧红命运中的悲剧感?她那广袤的悲哀与苍凉,是不容半点戏谑揣测的。而这种严肃的背负,大概也独属于萧红的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