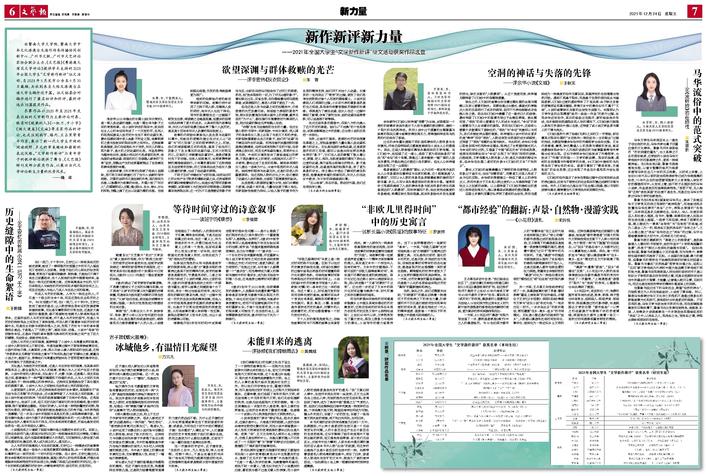“非欧几里得时间”本质上是一种对时间的碎片化处置。区别于以往对历史寓言的线性处理,《民谣》在撰史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时间错置和碎片化处理的色彩。非线性叙事时间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的同构书写上。小说《民谣》中的历史寓言书写是个人史—家族(村镇)史—革命史三位一体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开放的空间而非单向度的直线,叙事时间由多个言说主体承担,阐释空间朝着各个方向展开。莫庄、陶庄、小镇、县城都是作者讲述历史的基点,村镇中的人成就着历史,历史也塑造着每一个时代变迁中的人。
于个人史的微观角度观之,非线性叙事时间与不可靠的叙事主体紧密相关。第一人称作为一种具有极高限制性的叙述视角,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承担着相当程度的“风险”。将故事的唯一权威话语声音设置为一个精神方面有障碍的病人,其实是文本中一个相当叫人玩味的细节。文本中的交错混杂、不断闪回的“非欧几里得叙事时间”,其实是不可靠的叙述者的疾病投射。碎片化记忆在这部小说中以病症面目出现,用以讲述整个“文革”时期的“不正常”。这也进一步佐证了文本中的碎片化时间设置与患病个体、时代环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绾系。
而当作家借由非线性的时间通道来触摸乡土中国及其背后隐没的历史寓言时,这种反传统的时间形态本身为志史和历史反思又有什么独特创益呢?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再加上想象力与结构力的弱化,小说写作的潜力逐渐丧失。当下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新的“革命”。一方面,“非欧几里得”式时间结构是小说“打破循环”主题表达的重要工具。无论是相对封闭、固化的乡村历史,还是开放、未完成的当代现实,非线性叙事时间带来的动态化叙述,都是呈现历史含混模糊一面的更优选择。颠倒错乱的时序中更放大了乡土世界的模棱两可和庞杂浑浊。另一方面,对历史寓言的重组和编码,实则是借个人化的私密经验实现对历史“真相”的重新建构和表达。
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关注到,“打破循环”的理念召唤着一种潜沉于历史地表之下的有生力量,打破循环并不仅仅是打破封闭空间和单向度的时间本身,更是在完成对一代人的精神拯救:拯救每一个被囚于环状锁链之中倍感无助困惑的人。
(本文获本科生组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