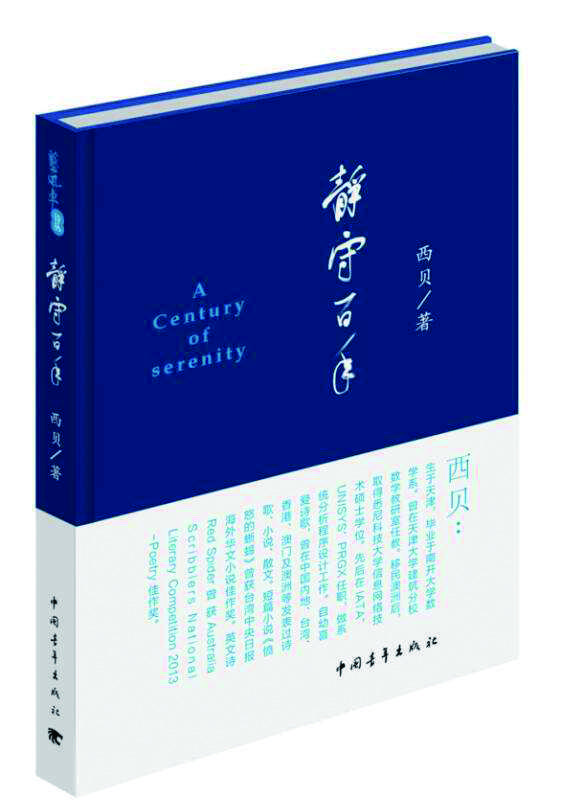在历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获奖作品中,诗歌总是少数的,而澳大利亚华人作家也总是缺席的。直到第五届“中山文学奖”揭晓,西贝和她的诗集《静守百年》赫然出现在获奖名单中,我们又被澳华文学唤醒。想起黄万华先生在1990年代末期的一段话:“澳华文学的可贵就在于它没有太多地重复思乡寻根的传统信仰,也没有简单地呈现中西文化撞击、交汇的形态。它一方面用自己的青春节拍共鸣于澳洲文化的质朴博大,另一方面也用对未知、陌生领域的探索拓展着海外华文文学的开放性。也许,21世纪华文文学的开放意义正孕成于澳华文学那样的努力中。”西贝和她的诗歌创作,正是延续早期澳华新移民作家表述自我的方式,在远行和“静守”中默默留下他们与时代、与家乡、与中国的互动和关联,不“重复”,也不“简单”。
若以时间为脉,在抒情中寻找诗歌的叙事线索,《静守百年》是从青春絮语到中年沉思的个体言说。和许多新移民作家一样,西贝进行文学创作源于非职业性热爱,她是1991年移居澳大利亚,在获得悉尼科技大学网络技术硕士学位后,从事IT工作。因此,《静守百年》中收入的20世纪80年代写的诗歌,如《无花果熟了》(1984)、《红蜻蜓》(1985)、《蜗牛》(1985)、《河边的垂柳》(1986)、《梨树坡》(1986)、《枫叶》(1987)、《石榴的秘密》(1989)、《早春的雪》(1990)等,都只能算作新移民写作的前史。但在这些诗歌中,我们看到西贝和那个时代、和自我对话的方式——在日常景象中发掘诗意的可延展性,幻想或玄想都与特定的情感经验相关。那时的西贝从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就成为国内一所高校的数学老师,在“数学”之外,她也用时代特有的朦胧风,表达属于青年女性的情愫、忧郁、慨叹或思索。比如《无花果熟了》,在窗前等候妈妈的少女,安静地望着无花果的形与色,不写母亲,却让人感受到她对母亲的情深,属于舒婷式的婉约优雅;而《红蜻蜓》《石榴的秘密》等诗歌中则是说“梦”话的青春色调;在《蜗牛》中,她看到的是蜗牛没走完窄窄的边道,却被人们匆忙的脚步踏碎躯体;《夏枯草》通过身体写感觉,“在火热的骄阳下/她的心枯黄”“在光天化日下/她体无完肤”;《红蜻蜓》是带给“我”彩色梦境的蜻蜓,在“我”醒来后死去,“小小的红色尸体/像一把冰凉的剪刀/划过夏天最后的花草”,敏于人或物,生或死,即便微小如蜗牛、夏日枯草、蜻蜓。及至1990年代之后,西贝的诗歌,渐渐褪去早期单纯朦胧的气息,从情绪化到化情绪为沉思,简单纯净的诗风也转向沉郁凝重。
重要的意象,如同潜意识之梦,是走进诗人内心的符码。后青春语境中,西贝多用空间意象、“黑暗的丰腴”、幽灵、风暴等表达对存在和人生境遇的思考。比如《宁静的花园》中“蜜蜂正在挣扎/被蚂蚁团团围困”;《绿灯笼》是非写实的虚幻意象,在山崖上,绿灯笼与古藤老树同栖,山野孤寂,毁灭和再生与共:“你飞快地奔驰/驶向悬崖巨壑/飞越了理想主义的深渊”;《红蜘蛛》写一只透明的红蜘蛛被困在水晶瓶里,让“你”想起更多类似的人生“那透明的红魂/带着某种宿命的痛苦/固执留守水晶的坟墓”;《有毒的野莓》中“你”在夏天的早晨迷路;《沉醉的柠檬树》中“她的密叶和膨胀的果/在天堂的风里颤抖/她无力拒绝 也无处逃避”;《镜子》里的“你”似乎独坐宴席散去的空落花园,“你从一个深渊/走到另一个深渊”;《行人》中的狭长街道和人影也都是暗淡的,而行走和观看似乎都是虚无:“走向面孔/走向阴影下移动的花朵/走向夏天靡靡的气息/或者 走向笔直的空旷”。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迁移带来的挣扎和困顿,让抒情主体时时感受到幻灭与无力;或许,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女性真正于社会中成长的某些境遇,让作为“她”的个体处处留意人生的孤独与悖论。
这种精神隐痛与《悬浮液》中所写的“游离的孤独”,大概到了2005年之后,才真正换了一种色调与心境,太阳、阳光、黎明、飞鸟、羽毛、溪水、春天、未来这类明亮的意象开始频繁出现,诗歌中的情绪不再低沉压抑,轻盈、温暖、超然于事和物的怡然与从容渐渐多了,诗人似乎获得了新生。比如在《陶醉》中,黄昏和音乐是和谐的,棕榈树滑落的温情可以压痛泥土,“玻璃暖房/几近完美”“饮尽最后一杯酒/陶醉 归去”。即便玄想也是如《脚印上的舞蹈》中那般走进神仙居住的山,而《沉重的往事》中心境也不再沉重,因为岁月已老,往事正在淡漠。但经年累积的平静和冷静,并不影响寻梦者每一次嘹亮的歌唱,以及穿透世事的睿智:《流放》中“你用血液燃烧/追逐风里的神话”,当唯一的真情变成谎言,“没有悲哀 也没有悔恨/只有莫名的衰老”,变化也正与不变相对,“你”在太平洋南端的绿岛遥想余生,半世情人已死,北半球来的是最后一封家书,而这一切情愁都消融于寂静的原始森森,“只有企鹅一年一度/从南极游来”。这种安之若素的豁然,不禁让人遥想南半球的春夏秋冬与生命轮回,是以怎样的方式淘洗漂泊者的情感结构与文化心理。
所以,还是以空间为界,重新梳理西贝的诗歌。我们看到意象跳跃处,是女性跨域经验的沉淀,越界与守望的张力正形成独特的诗语之魅,纯净、孤绝又带着隐隐的痛。那些睡在诗句里的秘密,透过地方、景象与情绪,以空间的方式,汇聚出移民者从离别故土,到落地生根之后的情感轨迹。但西贝不像典型的移民者那样表达思乡寻根,不是情深意浓到化不开、理还乱,而是如同黄万华所说的不太重复传统,但又不是不思念。家或母体以另外一种形态,成为永恒的背景和存在。比如《无根的植物》,诗人将自己的乡愁藏得极深,只是写植物的形态和状态,浓绿的青苔无根,伞菌木无根,水草亦无根,由水草-海面-海妖-水手,想到美人鱼“在海底不停地弹着琴/歌里歌外 漂泊的游魂/唱着叶落归根——”以物言己,借想象中的美人鱼委婉表达移民者的心境。但其实,这首诗已经是极具标签性的思乡之作。《静守百年》收录的诗歌依据主题或诗感进行分辑,刻意打散时间导向,以“静寂”“身世”“风景”“草木”和“古词新韵”分为5辑,直到白话诗最后一辑“草木”的最后一首诗《告别》(1992),我们才恍然,告别不只是和原有的梦分离,从“梦的白色陵园”“走进青蓝的海”,是人生的蜕变,以此再向前看,家乡的梨树、枇杷树、柳树都只是更开阔人生的背景。而前景,是移民者迁移之后的空间场景。大海自然是首位镜像,照出异域生活百态,而行走的空间如《寂静的贝诺克尔街》中犹太人的教堂、维沃利公园,《卡西格里》的山庄、石头人,《伊利瓦拉的夜》的街道,《盆地》中的布莱阿里克塞,《阿拉伯的挪威》中马斯喀特的香料、波斯湾的战事,《罗斯维尔的露天停车场》的停车场……日常经验与身之所至的地方密切关联,这些地方不是因为原本有名称而有了身世的延展,而是因为被诗人感受、凝视成为一个个有意义的空间。加斯东·巴什拉说:“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是凭借空间,是在空间之中,我们才找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而凝结下来的绵延所形成的美丽化石”(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第9页)。我想西贝并未刻意去为空间赋型,但因迁移造成的地方变换和时空切换,无形中成为移民作家空间敏感的质素。像《海边的孩子》这样的诗,是为三岁男孩在难民船翻覆溺亡而进行的悲悼,但“难民”何以就牵动了诗人的心?不只是对生命的爱怜或母性悲悯,应该还有迁移经验引发的共同感,因而个体生命的陨落,在诗歌情绪中是亿万颗心之痛,是人类共有之悲伤。
但其实,西贝并不介意时间或空间如何交错,诗歌是她在现实和想象中的“远行”与修行,与白话或古词的形式无关,日常琐细里的汉语诗意,是关于生命、生活、人生甚或人类的至深至情、哲理辩证,亦是跨界写作者以独语穿越“流浪”和“囚笼”守望文学理想的表征。从1980年代驶出的诗行,延至21世纪的当下,是个体记忆与行走的轨迹: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北方街道,到漂洋过海之后“悬浮”游离母体之后的异国“孤独”,再到当下作为后移民的情感体验与灵魂之探。情绪闪动的年代感与情感变化所折射的空间经验,又折射了新移民群体跨区域位移之后的人生境遇。如果一定要给《静守百年》刻绘抒情主体的形象,那应该就是诗歌《白杨林》形塑的白杨树,在苍然静寂的森林,阅尽一切,承受真相,沉默与黑暗都只是纵深处的瞬间,“诉说和请求的能力/转化为他们站立的方式”,以站立和静默之深邃守护的不只是自我,表达的姿态和路径或许更重要,正如用汉语写诗,用古体写词。但并不是说西贝的诗歌就是完美的或者纯熟的,她只是用她的方式,在非汉语文化语境中“守望”自我——向内是以诗歌唤醒灵魂之痛,疼痛撕扯之后回归个体心灵之宁;向外是以静守抵抗喧哗与中心的干扰,在自己的园地用母语表述最纯粹的自我。也正因为西贝这样的远行者在边缘处“守望”,汉语从原乡出走,再回到诗与原乡,我们看到汉语诗歌实践与流播的诸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