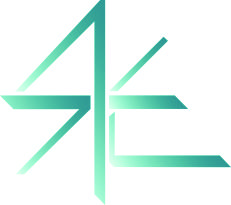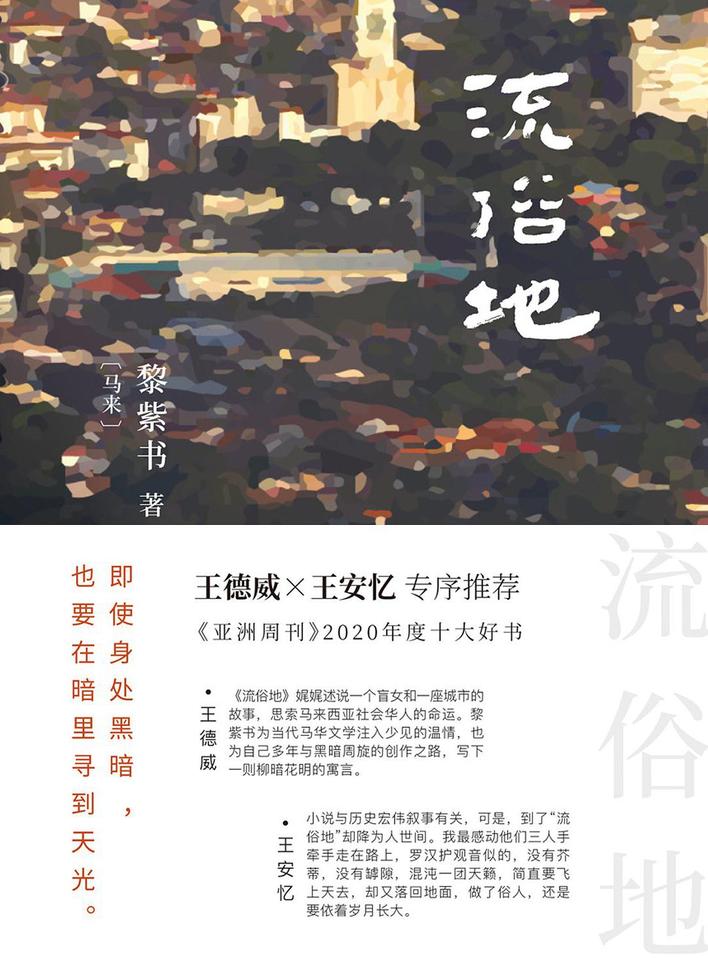戴瑶琴(主持人):《流俗地》是黎紫书回归现实主义的创作转型,“在地”书写保持“人—家庭—社会”的圈层架构,但其写作落点已由专注私人体验转向关怀社会生态。“流俗地”真实含义是锡都(抽象)和组屋(具象)的组合,黎紫书以记录家乡怡保的多族群人生为创作原点。“组屋”时代的社群生活不复存在,那么新变是真的新生还是再次陷入旧轨,小说没有给出答案,可能这正是凡俗的真实生态,谁也不能决断未来,只能期待未来。
“和光”读书会从锡都、耳蜗、猫、儿童、信仰、教育、记忆等视角,打开细读《流俗地》的多种路径。
@张晖敏:锡都
二十层的近打组屋是锡都城的缩影。燥热逼仄的空间里,人们匆忙地在这里度过一些不得志的时光,顷刻又一哄而散。有机质与无机质的噪音日夜喧嚣,昭示着组屋这架东拼西凑的大机器仍然在运行。尽管日子琐碎平实地向前推进,寄居忧虑却时刻盘桓。
多族群的嘈杂混响时刻混淆身处的位置。激烈冲突不复存在,危机却慵懒地伸开触角。组屋生活的成型与解体正呼应着锡都的不确定性。水泥土木构建的空间未必稳固,人与人间的联结格外脆弱。在永恒变动之下,任何庇护所都变得不可靠起来。对安稳的向往和对新变的拒斥,悄然改动人们行进的轨迹。
细辉代表着小城里平凡华人子弟的一员,银霞则把这一复杂回环的状态推向新层次。残缺身体和过分聪慧构成谶语:智慧的神/受苦的人。一半的银霞潜藏在黑夜里,穿行于镜面和幻梦之间,因其视障而获得格外的洞察力;另一半则作为再脆弱不过的生命,体验着马来华人,特别是华人女性所可能面临的一切灾厄。
智识构成向外走的蓬勃野心,银霞拒绝做技艺谋生的盲人,这与其母亲的愿景背道而驰。面目模糊的施暴者注定没有名字,因为挫败银霞这个“迦尼萨”的施事者,几乎是整个锡都,是发酵的欲望、异族间的疏离、限于文化与信仰的怯懦。
莲珠跻身上流、马票嫂安稳终老、蕙兰折服于盲目爱恋、浪子大辉改头换面隐身寺庙。走出去的人们周身棱角,驻留原地的少女们亦有许多化为冤魂。没有哪种人生通向绝对安全,也没有哪种人生应该被过分苛责或歌颂。
保守又大胆、坚韧又柔弱,时而进取、时而退缩。银霞身上凝聚当地无数华人的影子。突然降临的顾老师不仅给了她相对圆满的结局,更为整个危机抹上一笔温情。成婚那日,不再年轻的银霞坠入迷梦。未来日子还是一个未知数,不安的消弭需要更多时间,又或许这如履薄冰的警惕性还将与人们长久相持下去。但不论怎样,新的希望将永远覆盖着旧的创伤。
@于明玉:耳蜗
全知全能叙述者跳落在银霞身上的那一刻,就像被钳制进了一个广袤无限的黑暗牢笼。声音裹挟着怡保华人文化生态的诸多现实,从视觉意象生长,再借由耳的官能重返人物本身。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淡米尔语、汉语铺展开锡都多民族共生的复杂景象。民间情境充盈声响:坝罗庙宇旁的法器推拉式地震荡,《大悲咒》混杂“唯有真主”的诵经声浪……都肆意游走在质感细密的听觉空间之中。
当视界化为空茫,音景便交替登场。有所寓指的自然音与人为音此消彼长,为主体瞬时的情绪波动和外在氛围的延绵提供释义,而读者也在高度拟真的共鸣关系中,不自觉地替虚构人事实现了自洽。文中遍布生活的泥点——藤条划破空气的“咻咻”声、点字机发出的“咔哒咔哒”声、脖子转动时的“嘎嘞嘎嘞”声。与此对照,“无声”作为第四种声音景观,凭借过载信息量在刹那间搭建起意志擂台。于是,我们看到了孱弱的细辉以嘶吼为拳打向“一街融化中的蜡像”,丧母的银霞为囿于岑寂的自己捏起象头神的手印,光阴的无言中羁滞“暴风雨来临的前夕”。正是在意义的渐次衰微中,银霞对镇流器鼓噪是光明信号的解读,才得以焕发出童话神采。
银霞坐在“德士”电台办公室,握住了整本书千万条线索的枢纽。世界汇入盲女的耳蜗,又从唇舌滑出,向怡保的每一角落辐射开来。出没于主角灵魂周遭的每一个故事,屡屡在她接起大辉电话的那一刻闪回情节主线,进而按照程式完成一系列的怀疑、推论与判断。楼上楼里“内部传闻”的实情与真相、“人与人之间幽微的关系”,其吟哦隐蔽,却逃不开有限感知的镜照和捕捉。“可见”的退位,迎来全新的“可闻”秩序。
但需要注意的是,听觉敏锐的前景是视感的畸变。世界喧哗不堪,只剩一个沉默的银霞在永夜中踽踽独行。在其身份由孩童迈向女性的过程中,无法分辨的音响易位为恐惧的发端:“铁三角”关系早已埋下分离隐患,在功利性的结亲盘算中不断磨损,又随着拉祖死讯而彻底溃散;印度姐妹花对母亲杀死幼猫的欢快描述,与手术台上小金属器件的清脆撞击隔着渺远的时空邂逅,锐化为一声摧心剖肝的哀鸣。
在善恶交错的锡都,读者再难以绝对享受的姿态去看待这本杂响“盛飨”。每当驳杂声源与偏狭信息泥浆般涌入耳中,前尘往事惊鸟般同时炸响,银霞只能拖拽着她的耳蜗,从那些转瞬即逝又潦草褴褛的讯息过滤出生活的“纯音”。肉眼可见的世界被奇绝诡异的集体意识取代,银霞是唯一的钥匙。伴随着一声“喵呜”,注定只有她将在昼与夜的夹缝中直奔真相。
@王玥枭:猫
怡保流传着“自来狗富,自来猫贫”的说法,甚至延伸出“马来人养猫,华人养狗”的民族立场。小说中的猫被赋予了“人”的色彩,既是隐藏在故事内的灵动线索,也结构出“流俗”真意。
猫贯穿“楼上楼”与“美丽园”两处空间,连接起银霞的幼年和成年。寄居在“楼上楼”的印度姐妹花曾给银霞讲过猫的传说,它既神奇又脆弱。“猫的两重性呼应着银霞的残疾和倔强,也隐喻共同主宰猫与人的无情命运。银霞在姐妹一家搬走后前去调查,猫却无影无踪,如同在时光中消隐的众人。
真正的猫在“美丽园”中才现身,成为开启新叙事的契机。它只在夜晚出现,银霞用淡米尔语取名“普乃”。顾老师唤其为“疤面”。不同命名寄寓着二人各自心绪。“普乃”一词让银霞想起印度姐妹、莲珠姑姑,借由这些联想,“普乃”成了无法忘却的记忆化身。而猫的柔弱也成为银霞和众多底层女性困境的象征。“疤面”出自电影《疤面煞星》。这个独特的命名既是顾老师对昔日友情的追忆,又是他对失败婚姻的释然。“一只猫吃两家茶礼”,“普乃”或“疤面”拼接黑暗和光明,牵动两人间的红线,以物象带动小说叙事。它曾失踪又归来,复现大辉的出走与回归。“猫”的变幻无定,人事的因缘际会失去了巧合的刻意,让原本的“传奇”重新落回“世俗”。
但归来的可真是“普乃”?小说结尾恰是一处虚写,既可理解为结构的回返,也可视作是未知未来的开启。流浪猫有两副面孔。“普乃”看准了银霞的失明,在黑夜中展露出它本真的阴森。但白天“它就以为自己是另一只猫了”,慵懒而顺良。其间的差异正是小说运作的辩证法:世界的黑暗与光明、生命的美丽与残缺都聚焦至个体。“流俗”的深意也汇集于此。
@孙艳群:儿童
从最初在胶林都市游走的亡女(《蛆魇》)、肖瑾(《某个平常的四月天》)、小爱(《推开阁楼之窗》)、旅人(《无雨的乡镇》)等,再到最近身处锡都“楼上楼”的银霞(《流俗地》),黎紫书在构建人类生存困境的文学图景中,常借助儿童的感性经验去呈现和图解外在社会世相。
处于成长初阶段的儿童由于理性认知的匮乏,其对成人世界的感知多源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的官能作用,因而儿童叙述则具有主观化和碎片化痕迹。男孩“我”在幽闭中细嗅异变酸味(《浮荒》),小爱(《推开阁楼之窗》)痛失爱人后的世界被搅成一团斑斓颜色,俗世音流中的秘密穿透视觉死角,钻进了盲女银霞的耳道。儿童的魔幻想象与体验使其情感触角延及蚕食的白日、混沌的黑夜与浓稠的梦境,最终令有气味、有色彩和有温度的感性世界显形。
但是,儿童的情感世界却包裹着成人欲望,成人间背弃或虚伪的原始狼性在潮湿气流的催动中发酵变质。晓雅忍受父母的重男轻女(《流年》),蕙被父亲抛弃(《把她写进小说里》),而银霞在暗沉午后惨遭侵害。儿童只能蜷缩在阴冷逼仄的阁楼老屋,或在一摞摞尼龙网兜勾连的“盘丝洞”中孤寂沉默,掐断与社会空间的联络,终结与自我心灵的对话,那些用以表露心迹和沟通对话的日记书信被淋湿发胀,卷起波皱至无法辨认,从这一刻开始,儿童逐渐失语、自闭、直至病态。
成人的“不合格”在给予儿童创伤之余又扮演着“启蒙”角色,儿童则在病态中被剥离纯真本性,他们开始凝视、模仿、追随成人世界。卢雅乖张(《卢雅的意志世界》),亡女弑父(《蛆魇》),小爱(《推开阁楼之窗》)将婴孩溺死在马桶浊黄的污水里,充斥着色欲、暴力和罪恶的行径野性勃勃。儿童与成人之间身份逻辑逐渐松散,其情感世界里纯洁与野蛮的界限暧昧不清。
儿童陷入成人世界的泥潭,挣扎着,同化着,最终消失,隐隐与成人合成一个影子。亦或许,黎紫书不愿儿童在苦海自沉太久,在清一色的病态儿童里,银霞并未与之殊途同归,她被迦尼萨眷顾。在她身上,黎紫书再现了生存残酷,又倾注了无限柔情。
@刘艳:信仰
《流俗地》描摹的俗常人间,指向怡保马华人松散的“民间信仰”圈层。在华人人口占比极高的城市怡保,神明信仰及祖先崇拜如同编织的环形网,将马来华人与中国在精神层面系联,也网罗生活在近打组屋的人,让每一次“出走”和“新变”都处于博弈当中。
《辞海》解析“民间信仰是民间流行的对某种精神观念、某种有形物体信奉敬仰的心理和行为”。石窟寺、南天洞、三宝洞、观音洞;玉皇大帝、吕祖先师、财帛星君;栉比鳞次的神像有形实体,凝聚成怡保的中华文化飞地,与中国各地香火兴旺的佛道寺庙并无二致。问觋于九天玄女庙,白米细香即可经“问米婆”沟通阴阳;大伯公坝罗古庙、九皇爷斗母宫祈福求财,每年各需走一遭;组屋华人各家神台供奉白观音和祖先牌位,将神明信仰与祖先崇拜汇聚于民间信仰的共同体。
民众是民间信仰的主力军,“有灵必求”“有应必酬”是民间信仰的普遍心态。不过,近打组屋的华人家庭并无“主祭神”,神灵系统庞杂而任意,神话形象、功臣圣贤、社会名流、显赫祖先,各种具有不同功能的“神”各司其职,都是民间信仰圈的一部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马华社会。
然而,细辉父亲死状惨烈;拉祖进城念书却英年早逝;莲珠姑姑搬离组屋成为“拿督夫人”后婚姻不幸;银霞一家察觉“美丽园的人们却都寡言,碰面了连目光也不打招呼”。楼上楼的居民们抱着寄居心态,不断出走,离开压缩着满天神佛的组屋,如同浅水鱼一般,试图游入广阔的深海,却因缺氧而溺毙“水”中。看似“人生路上走到了宽敞地,再不需要与同病相怜者相濡以沫”,实又踏入另一个困境。《流俗地》所反映的民间信仰之枷锁,最终落入了“分裂——坠落——治愈”的叙事圈套。
@赵佳杰:教育
怡保华文小学六年的中文教育培养了黎紫书的阅读习惯与写作爱好。她的中学阶段是在每周仅有几节中文课的马来西亚国立中学就读,但这没有影响她对华文创作的热爱。
银霞所在的盲人学校就是华文教育的成果。马来西亚在1819年建立第一间华文学校“五福书院”,同时民间也自发借助庙宇和宗祠建立私塾。怡保市华人私塾拥有百年历史,霹雳福建公会于1917年设立私塾,8年后以此为根基创立培南华小。地方侨领推动开办华校,学校以中国“四书五经”等为教材,没有设立专职教师,只聘请当地华人中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教学。小说中的这所盲校距离福德祠不远,也在密山华小附近。
怡保第一所华校是设立于1907年的育才学校。华人生活稳定后在当地办校,目的是让子孙后代传承中华文化,日后能够与中国亲人再度联系。华人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华校被设立。据马来西亚《星报》2020年11月11日报道,与过去十年相比,更多马来西亚人选择到当地华文学校就读。《流俗地》揭示了与华校相比,国民学校存在教育效果不显著、学校管理层薄弱等问题,因此除了华裔家长,其他民族家长也把孩子送至华校,华文学校呈现更宽广的包容性。拉祖虽是印度裔,但在坝罗华小多次获得全年级第一和各种奖牌,而他在马来学校的哥哥姐姐却很平常。父母欣喜拉能用华文流利与他人交谈,他更因在教育文凭考试中华文成绩为A而被学校和媒体宣传,风头盖过真正的会考状元。
“马华新生代”代表作家黄锦树提及“华文教育是马华文学存在的必要条件”。华文教育的推广、发展与兴衰直接影响了马华文学的未来。
@韩贵东:记忆
莱昂纳德·科恩说:“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流俗地》正是以这样一种光影斑驳的书写再现了“楼上楼”喜怒哀乐的往事。行至生活角落,总会有人在古铜色的黑夜中,突然打翻了手中的聚光灯,以至于剥开那层满是泥土的皮囊,露出尘埃落地的喧嚣与隐秘,这是属于《流俗地》的纯粹。那些伴随着黎紫书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事也在明灭不定的流年中镌刻成永恒的锡都记忆。
《流俗地》似乎更像一本族群记忆之书,里面密匝写满了生与死、罪与罚、黑与白的俗地与俗人之事,而人物都逐渐在时间碎片中随风尘而去。我们的确看到了那些为生活而颠沛流离的小人物,连同那些被时光打捞起的边缘琐事,而这一切都在触碰黑暗中诠释了人性深处的光辉与救赎。银霞、大辉、婵娟都在生死别离的日常中,淡然面对生活的凋零。蕙兰在房门口“脚下踩着房里挤出来的微薄亮光,大半个身子泡在暗中”,转瞬间,生活便遁入了无尽暗夜。
《流俗地》不单是文学性的书写表达,更是将生命交给思绪跃迁中的普适性价值探讨与俗世之魅的哲学忧思。飞到天上,又落回大地,其严丝合缝的情绪回环将“楼上楼”故事娓娓道来,流贯其中的是媚俗、遗忘、伦理、偶然与必然等的共情。诚然,我们也无须刻意寻求生活的意义,而是要像书中人一样去体悟生活的本然状态,也便是过好这生活。
那些侵入骨子里的冷漠与倨傲,都在生命不羁的年轮中褪色。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借主人公托马斯之口阐明:历史和个人的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太空,明天不复。《流俗地》写尽了狼奔豕突、离乱凉薄之状,却规避了洪钟大吕的史诗叙事,只是在锡都看得见的生命中规划我们都未能预见的前程与归宿。黎紫书用俗地之人的身影形貌钩织了黑暗之网,可这里面藏匿了光亮的未知。黎紫书在《流俗地》中为我们书写的恰是看待生活的方式与读解自我的意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