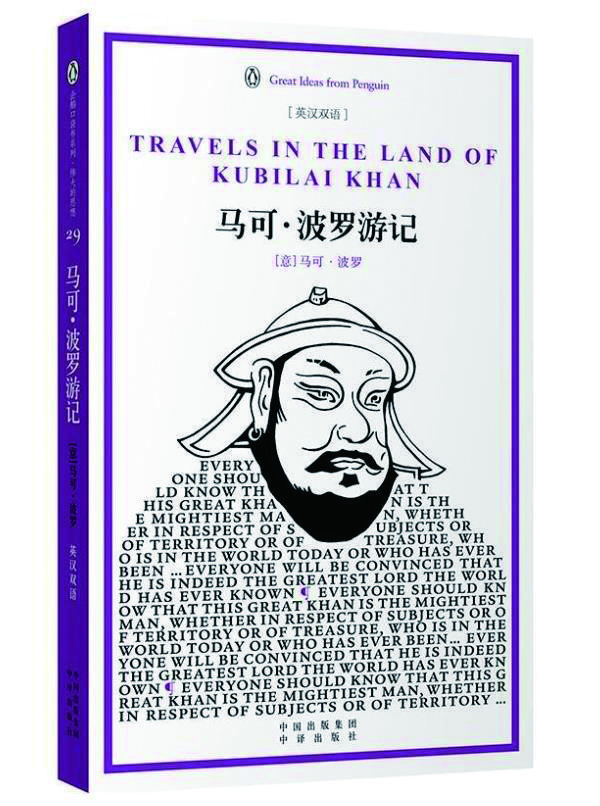完成于13世纪末,行世于14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是西方人著述的关于东方中国最早一部内容最翔实、影响最深远的图书。由于它的成书过程是一种口述的记录,记录者又是当时的通俗文学作家,免不了按时风给记述穿靴戴帽,使之像是一个俗文学文本。这使得它一经问世就风靡一时。那时的西方对东方的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或者略有耳闻却不得其详。成吉思汗和他的铁骑正横扫欧亚大陆,西方人也在恐怖中茫然无措。马可·波罗的中国“传奇”吸引了西方读者,让他们意欲了解神秘的东方。
马可·波罗在世的时候,人们就曾经直接质疑过他的中国讲述的真实性,他回答这些质疑说“我还没有把我所见的事说出一半呢”。多少年后,蒙古铁骑的血腥散出,马可·波罗的中国盛景(黄金香料和奇风异俗)却在西方人头脑中久久挥之不去,越来越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它甚至成为随后而来的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航海时代到来的导火索或者说是触发器。在航海热潮兴起之际,游记几乎影响了所有重要的航海人。葡萄牙亲王航海家亨利是15世纪西欧航海探险和地理发现事业的奠基者、组织者和发动者。他就有一本《马可·波罗游记》的手抄本并经常翻阅。欧洲中世纪第一个地球仪制作者马丁·贝海姆也热心倡导从西方航向东方,他自述自己的地球仪地图受到马可·波罗的影响。15世纪末佛罗伦萨著名的地理学家托斯卡内利也是西渡大西洋去东方的积极倡导者,他也看过游记,赞赏马可·波罗的说法,认为亚洲大陆比托勒密设想的更加向东延伸,即欧洲西向与亚洲东方比过去已知的更近。哥伦布曾带着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开启了他的创世纪的航程。所以,这部游记在后来的元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地理学史研究等方面成为其中的显学。由于民俗学兴起于18世纪,人类学成型于17世纪,所以,早于它们两三个世纪的“游记”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在民俗学史和人类学史中占有应有的学术史地位。这种学术史的“忽略”应该得到弥补,中国学者尤其应该关注到这一点。
民俗学和人类学是有着学术亲缘关系的两个学科。这两个学科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从民俗学记录或人类学记录(包括旅行家、传教士、记者、作家、商人、外交官、学者等的异地记录)开始,进入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后来,逐渐强调本学科研究者自己的亲历调查与研究,但此间依然不断出现杰出的“摇椅人类学家”,即仅坐着摇椅依靠图书资料和他人调查或记录资料开展研究,著名的有弗雷泽和他的名著《金枝》。在这个意义上,《马可·波罗游记》可以说是一部首次全面系统呈现中国民俗学和人类学资料,且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世界影响的著述。中国的民俗学和中国的人类学有必要给予其学术史定位并对其进行深入的学术开掘。我以为,《马可·波罗游记》在以下几点尤其值得关注:
一、《马可·波罗游记》的民俗学立场
马可·波罗在中国有17年的时间,此前他的父亲和叔叔曾经先行来过中国,然后又带着他一起来到中国。所以他的中国经历、见闻还要加上他父叔对中国的了解。他的游记记录和讲述了许多为西方人闻所未闻的中国风俗。这也是西方一直以来都有人质疑他是否到过中国的一个切入点。比如有人以为游记里没有记录人所共知的经典的中国事象长城、茶叶、汉字、妇女缠足,由是怀疑他的中国之行的真伪。
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实际上以中国之大、风俗之盛,一样不落,恐怕过去做不到,今天也不是易事。事实上恰恰相反,是他的中国民俗记录,证明着他一定亲历过中国。民俗事象的被记录必须基于实地、在场和亲历,没有身在其中民俗甚至是不可记录、不能被记录的。马可·波罗首次记录了中国的纸币及其使用,这是无论如何也杜撰、虚构或想象不出来的。他记录了泰州、南京、行在(杭州)、刺桐(泉州)、高邮等南北十几个城市流行的纸币,而且说出了纸币在中国流通的范围、流通的法律保障、使用的便利性、币值与纯金无别、纸币在流通中的轻便等。这是世界纸币的发生和起源。他记录了中国制陶人存贮陶土的细节,也被西方陶瓷史家认为是西方文献第一次提到陶瓷。他说出这样一个细节:匠人们会存贮陶土达几十年甚至几代人,陶土需要在漫长的时间中风化成熟,他们有时就是为了子孙囤积陶土。这种情况至今还比比皆是。他对卢沟桥狮子的记录毫厘不差,说其雕刻甚精、石狮巨丽,一步一柱、其状皆异。关于中国的桥,他说杭州有石桥12000座、苏州有6000座,把中国水乡的特色界定得非常准确。
二、马可·波罗具有卓越的“讲俗”能力
他到过世界和中国的很多地方。恰恰他接近的忽必烈大汗是一个喜欢听讲各地风俗和奇闻异事的皇帝。正好马可·波罗长于此道。他还为投大汗所好,刻意地训练了自己的风俗观察和绘声绘色讲述能力。所以,他实际上在民俗学诞生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民俗学家”。他在游记中自述自己专意熟习中国风俗且达到精练得不可思议的程度。在众多来自四方或派出四方的使臣面呈大汗时,其他人笨嘴拙舌,被大汗斥为对自己想知道的各地风土人情一无所知,只有马可·波罗的讲俗,深获好评,常常使大汗大喜过望。这使他每次外赴都要专意民俗记忆,每每都要“专事访询”。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俗调查。据统计他提到过的中国地名有70多个。还有外国学者统计比较了9到16世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献中的中国地名,合起来也没有他的游记记得多。
他的中国地理既包括北部元蒙皇室生活地区,也包括中国江南和东南沿海广大地区,还包括西部、西南边陲地区,与元朝中国的疆土广大对应,他的中国呈现也是广大、辽阔、多样的,是具有整体性和丰富性的中国。他记述的中国风俗还有丝绸、占卜、节日、杀羊祭祀、盐税、城市、园林等等,达到了可以说是外国人写的中国“民俗志”样本的程度。大概他还从民间采集和习得了很多“讲古”的材料、技巧、方法,所以,他把民间文学的“文学性”也保留在他的讲述风格里。有时他会直接转述一些民间文学作品,但又像民间传说一样“煞有其事”,这应该也是让人质疑其真伪的一个无意中产生的原因。事实上他也因此对西方文学史中的乔叟、但丁、弥尔顿等文学大家都产生过文学影响。他讲过西方著名的“东方长老约翰”的故事,反倒使这个传说更增添了新的谜团。他讲的“巴格达之移山灵迹”又与我国古代神话愚出移山颇为类似。他讲的波斯三王的传奇,极富民间文学特色,是对波斯民间文学的转叙。这些真真假假混为一谈的“讲俗”,颇有民俗学的价值或者属于民俗学的方法,但却又是引起质疑的重要原因。
三、马可·波罗影响过世界人类学研究
马可·波罗对世界的影响,除了众所周知的大航海一干人等外,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个是利玛窦,一个是拉法格。利玛窦与马可·波罗的关系往往不被人提及。事实上,利氏在晚明时来到中国也是怀揣着《马可·波罗游记》而来。游记中讲到一个宗教事件深刻影响了利玛窦。马可一家三人来华时,从马可·波罗来华路途开始,欧洲基督教会和教皇就对东方极其关心。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还直接为教皇和忽必烈进行沟通,忽必烈盛邀传教士到东方,教皇则通过他们俩将圣杯赠予忽必烈。在《马可·波罗游记》的序说部分,对此有详细叙述。他们一家三人最后这次东行,与其说是为了商人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完成忽必烈对基督教的企盼和教皇对基督教东传的重托。在哥伦布被游记中的东方黄金、财富和商机诱惑时,真正的基督教传教士们也被游记中这些传教传奇所吸引。包括利玛窦在内的许多传教士都曾对这部游记手不释卷。利玛窦对游记中的传教事迹一定是深深铭记在心了,他对教皇期待基督教东传的圣意心领神会,也对忽必烈希望神学、科学家东去,并用西方的神学和科学证明信仰与真理征服东方的豁达开明深有触动。他后来的传教实践似乎就是在践行这样一种传道境界和宗教精神(合儒、补儒、超儒三步曲)。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哥伦布为发现中国而出航,最终只是中途发现美洲大陆;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才是中国的真正发现者,他们发现的最东方的伟大文明和文化,最终完整绘制了世界文明版图。而游记给予利氏的又一个重要启示是他在中国的成功取决于他的“入乡随俗”的方法。这个方法也可以说使他成为现代民俗学的又一先驱。他的方法还被康熙定名为“利玛窦规矩”大加褒扬。这个民俗学史的案例也是颇值得民俗学者研究的。
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是马克思次女劳拉的丈夫,也是19世纪末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学者。他著述颇丰,其《财产及其起源》《思想起源论》都可以列为与人类学有关或者大量利用早期人类学资料的著述。他的“起源”研究中的《母权制——家庭探源》直接对马可·波罗记录的一个人类学现象进行了扩展式研究。这就是“产翁制”。《马可·波罗游记》应该是产翁制(丈夫代替妻子坐月子,以示孩子是父亲所生)原始习俗的最早人类学记录。拉法格引用了马可·波罗在中国云南见到的这个奇异风俗,由此联系到传教士和人类学家在美洲发现和记录的若干产翁制习俗,进一步又往欧洲文献探赜索隐发现了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的类似记录,由此得出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证明:“产翁习俗——就是男人为了取缔妇女的地位和财产而采用的花招之一。”这是原始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历史转折。就像人类学独立发展伊始,摩尔格的人类学调查及其著作《古代社会》促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社会的新认识新判断一样,马可·波罗的产翁制发现对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演进提供了有力的民俗学和人类学材料。
大半个千年纪以来,《马可·波罗游记》先是在阅读界久传不衰,然后又在国际学术界持续引发一波又一波的学术热潮。这是让中国闻名世界且由于它的存在直接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图书。它长久地引起世界关注不足为奇。与之相反,中国的研究和关注起步较晚,且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民俗学和人类学介入其中又尤为不够。这倒是应该引起我们省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