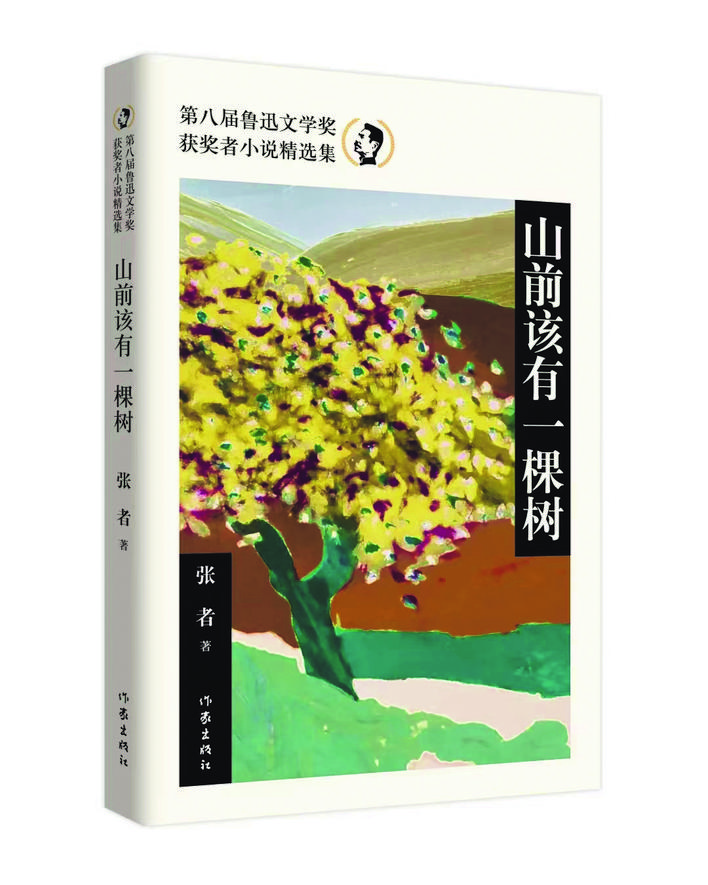教鹤然:张者老师好,首先祝贺您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苦泉水》《沙漠边缘的林带》等作品开始,到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老风口》,再到此次获得鲁奖的《山前该有一棵树》,书写新疆的小说始终是您文学创作的重要序列。作为兵团第二代,您年幼时就随父母在阿拉尔垦区生活,这段青少年生活经验给您的写作和人生带来了什么重要影响?
张 者:我出生在河南,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兵团是养育我的地方。兵团的日常生活当然是很苦的,但兵团的生活却是一个大的集体生活。有时候集体生活往往能帮助我们克服日常生活的苦,给人带来希望,带来乐观的心态。
我的父母曾是新疆兵团一师一团的职工,我曾经跟随他们在一个荒凉的山谷生活过几年。那里曾经是一个水泥厂,没有淡水,要水罐车拉,没有蔬菜也要从山下运。水泥厂烧地窑的时候,浓烟弥漫开来,大家居然在烟雾中躲猫猫,犹如仙境,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记得在后山的苦泉水边生长着唯一的一棵沙枣树,在沙枣花开的时候,一群孩子手提录音机围着沙枣树跳迪斯科,如魔似幻。可是,无论多么艰苦,一群少年没有一个愁眉苦脸的,大家的生活还是那样天真烂漫。新疆兵团的孩子特别开朗活泼。高天,淡云,戈壁滩;昂首,望远,冰达阪。什么都不怕,再苦都没啥。这就是疆二代,兵团的“儿子娃娃”。
在寸草不生的天山南坡的山沟里,生活中最缺的是树。我们太需要树了,一棵树有时候比水更重要。水关乎我们的生命,树却关系到我们的心灵。这不仅仅是遮荫那么简单,人类是树上下来的,树才是人类真正的精神原乡。
水和树在我的潜意识中打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记。
多年之后,我在重庆工作和生活了,我买房子一定要挑嘉陵江边,坐在客厅里能望得到江水才安心。小区里也要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可是,在梦中我还会回到那个寸草不生的山沟。在梦中,那个山沟总是青山绿水的,当我醒来时不由得想念那个已经废弃的小学校。有小学同学居然经常开车去那个地方搞同学会,大家坐在那个废墟中兴奋地唱歌。
兵团人给一棵胡杨树赋予了很多神奇的力量。胡杨树可以断臂求生,也可以向死而生。胡杨籽就像风车一样,随风而去,见水而停,春暖发芽,随季而长。胡杨精神就是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屯垦边疆、守护边疆的兵团精神。父辈们很多已经去世,长眠在戈壁滩上,他们和胡杨一样睡去了。人们在胡杨树身上赋予了很多神奇的传说,说它三千年不死,死了三千年不倒,倒后三千年不朽。其实,树哪有不死的?死后的木头哪有不朽的?这只是人类对胡杨树的一种精神信仰。
我希望能唤醒天山南坡被旷野和风沙尘封的生命意志,表现大漠边缘和戈壁滩上与生俱来的生存状态。当我动笔写新疆的水和新疆的树时,我才发现,我写的不仅仅是树,原来也是人。人和树在那种环境下的死亡,总是让我无法忘怀。
新疆有好多民歌,唱的大多是现实中的缺失,表达一种美好的憧憬和向往。将荒漠开垦为绿洲,把荒山栽满树,这是父辈实践的结果。在文学创作中,一个作家在潜意识中缺失什么,曾经的现实生活中缺失什么,文学就要补充什么。这就是文学最重要的作用。我写了不少新疆题材作品,我的新疆题材是和一些作家朋友的地域背景和自然风貌不一样的,新疆太大了。我写了兵团人的生存环境极为不完美的地方,因为“从不完美中发现完美,便是爱这世界的方式”,就是爱我第二故乡的方式。
新疆是我文学创作之根。《山前该有一棵树》、长篇小说《老风口》都是描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故事的作品,目前,我正在创作有关新疆兵团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新疆是我的记忆之根、文化之根、文学创作之根。未来我想回新疆去体验生活,喝伊力特,把酒唱胡杨,对酒望大漠。
教鹤然:除了新疆之外,《零炮楼》《老家的风景》《赵家庄》等作品,也编织出您故乡书写的另一个序列,那就是您的出生地河南。作为“故乡系列”的两个精神原地,河南与新疆序列取材不同,风貌有别,故事情感也有所差异。能不能谈谈这两个系列创作对您来说,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张 者:我的父母都是河南人。母亲生下我后,父亲去新疆加入了新疆建设兵团。母亲在我一岁多时把我托付给了我的姥娘,要上学时我就去新疆找父母。姥娘家的门口有棵大桑树。那是我少儿时玩耍的地方。大桑树很粗,至少有两搂。每到夏天,大桑树像一把大伞撑起了一片绿荫。树上的桑葚乌紫乌紫的,我会爬上树去摘桑葚吃,吃得满脸是紫色花。我会在树下铺一张席,在席上玩耍,在席上睡午觉,天太热时,晚上就睡在那里。在月圆之夜,孩子们会牵着对方的后衣襟,围绕着大桑树,唱无数的童谣。那些童谣全都是我的姥娘教的,那村叫贾坡,全村都姓贾,全村人中老的都喊姥爷、姥娘,年轻的都是舅,都是姨。作为一个外甥,我极为淘气。那真是上房揭瓦,下塘摸虾,翻墙摘杏,下地偷瓜。现在回想起那棵大桑树,心中还有一股暖流。我在那棵大桑树下度过了最美好最温馨的童年。同时,我在那个叫贾坡的村庄,也度过了一个最讨人厌的童年。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特别是童年记忆和少年经历往往是文学起步的开始。我文学的起步就是从写河南农村题材开始的,当年我写了中篇小说《老家的风景》《老调》《老灯》等,后来写了长篇小说《零炮楼》,河南老家的童年生活对我的写作影响深远。从河南农村题材开始,然后写了新疆题材,最后到校园知识分子题材的写作。这样算来我的写作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写作呈现了三种文学地理标识。
有人说世界观的匮乏是由于地理知识的匮乏。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如何建立起你的世界观,实际上要看你在这个世界上能走多远。你要了解地理观念,不是空的地图上的观念,而是你真的去过没有,你走过没有,你是在高原还是在平原。你曾经在大平原上生活过没有,你曾经在大漠荒原上睡过没有,你在大江大河边垂钓过没有?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有了这些经历自然就有了自己的地理观念,就建立起了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一个人的世界观是由他的人文地理观念所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光读书还不行,读万卷书是一种准备,行万里路才是目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写作,而写作是要有自己的世界观的。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就是要有独立的思考,要有思想和人格,这是作家的立身之本。如果去一味地追随权势,扑向资本,把写作变成既得利益者的服务工具,不为民众发声,不为作品立信,作家就成了跳梁小丑。好作品面对读者是要讲信誉的,不要用文字的垃圾去糊弄读者。
教鹤然:您在1980年代进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在西师度过了充满文学气息的校园生活。在您的小说创作中,最受关注的可能还是以大学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为代表的大学校园生活系列,这些作品想必也与您在嘉陵江畔的求学生涯密不可分吧?
张 者:我的大学三部曲前后写了十多年。从第一部《桃李》出版,到今天已经有20年了。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为我出版了《桃李》20周年纪念版。
在西南师范学院读书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现在看来那时算得上中国在一个阶段内的文艺复兴了。校园内有各种文学社团,每一个同学都是文学青年,都在写诗。整个校园氛围都是文艺的和文学的。文学的种子就在那个时候在我心中播下了。要说真正写以校园为背景的知识分子形象,或者说开始思考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命运应该是在北大读研期间,那已经是新世纪了。在读研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了,当时在《钟山》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春天里不要乱跑》,那应该说是我第一部写知识分子的小说。然后,在离开校园前,我开始集中发表文学作品。中篇小说《唱歌》以头条位置发表在《收获》上。那一年我在《收获》上发了三个中篇,两个头题。然后就是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花城》等刊物发表作品。200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桃李》。
这样在我的创作中除“河南老家系列”和第二故乡的“新疆系列”之外,就有了“大学系列”的作品。有批评家认为,我的“河南老家系列”主要写人性的丰富和悲哀,“新疆系列”则写生存的困境与抗争,“大学系列”主要写欲望时代的尴尬和选择。我认为这个总结很到位。
这样看来我的写作呈现了三个方面,我称之为写作题材的三角关系。我很信任这种三角关系。三角关系往往是一种稳定的关系。我希望我的写作有博大的气象,在技术上首先要拉开时空,不单纯地局限于某一个地域,所以我不断更换作品的背景,更换题材。曾经的童年和少年经历成了美好的回忆,也成为创作的宝库。这个地理的三角关系恰恰和生活经历形成了我创作的一种世界观。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会有这种经历,个人经历有时候不是以个人的意志而决定的。比方你的出生地,你的童年和少年经历,往往是父母决定的,那时候你不是一个有完全的行为能力的人,你无法选择。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个作家必须在童年或者少年时代有丰富的地理文化经历,也不是说没有丰富的地理文化经历就成就不了一个好作家。有些作家在单一故乡的大地上深耕苦挖,挖出了水,挖出了油,也写出了好作品,这也是一种创作方式。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肯定不会在一个文学地理环境中学习前辈作家去深挖,我需要自己的文学标识度。如果让我只面对一种文学地理环境不断地写下去、挖下去,我肯定不放心。那会让我气馁,让我气恼。
我需要一种三角关系,这样才能让我搭建自己的文学之塔。只有这种稳定的三角支撑才能使其更高。我们现在不是提倡攀登文学高峰嘛,从高地到高峰需要稳定的文学高塔。
教鹤然:校园题材看似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现实经验非常贴近,却又很难拉开距离,真正处理好真实与虚构的复杂关系。您认为,书写青年知识分子生存境况和生活状态的时候,怎样才能避免流于一般现象的描述,进而实现小说创作的历史感与纵深感?
张 者:小说创作要有历史感与纵深感,这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理想,或者说这是一种文学常识。有历史纵深感的小说往往能让人怀念过去。怀念过去恰恰是阅读驱动力的一种。当《桃李》出版20年后,你再去读它的时候,你读出了什么?当然就有了历史纵深感。
最近,丛治辰先生重读《桃李》,读出了另外一种感觉。他说:“《桃李》写出的是一派沦落颓丧的大学景象,但多年之后重读这部小说,我居然心生几分怀念。”
这种怀念是什么?这种怀念让我也吃了一惊。你看看现在的校园周边,别说酒吧和歌厅了,连餐馆都养不起几个。“00后”的学生们似乎更愿意猫在宿舍里对着手机、电脑打发闲暇时光,呼朋引伴吃肉喝酒的大学生活已成了前尘往事,缺少了醉后吟诗的校园才子显得无比寂寞。
那个生机勃勃的大学校园呢?我和丛治辰在北大校园中相识,至今我还能记得当年正读北大中文系本科的丛治辰帮我提着一大捆《桃李》穿过校园去开研讨会的情景。丛治辰本科毕业后,先读硕士又读博士,然后在大学里教书,他没有离开过校园。他见证了校园的过去和现在。他重读《桃李》发出了这种感慨:“《桃李》出版已经20年了,作品中邵景文的品行诚然值得商榷,但他和学生们亲如兄弟的平等交流还是颇有圣人遗风。而今学生们越发拘谨,老师们大概也日益庄严,一起面目可憎了起来。20年来校园之外越来越繁荣,也越来越安定,一切秩序都趋于稳固,而那些尽管毛糙幼稚却十足有趣的(准)知识分子也因此风流云散。当名校骄子们纷纷内卷,从进入大学校门的那刻起便致力于考研与考编,似乎《桃李》中那个新旧交杂的校园反而显得浪漫了起来。好的文学作品的确就像一坛美酒,时间会赋予它意想不到的醇香,只是《桃李》这一缕意外的醇香,闻来多少令人伤怀……”
丛治辰的伤怀引得我黯然神伤。如此枯燥无趣的校园不要说和上个世纪的80年代相比了,就是和上个世纪末相比也让人望而生畏。过去的校园是我向往的地方,甚至是我周末散心的去处,在郁闷的时候,总是冲动着想回校园看看。如今,那种激情和疯狂都没有了,校园是我们永远也回不去的地方。我的大学校园题材的小说从此也结束了。当然,人总是要从校园走出来的,出来后的文学地理是另外一种景象,而这些走出校园走向社会的人生经历我还没有开始呢!
教鹤然:您曾经提及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物,以及大后方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很值得写一部虚构作品。不知道您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写作计划?
张 者:西南联大师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坚定担当和心怀民族复兴的强烈使命,为民族独立、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一边跑警报,一边做学问完成学业。他们时不时昂头望着天空,时不时又低头看着书本。昂头向上虽然是防着敌人的飞机轰炸,同时也表现出了不屈的高贵和尊严。无论在什么地方躲避敌人的飞机,他们抬起的头颅望着的不仅仅是敌人的飞机,他们望着的是民族的未来,志在高远。当他们低头向下时,他们又回到了现实,必须认真学习,必须做好自己的学问,为一个民族留下文化的种子。
他们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同时又是乐观和豁达的,这从跑警报中可见一斑。不叫“逃警报”也不叫“躲警报”,就叫“跑警报”,既不“躲避”也不“逃遁”。跑着望天,跑着看书。那种紧张中透出的从容和风度是对日本鬼子最大的轻蔑,同时也透露出中国人最伟大的民族性。
在疏散的人流中,金岳霖拎着装满书稿的公文包,傅斯年扶着患有眼疾的陈寅恪,费孝通则牵着行动不便的妻子……这都是你现在无法想象的情景。陈寅恪的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下降,他坚持准点上课。跑警报时,他跑不远,也上不了山,就带着凳子,在一个大土坑中躲避。昆明雨多,土坑里水深盈尺,他常常坐在水里望着天空,等待警报解除,陷入沉思。
从跑警报中,你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遇到困难时的那种幽默,那种不屑,那种乐观。这一切显得夸张,从夸张中你又看到了荒诞,从荒诞中你又看到了魔幻。在现代人眼里的这一切才真是魔幻现实主义。抗日战争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战争。时局虽然艰难,但学生们坚信,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五千年的文化种子。敌人的侵略,只能暂时改变我们的生活,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不可改变,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炮火洗礼中变得更加刚毅、勇敢、坚强。
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物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去书写。我虽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可要想真正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确实很难。关于这方面的写作计划是有的,也不断地在收集资料,可是还没有完成构思,还没有达到灵感推动我动笔的那一刻,我甚至不知道那一刻什么时候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