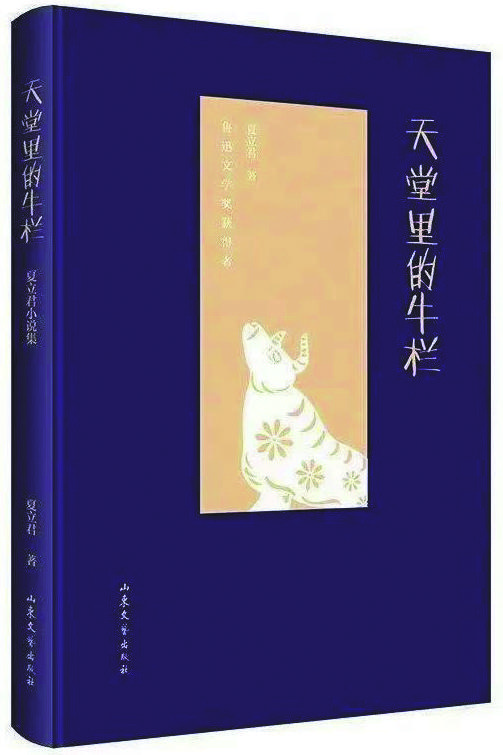夏立君首先以散文闻名,《天堂里的牛栏》是其首部小说集,收入《草民康熙》《一个都不少》《在人间》《俺那牛》《天堂里的牛栏》《兔子快跑》6部中短篇小说。沂蒙、民间是理解夏立君小说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其外延与内涵可进一步拆解为对乡村原生形态及其内部各类小人物自在自为生命属性的指涉、描写与建构。以此为视角和方法讲述一幕幕令人惊叹不已、感慨万千的乡村及更广大土地上的故事,以及在故事中融入对特定历史境遇中人之生存本相与生命本质的追问,就成为其小说最引人瞩目的实践向度。
首先是言说少年之痛、之困。无论《天堂里的牛栏》以“我”这个“人见了人嫌狗见了狗嫌的村童”为视点,讲述物质极端困乏年代乡村人为“吃”而引发的种种发疯发狂的异态故事,还是在《一个都不少》中讲述几个农村孩子因家贫、多子、母病而不能或难以上学的无奈遭际,都为这一文学主题和叙事模式提供了新内容、新形式。
其次是记述民间之野、之趣。回到元气淋漓的民间社会,以生长于其中的典型人物和事例为原型,继而以小说方式对沂蒙民间野生人格、特异形象、传奇故事予以再建构,是夏立君创作中极具特色的部分。比如,《草民康熙》开篇便讲述小毛贼“康熙”以拉家常、套近乎、做示范方式在羊主人眼皮底下当面偷羊的故事,一下子就把读者引入一个庸常却又有趣的世界。
再次是书写民间之爱、之善。比如,《一个都不少》讲述公社小学校长兼班主任的罗老师在大饥荒尾声力劝农家孩子复学的感人故事,单线情节平铺直叙,却异常动人。《一个都不少》是继刘醒龙名作《凤凰琴》之后出现的又一教育题材小说力作,是一篇洋溢着鲁风齐气及浓厚沂蒙地域文化色彩的小说精品,也是一篇直接正面塑造大爱者形象、讴歌奉献精神的新时代文学代表作。
最后是反思人间之相、之异。作者把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重要的表现对象,他尤其擅长并置两种视角(动物视角、人或人类视角),建构两种空间(动物世界、人界),并让前者审视和俯瞰后者,以达成对人或人间世相的反思性书写。《在人间》下半部以老鳖为视点,建构老鳖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既而以老鳖和老鳖世界来反观人和人间世相、世态、世情。《兔子快跑》以一只母兔为视点,讲述它在一年中从定居、孕育、生产、与人对峙并规避风险的历程,并以此来审视人类施与它们的对峙、驱赶、围猎等行为。这两篇小说非常鲜明地区分“人间”与“非人间”(动物界),作者笔力重心在塑造、建构老鳖和母兔的神异形象及其主体世界,但在整体上又无不指向对人间异相的审视、反思或批判。《草民康熙》则另具典型性,在小偷与被偷者的对峙与碰撞中,深度切入现实。小说接近结尾时,小偷“康熙”想洗心革面做个体面好人,可情节猛然反转,读大学的儿子因偷窃被逮捕的消息传来,“康熙”被上官老汉的儿媳妇治好的强迫症立即复发。故事戛然而止,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应该说,这一类小说是夏立君目前最具代表性和艺术独特性的作品,是对他所称“抵达可能的真实之域”“往大里想,往小里说”“越虚无缥缈越能接近真实”等小说理念的充分实践。
小说的语言也值得称道,对沂蒙方言、方腔做了创造性转化与运用。读其小说,首先倍感自然、轻松、流畅,毫无雕琢、做作、装腔之态,从句群推进逻辑到叙述节奏,一切如同流水,自然天成。作者将作为地方语言的沂蒙口语予以艺术提炼、加工、转换,从而生成了一种带有标志性、风格化的文学语言。口语风格,轻松幽默,是其小说语言的首要特色。这种语言风格与刘玉堂有点类似,都以沂蒙口语为基本语料,以普通话转译为主,从而形成了一种极具地域性、个体化的小说语言形态。话语杂糅也是夏立君小说语言的一个鲜明特征。其中,革命、政治等意识形态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常被整合在一起,并让前者辅助后者的意蕴生成,是其中较为常见的实践向度。将散文语言融入小说,亦成一景。这主要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以偏于摹物或达情方式构建“有我之境”;另一种是以述事或谈理方式直陈某种真实,直达某种本质。这两类语言主要是凸显“作者声音”在文本中的在场性,是作者处于自我表达的强烈需要而直接言说的结果。由此也可以看到散文与小说两种语言形态在同一文本中同生共存、相互影响的多姿风景。
总之,小说集中的每一篇都是用心之作,且在思想表达和艺术风格营构方面自成一体。一方面,无处不在的“沂蒙元素”,对生产队“牛栏”这一空间形象、内涵及其内部关系的建构,对乡间诸多小人物形象及其生活世界的描写,对乡村文化及其精神内涵的表达和再建构,以及方言运用的自觉,构成了夏立君小说创作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另一方面,关于大地上的神异之事,关于乡村少年的青春爱恨,关于成人世界里的原欲原性,关于乡间的人伦、奉献、生死……这些令人感叹、感伤、疼痛或戏谑的人与事,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历史风景、时代镜像、人文关怀,将夏立君及其小说的境界、情调、格局提升至“独特这一个”的位置。从小说风格来看,他又较为充分地展现了蕴鲁风、兼齐气的特有格调和崭新气象,既显隐逸之气、汪洋之象,又有舒缓之态,还有大胆、恣意之笔。这种用笔之势、想象之力、修辞之魅,是在莫言、张炜及其齐气文风一脉上的继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