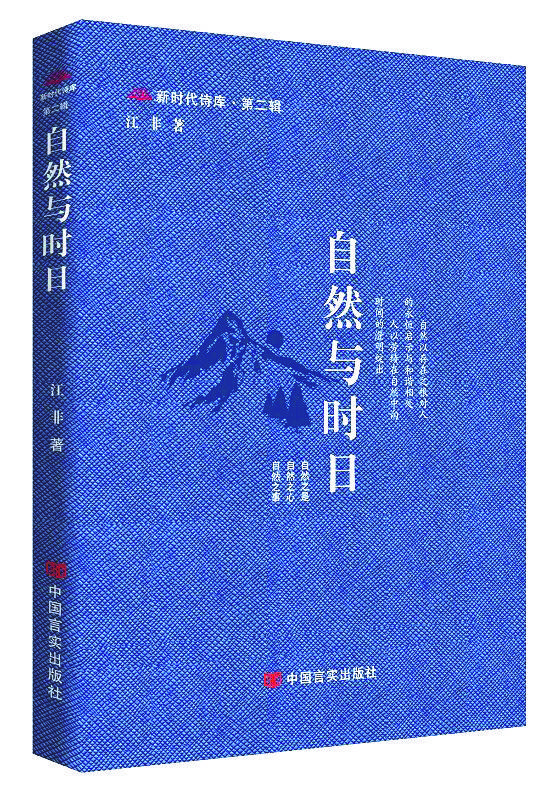作家迟子建曾说过:“一个作家命定的乡土可能只有一小块,但深耕好它,你会获得文学的广阔天地。无论你走到哪儿,这一小块乡土,就像你名字的徽章,不会被岁月抹去印痕。”“70后”诗人江非带着“徽章”,不断地在乡土里深耕。他早期的诗以故乡平墩湖为抒情中心,写出了现代处境之下自身对乡村社会、乡土文明的怀恋与忧戚等种种复杂情状。而后,“平墩湖”虽然成为一个宽泛的概念,但仍作为精神所在的重要场域,构成其抒写中的重要部分。近日,我又读到他的新诗集《自然与时日》,从中感受到他的写作依然以乡土为中心,但更为直白、平和、真诚地呈现出乡村悠然、纯净和宁静的特点。
虽然江非的“乡土”在北方,我的“乡土”在南方,但是乡村的生活气息和意境具有同构性。诗集《自然与时日》勾起我对乡土的深刻记忆。不可否认的是,我熟悉的乡土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望无际的稻田,被纵横交错的高速路分割得七零八落,早出晚归劳作的人“逃离”村庄,土地荒芜,铁牛和锄头渐次退场,村庄如同黑夜中开放的花朵被人忘记。看着逐渐消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劳作场景,看着田间逐渐消失的雀鸟,心中难免产生失落和惆怅。现如今,蛙声阵阵、稻浪翻涌、鸡鸣犬吠、炊烟袅袅的田园牧歌式生活已经成为许多人怀念的一部分。
当现代人无法从现实的自然中获得心灵的栖息,文学就开始发挥作用。我对《自然与时日》爱不释手,并非仅是因为江非笔下的繁星、公牛、柿子树、布谷鸟、镐头、铁锹等勾起记忆深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更多的是这一诗集描写的田野自然意味着劳作和亲和,人在其中获得启发,即《自然与时日》呈现出人与乡土自然的存在关系。
江非曾说:“自然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人的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并令人充满了恐惧和好奇。它会像一场持久的地方性薄暮,进入了我的幼年经验,并和生命深处的某种东西嵌合在了一起。”这便强调出自然中的奇妙景观能够作为诗人的丰富资源,尤其当自然与生命融合起来时,个体的创作灵感能最大限度地被激活。他的乡村生活经验深刻烙印在骨血里,其对乡土自然心存善念和诚挚,常以直白的形式表现这一情致。且看《刈草》:“我在门前的空地上刈草/锈钝的刀刃卷着细嫩的草叶/嘶啦一声,草茎斫断,我听见草根在问/镰刀,镰刀,我是有何罪/你和人的手把我分割,刈倒”。江非在劳作的过程中思考着生命存在的价值——草与人一样,具有情思和存在的意义,人不可放纵自我意志随意践踏之。显然,诗人对自然的善念喷薄而出。又如《除草之日》这首诗:“整个早上/向远处延展/鸟/集鸣着/从前是我的祖父/现在是我/立于其上/带着光/打着露水/举着一把发光的阔嘴锄”。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劳作的场景日渐远去,早上鸟儿立于电线杆头、树梢上集鸣的场景也是如此。时间流转,但在江非的记忆里,乡土自然如故,只是晨间除草的人由祖父变成了自己。他把侍弄田务看作“乡村之子”的使命,且虔诚又真挚地对待耕种的土地和使命。
江非的《自然与时日》非风花雪月,他既直白地抒写自身对自然的善意与诚挚,又洗练地由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表现哲思。如,大雨来了,他在雨中扶起刚栽下的菜苗,琢磨在雨后的菜地补种什么,感慨“那些被思想/和被拯救过的东西/必然会不同于/那些被遗弃/和被忘记的东西”。江非常如此,从血脉的根性出发,传达哲思。他掌握田野自然的生存之道,深谙万物生长秩序。他写果园里刚栽下的樱桃树,“都知道/泥土对于身体/和活着的意义”,它们会像人一样“长起自己的身体”,而结过果的老树,“更不必为它们忧虑”,“风雨中的果园/就让它们在风雨中/自己生长好了”。写没有雪落的夜晚,不去摘下最后一个柿子,“把它留给雪后的/鸟儿/如果没有鸟儿/就让它那么红红的/挂在明日”,留存生活诗意,喻示人不能向自然过度索取。写八月繁杂的农活,除草、施肥、摘果、整理爬墙虎……所有“问题要在八月里得到解决”,人应该顺应时序,放宽心态,“知足就好”。诗歌是江非哲学沉思的瞬间补充,他用“形而下”的方式表达“形而上”的冥想,重构写作的精神维度,同时也为诗歌的现代表达提供新的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自然与时日》在表现人与自然关系时,仍保持对时间的高度敏感。他以往的诗作尤其喜欢将抒写时间定在春季和秋季,但《自然与时日》大量地出现“雪”这一意象,冬季与春、秋季等量,而晨昏依旧是江非抒写的另一时间维度。在他看来,“诗歌是沿缝隙(时间)展开的”。质言之,经由缝隙(时间)产生的一列微妙的、细腻的、磅礴的、奇异的、真挚的感觉和体悟,构成了诗歌的抒写谱系。如《黄昏》,“一只吃草的羔羊,它在/抬头寻找它的父亲/可它的父亲昨天已经被一个屠夫牵走了/它的目光和我碰在了一起”。江非意识中的内在时间将羊的命运、羊与“我”的关系这两个命题连接起来,孤独、无奈的情感油然而生。这正是印证了波德莱尔所言,“几乎我们全部的独创性都来自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印记”。
现在的故乡留给作家的多半是过滤后的幼年记忆,它业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情感象征物,它的存在是异乡人对过去的凝视和重构。现居海南的江非,用智性的敏悟与知觉将乡土的情感进行淬炼,返璞归真,写就《自然与时日》。这本诗集对于失去“乡土”、在“人与乡土自然”关系中迷失的人而言,值得反复品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