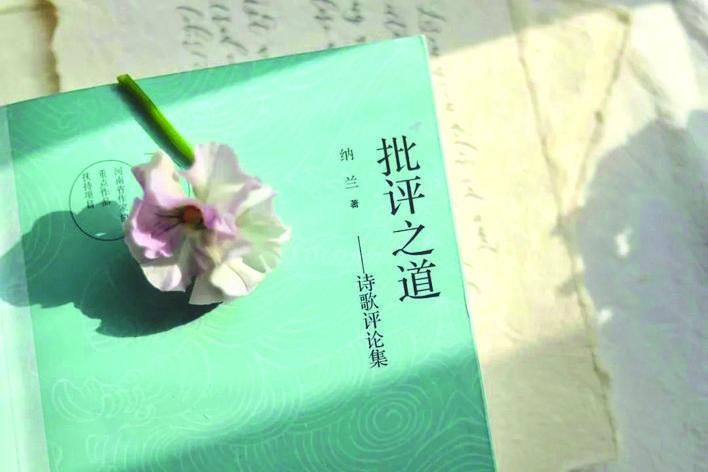英国作家伊利亚斯·卡内蒂在《钟的秘密心脏》中曾说:“哲学家们最深奥的思想有着它们自身的变戏法。众多的隐遁是为了某些事物突然出现在手掌里。”这句话很有意思。前半句大家都懂,柏拉图的理想国,尼采的超人哲学,老庄的呼吸,萨特的存在——哲学家会让思想陷入严肃问题的辩论与纠葛上。卡内蒂的后半句则含糊其词,何为“众多的隐遁是为了某些事物突然就出现在手掌里?”有点玄妙之意。海德格尔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为理解这句话提供了思路。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的本质是道说(sagen),他将道说解释为“世界的显现”。他所说的语言正是诗歌的语言。诗用语言重新命名世界,诗歌语言将真理从日常生活的遮蔽中显现出来。海德格尔举隅的例子是德语诗人里尔克、特拉克尔、荷尔德林。《林中路》和《在通向语言的途中》都是哲学书,但它们首先是艺术和诗歌的评论集。
读青年诗人纳兰的诗歌评论,就如同在欣赏一顶语言的王冠。他的《批评之道》收录了诗歌(集)评论30余篇,另收录《作品与文学批评的隐喻关系》以及《诗的语言是一种生成性的语言》两篇,后面两篇是整本评论集的压轴之作,是纳兰批评观和诗歌观念的集中呈现。纳兰引用乔治·斯坦纳“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写作。他要别人提供诗歌、小说、戏剧。没有他人的智慧,批评无法存在”的观点,进行质疑和反驳。而他在评价张执浩的诗时写道:“最好的诗应该是爱、美学和神学的结合。它既能给人以审美的满足,又能给予灵魂的净化和救赎。”这可以概括他的诗歌美学观念。
如果说“元诗”是“关于诗本身的诗”,那么纳兰的评论就如同一种“元评论”,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不是断裂的,而是一种双胞胎关系的文体延伸。“隐喻让一颗心灵走向另一颗心灵,一个思想照亮另一个思想。”评论也是创作,是诗歌媒介的延伸,二者是双子座。现实中,人们追求所谓的诗和远方,因为诗和远方增加了生命的广度和深度。批评亦是如此。批评为一首诗语言的高贵性作证,好的批评提纯了诗的纯度。比如,耿占春的诗被认为是“思想的灵兽”,纳兰就写出哲学式的评论;汤养宗的诗是“无底”的语言,纳兰就阐释诗人如何追求“空灵意义”。纳兰的评论和诗歌皆出于他的诗观:“事物本身即诗;梦想和现实,此即诗艺。”所以,诗人将批评视为词语的场,为每一首诗立碑,开路。他的诗里溢满光晕,是语言的高蹈。这样的语言质地里,不可过分希冀现实的质感。
作为诗人,纳兰的诗歌创作是隐喻型的。耿占春在《隐喻》中说:“每一个词都在三个向度上与他者发生关系。词与物,词与人,词与词。”追求隐喻似乎是诗人的天性。哈罗德·布鲁姆在《读诗的艺术》里写道:“现在我们普遍把提喻称作‘象征’(symbol),因为以部分代整体的比喻性替代也表示了未完成的状态。在此状态中,诗里的东西代表了诗外的东西。诗人们常会更加认同几种修辞中的某一种。隐喻是在严格意义上把一个词所具有的通常的含义转移到另一个词上。”纳兰就是这样一位隐喻型诗人,他从文本里提取葡萄、麦穗,然后又把这些意象以诗的形式进行生产,让语言“经过一扇提喻之门”。
纳兰的玄学诗思想纹理,在不少诗中可窥见一斑。他在《陌生化》一诗中写道:“雪落下的时候/一切将更新/一颗星与众星/既有哲学的对峙又有美学的疏离/星象可解/卜辞是事物系上的一道语言的活结/我的谬误在于用一种稳定的言辞。”就诗而言,纳兰的诗如同历史,是思考的荣耀;就诗中形象而言,纳兰是在诗里追求水喻。“哲学的对峙”和“美学的疏离”是鸠摩罗什所言的“空”,是本体、底子、源头;“星象”和“卜辞”则是“喻”,是语言的显像,是可以被诗的具象所把握的秘密。
西方中世纪美学往往喜欢将美和光联系在一起。对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人们记住了他对艺术的判断:艺术是对于理念的模仿。但是,人们忽略了“洞穴”背后光的照耀。不管是诗歌还是评论,纳兰偏爱“光”的隐喻。《批评之道》里纳兰使用“光”这个词语有很多处。比如评价青青的诗,纳兰用了“身上的第一缕光”这个字题。而他自己的一本诗歌集《水带恩光》就以光命名,另一首《不远的灯火》里,纳兰也写道:“那些逝去的事物,像是从未逝去/它们靠近爱的源头、从远处光照我。”纳兰并非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会像巴尔扎克一样将社会作为主角加入小说写作中,他全神贯注地将词语凝结到心灵的尺度上。他的评论是玄学的延续,是锁和钥匙的关系,水流和源头的关系。
在我看来,纳兰的《批评之道》是关于中国当代新诗的思想录,充满海德格尔式的哲学气息。“启示”是解读纳兰诗歌和诗学批评的关键词,他的诗歌和评论是一体不可分割的,读他的评论,分不清哪里属于诗句,哪里属于评论和思考——他发明了一套诗和评论体系,诗和评论是词与物相连的脐带。二者之间,诗人通过自我和分身出场:诗歌是象征的,评论就是智识的;诗歌是容器,评论就是容器中的水。对纳兰而言,诗是一件认真完成的事。隐喻、启示、抒情,最后都肩在语言的桥梁上。
然而,诗从哲学中取例,并非没有危险。乔治·斯坦纳在《沉默与诗人》一文中认为,当诗人越来越接近神灵所在,语言面临的转化任务会越困难。因为“面对目不暇接的启示,语词越来越难当重负。”隐喻本身有本体和喻体两个方向,犹如太阳和月亮,一个负责发光,一个负责反射光线。光源的传递发生在语言的尽头,在本体的边缘,喻体才可能作为被照射方照亮。使用超越性的语言,无疑会将语言的水位拉高。过分地靠近哲学,会无意限定诗意的范畴:自省。自省的诗,其意象中本体和喻体靠得太近,读者在句法中无法听到言外之意。换言之,读者能通过语言“聆听”一首诗,理解它的意义,但是却无法听到它的“声音”过程。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