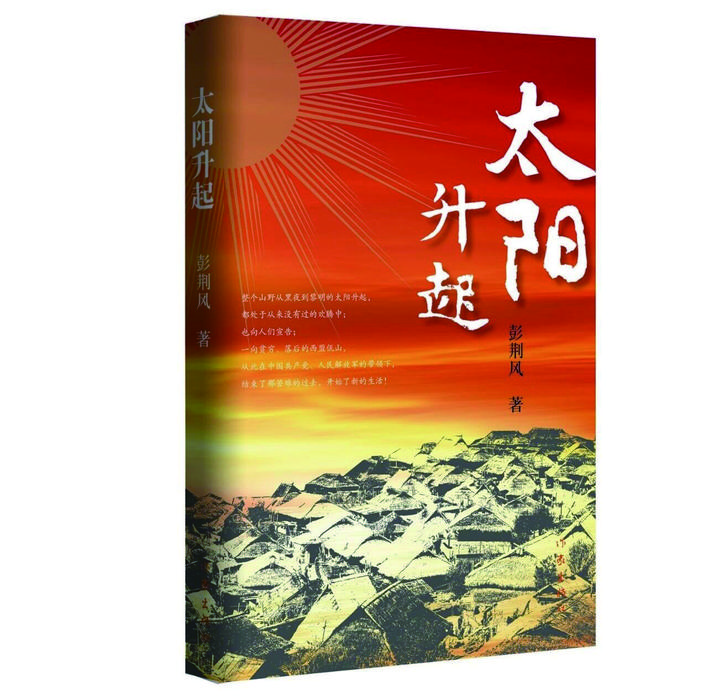佤族是分布在中国云南西南部和缅甸佤邦、掸邦等地区的跨境族群,就中国佤族而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未经过民主改革,直接由刀耕火种、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属于“直过民族”。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阿佤人民究竟是怎么唱起来新歌、过上新生活的,彭荆风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就是通过文学的形式讲述了佤族在1950年代“直接过渡”历史过程的细部。
人都读过《驿路梨花》的节选,更久远的记忆来自20世纪50年代的老电影《芦笙恋歌》和《边寨烽火》,但未必知道这些作品与彭荆风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从1952年开始创作算起,到2018年去世,尽管中间有7年时间含冤入狱,他的文学生涯持续了一个甲子有余。如果将最后的遗作《太阳升起》置于彭荆风创作以来的作品序列里,我们会发现他有着一以贯之的题材与美学风格,素朴、写实、洋溢着刚健清新之风。艺术之树是如此常青,以至于我们在《太阳升起》中丝毫不见所谓的晚郁风格与沧桑暮气,而依然在细腻的描写与自然的节奏中焕发出内在的激情。
《太阳升起》的主线并不复杂,讲述的是1952年人民解放军某部小分队进驻云南西盟佤山村寨开展民族工作的插曲,情节重心集中到侦察参谋金文才带领小杜、小康两位战士艰难地在邻近边境的佤族蛮丙部落,同当地头人和民众之间在不长时间之内发生的事情。通过佤族人民尤其是头人窝朗牛的犹疑、惊惧与排斥,到金文才等人主动友好地接触、交流与救助,最后在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共同斗争过程中他们交融在一起,西盟佤山最终迎来了新的生活。
从叙事结构上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外来者进入某地,改变固有文化生态”的模式。但是,与启蒙精英的教化视角不同,《太阳升起》秉持的是人民文艺的平视视角,即一方面金文才等人因地制宜,严守民族政策,尊重差异性的民俗风习;另一方面,他们也尽力在同情理解的基础上去移风易俗,比如解救被窝朗牛捆绑在人头桩将要处死的叶妙的情节中所显示的对陈规陋俗的耐心改造。这是一种中国式现代化的艰难曲折而卓有成效的历程。
当时在云南实行“直接过渡”的主要有景颇、傈僳、独龙、怒、佤、布朗、基诺、德昂等8个民族,以及部分拉祜(也就是彭荆风笔下的苦聪人)、苗、瑶、布依、纳西、阿昌、哈尼、彝、傣、白、藏等共20个民族及尚未确定族属的“克木人”共66万余人。可以想见,这部小说中所写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而这么多不同语言、族系、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能够平稳过渡,党和人民政府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努力,人民解放军无疑是其中的先锋队。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在民族工作推进中穿插了景物与习俗的展示、爱情故事与战斗情节,从而使得文本具有了相当的可读性,从媒介融合的角度来看,它具备了影视化改编的丰富潜质。
不过,显然《太阳升起》并不仅仅是一个娱乐性的革命英雄传奇或者带有异域风情色彩的民族故事,它的文学性价值至少体现为三点:
首先是历史与虚构的有机结合。小说是在云南解放初期、边境局势未稳的真实历史背景中展开,许多人物与事件都来自史实和作者的亲历经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江花边草笑平生”,正是彭荆风丰厚的生活积累,让整个叙事不仅具有宏观上的说服力,同时在细节上也增加了质感和可信度。小说作为稗官野史的意义也就在于此,它弥补了正史叙述在体验性上的不足,就像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所说的:“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历史提供总体风貌与变迁的趋势,但文学书写不是数据报表或规律总结,它通过虚实相生的具体情境带着读者进入到历史的现场,而让历史中人有血有肉,让历史进程中的事物与行为可亲可感,进而也就产生了感染熏陶之力。
其次是细描与抒情的圆融交汇。彭荆风在小说中平视他的写作对象,既没有在浪漫的想象中把身处边地的佤族民众当作“高贵的野蛮人”人为地进行拔高,也没有用猎奇的眼光将他们视作异域风情而加以歧视,而是真正将他们当作人民共和国当中的平等同胞。他没有避讳描写当时佤族村寨环境的肮脏、人们的普遍贫困、男女之间出自本能的情爱欢娱、“莫伟其”神信仰及祭祀魔巴背后的世俗因素。这是一种“祛魅”的书写,带有人类学意义上的细描与认知色彩,揭开了边远之地、陌生文化的神秘面纱,令现实主义落在了实处。但也并没有因此而堕入到自然主义和相对主义,而是在压抑、紧张的氛围中时常以抒情的笔法表达对未来愿景的畅想,显示了现实主义之上的理想主义。
第三,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过程的认知开拓,拓展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这不仅是《太阳升起》的价值,也体现在彭荆风从《鹿衔草》到《解放大西南》等一系列关于多民族题材的虚构与非虚构作品之中。中国文学的主流在前现代时期,以华夏文化为中心,构成了后来汉文化儒道互补、阳儒阴法结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经过“新文化”运动的现代转型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学观,是以启蒙现代性作为主导;直到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将一度处于被压抑与被损害的少数民族文艺纳入视野之中,提升了民族民间文艺的地位,才有了人民文艺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人民共和”和“人民文艺”的视野中,才得以自觉地确立起来,而边地边疆边民的生活与文化才成为书写的内容。彭荆风以及冯牧、徐怀中等新中国初期成长的作家是这一多民族书写的开拓者,完整展现了中国丰富复杂的文化风貌,正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才构建起了完整的中国文学地图。
如同一滴露珠可以折射出太阳,《太阳升起》也可以生发出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延伸思考。主流文学史的叙述容易倾向于关注某些戏剧性的节点事件和形象鲜明的思潮流派,因而在书写中往往是以“先锋”“前卫”的创新性为导向,而不是真正意义上对一个时代文学生态进行全面的展示。受特定认知范式的影响,当代文学史的惯性语法是按照“十七年”“新时期”“后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为脉络,即以“新时期文学”为例,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朦胧诗、先锋派这样的主线索,而在这条线索之外的作家作品则很容易被忽略。彭荆风的文学生涯横跨了整个新中国70余年,经历了各种文学潮流的变迁,很难被某种单一的话语或符号所归纳和概括。他可能会被打上“军旅文学”或者“边地文学”的标签出现在文学史的某些章节,但阐释是不足的,并且这些标签也不足以构成对他的整体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彭荆风是一位被当代文学史低估的作家。无论从艺术审美,还是从宣传教益,无论从对边地多民族的认知,还是对于中国文学的总体性而言,在未来文学史的重新衡定与书写中,他都应该是值得再认识和再解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