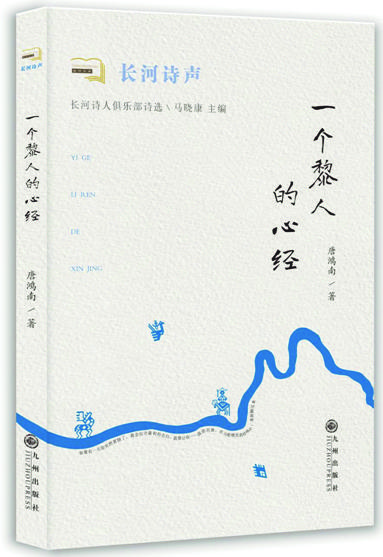□吴 辰
诗不易写,散文亦不易写,散文诗呢,看似好介入,但要写好,也不容易。
文体形式中往往蕴含着“意义”,诗主抒情,而散文主叙事。自中国新文学诞生的年代起,诗与散文就在暗暗角力,也在互相学习,而散文诗正是文体之间平衡融合的产物,在抒情与叙事的基础上,散文诗还着力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发掘出深刻的道理。
黎族诗人唐鸿南的散文诗集《一个黎人的心经》之所以取名为“心经”,是因为其中收纳的作品大多涉及一个问题: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当生活在山海之间的黎族民众总结出的古老生活经验与现代社会生存法则之间产生碰撞时,路在何方?
阅读《一个黎人的心经》,随处可见的是唐鸿南对于黎族命运的思考。作者看到了“故乡的脸在变”,而自己却“别无选择”(《故乡的脸》),也曾追问过“我的父老乡亲啊!今后,你们该往哪里走?”(《山路》)却在寻觅中发现“丢失的鸟声还在,丛林还在,流水还在,人烟还在”(《黎歌》)。于是,唐鸿南“从船形屋的毛孔里窥视一种透亮的眼光”(《向往大海》),他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庄严宣誓,要让黎族“在山歌嘹亮的召唤中,重新醒过来”(《告白》)。百余年间,尤其是在最近的三四十年,那些传统的习俗不断被现代性所吞噬,一些赖以维系民族血脉的东西也渐渐地随着人口的流动而无人问津,作为黎族作家,唐鸿南对这个问题有着切肤之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新的生活方式和商业开发不断地冲击着群山,也冲击着生活在群山之间黎族群众原本宁静的生活,以及那些古老的黎族文明和精神。
如果对《一个黎人的心经》中收录的作品做一个“编年史”的话,可以发现唐鸿南的一些早期创作对这一问题是十分关注的,甚至称之为“焦虑”也丝毫不为过。他写到了为偷猎者所伤害的祖父(《祖父与土枪》)、高山上采石者的灯(《高山上的灯》)、被开发为景点而满目疮痍的西山岭(《家在西山岭》)……在另一些诗中,被“来路不明的拖拉机”拉走的老黄牛(《跪地》),在中秋夜没有回来的“洁白的母亲”(《中秋夜》),同样影射着黎族面对现代性时的处境。如果仅仅是保持着这种焦虑,“心经”也不称之为“心经”了,在稍晚近一些的诗作中,唐鸿南超越了这种焦虑,他发现祖母看到城市的车流“总是说,我来得太晚了,太晚了”(《祖母的背》),他看到侄儿看着运芒果的卡车露出了笑容(《采摘芒果的季节》),他看到黎母山脚下的草儿们“在阳光的呼唤中展开富足的生活”(《倾听草儿们》),这时,他看到了一个民族的韧性,以及蕴藏在民族文化深处的强大生命力。于是,在唐鸿南的诗作中,一种与民族息息相关却又超越具体民族的宏大气场产生了,他不再执着于那些旧日的辉煌或是历史的伤痕,而是将目光放得更远、更长。在这些作品中,“男人和女人并着肩唱,黎话和汉话混搭着唱”(《作雅村》),“那些悄悄的惊喜,将会悄悄地生长回来”(《黎歌》)。在《一个黎人的心经》中,可以读到一位黎族青年的成长心路,他将自己的生活与民族的命运系在一起,反复叩问着“现代”,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唐鸿南的诗作中有一名黎族诗人的担当,也展示了这个古老民族的豁达与奋进,那些过去的伤痕正在被疗愈,一个更为健硕的巨人正在山林中醒来。
对唐鸿南来说,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体裁,更是他反思民族历史与未来的路径。唐鸿南深知“我一个人无法改变你的命运”,于是,他改变自己,“把书桌打造成你喜爱的港湾”“竖着一支会走路的笔,从山里迈向山外”,用“遥远的故事”来“喂养我年轻的诗章”(《告白》)。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一个黎人的心经》中,唐鸿南总是保持着一种“行走”的姿态,这并不是文艺青年口中的“在路上”,唐鸿南无论走了多远,心中总会围绕着那黎族聚居的群山,他执着于“大海与大地的对话”,“真诚书写这片民间的甘苦”(《拜读龙沐湾》)。实际上,唐鸿南并没有停留在黎族聚居的地方,而是走遍了海口、三沙、文昌等地方,他还“左手画着中国地图,右手写着诗歌散文”一路北上(《带着诗歌散文北上》),甚至书写地震后的废墟和灾区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废墟》)。诗作是唐鸿南介入现实的方式,而散文诗的文体更是唐鸿南所寻找到的最适合自己思索民族命运的选择,在“现代”面前,单纯的抒情可能显得软弱,单纯的叙事可能显得保守,那么,就让抒情和叙事携起手来,正如那些携手并进的群山与大海一样,于平凡的生活中寻找哲理,书写人民探索新路的精神风貌。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